按季节生长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于)

《绿茶》是张元今年的第三部作品,如果把电影和歌剧《江姐》分开,它应该是第四部了。最起码在今年前半年,张元是国内最丰产的电影导演。7月份见到张元时,他正在电影洗印厂做《绿茶》的后期。大大小小几台监视器里,很轻易地认得出赵薇,除了长相外,看不出任何小燕子的影子。还有就是姜文。两人和其他几个人正围坐在桌子边,姜文跟别人说,赵薇可以通过杯子里的茶叶看出对方的爱情。桌子边还有位“老方”,仔细辨认后发现居然是著名画家方力钧扮演的。张元挠了挠头说,方力钧已经跟他说了十年想在电影里扮演个角色。只是镜头将来在电影里有多长,处在什么位置还是未知。问张元《绿茶》的内容,他只是很简单地说了句:“一个女孩找对象。”
有一张张元早期的工作照,应该是1989年拍的,他光着膀子贴在摄影机边上,一只眼闭着,一只眼凑近取景框——正在为同学路学长的毕业作品《玩具人》做摄影。现在倚坐在椅子上时不时抓抓头发的张元比那时候胖了,但标志性发型还是那样。记者曾好奇地问他是不是天生就是这样——现在想想这样的问题真是没有必要问,没有一个人会十几年留一样的发型,尤其是像张元这样有好奇心的人。顺便说一下,张元的汽车很漂亮,是奥迪A4,3.0的排气量。他的一个朋友说,张元刚买了新车后,给朋友家打了好几个电话,就是为了说车上什么什么好玩。张元的拍片方式也是这样,只要有钱,只要他对题材有兴趣,就去拍。王小帅和贾樟柯都是有明显创作领域的导演,他们都很清楚自己能拍和想拍什么,而张元就是想拍。

左图:在《绿茶》中,张元启用了最惹眼的组合,赵薇和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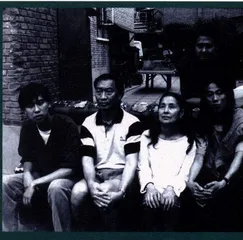
上图:张元和《儿子》中的一家人,他说那是他写实主义的电影中最好的一部
几次见到张元,他都是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即使是在繁忙的工作期间。一方面他会放松自己和推掉不是很重要的允诺。有编辑催逼稿子,经劝说,张元同意写。但在交稿期已经过去的好几天后在三里屯“王吧”见到他,他也不见内疚,兴致很高地说现在要放松放松。后来张元说他写的时候感觉不对,最后编辑只能无奈地放弃了事。但在拍电影上面,张元可是 从来不怠慢。拍完《江姐》,他看到了《水边的阿狄丽娜》,当天就联系上了作者,第二天把作者请到了北京。另一方面,他好像还没有失去对工作的热情。从1989年的那张照片,到2002年拍《江姐》现场他边比划边说怎么样被感动到流眼泪,两者之间的专注没有任何差别。从1989年第一部电影《妈妈》开始,到2002年的《绿茶》,张元几乎从没有闲下来过,不是在拍电影,就是拍MTV、记录片。他始终是自己电影的制片人,或是制片人之一。他说这些电影里有的是他找来的钱,有的他投资了一部分,有的干脆是个人投资。从电影制作角度看,张元是个名副其实的独立制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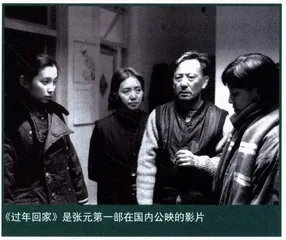
《过年回家》是张元第一部在国内公映的影片
至少在一定范围内,张元最近是人们的主要话题之一。先是年初拍《我爱你》,这部电影据说是张元商业性最强的一部电影,合作者的名单里有王朔和徐静蕾这样有影响的人。联系到张元以往电影的风格和票房收入状况,人们的好奇心很容易被理解:这样的一位导演能拍什么样的商业电影。引起人们争论最大的是接下来的《江姐》。《南方周末》一篇采访的态度有代表性——想知道一位以独立而著称的导演怎么拍起了样板戏。文章写得非常有趣,两个对话人物的状态呼之欲出。事后张元跟记者说那篇文章写得很好,访谈结束后两人还成了朋友,但《南方周末》的记者那样问,最后他只好开始胡说。张元自己认为他是个商业上的老兵,今天人们质疑他为什么妥协去拍商业电影时候忘了他曾经拍过特别多的广告和MTV,他做过50个或者更多的MTV,其中包括崔健、艾敬、罗琦和香港、台湾地区的歌手。1990年他拍崔健的《快让我在雪地撒点野》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MTV,崔健告诉他是就music television。而崔健是当时中国最有商业价值的明星了。

左图:《江姐》的影像尽量复制了25年前的风格。当时的英雄都是:“站在山岗上,身穿红衣裳,手指红太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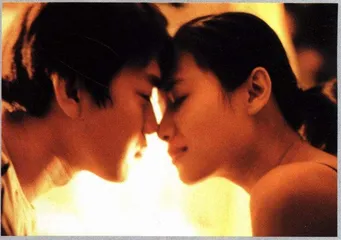
上图:《我爱你》,带有张元个人印记的商业电影
对中国电影的发展状况而言,张元的经历是个特别有趣的现象。1989年张元开始拍电影,他的关注对象是处于边缘状况的人群,提及中国独立电影时,张元是必须谈到的一个人物。但从《回家过年》始,张元转而成为“地上电影明星”。经过1996年特别糟糕的处境之后,张元看起来一下子又在体制内如鱼得水。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制片体系内能这般游刃有余地转换角色的,似乎也只有张元一人。这样,已经习惯了原来张元的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妥协了。但张元认为他亦成功地摆脱了他已经厌倦的、不能接近中国电影观众的阴影。只不过他的过渡过于光滑,所以有人怀疑他的动机,认为他不是妥协了就是开始玩了。
当有的媒体开始讨论张元的做法是妥协还是明智时,张元自己是一副浑然不觉的样子,最起码表面看起来是这样的。因为在他那里,商业和非商业、独立和非独立之间并没有什么界限。界限的消失使得他看起来没有立场没有原则。而张元也确实不打算在这上头有立场。他认为一个导演不需要去反对商业,“否则带来的恶果就是电影死亡,观众减少。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电影还有什么文化意义?艺术本身是就为了追求自由,给大家带来一个最大的想象空间。现在我们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原则和限制,如果自己再给自己加一些限制很没有必要”。张元很爱说:“像我们这样拍电影,导演算什么东西呢?”在这样的认识下,他觉得导演再给自己硬性规定哪些东西能做哪些不能做是太可笑了。今天拍《江姐》的张元并不觉得自己背叛了过去的自己,他认为,都是他的作品,都花了很多心血。
“文革”时张元还在南京,他看得最多的就是样板戏,印象最深的是里面的英雄人物。他看过的第一个样板戏《红灯记》里有一段听奶奶讲述革命家史,张元说小时候看到这里总觉得惊心动魄——这么一家人,不是亲爹,不是亲奶奶,三个奇怪的人因为革命被拧在一起。重拍《江姐》之前,他重新把《红灯记》拿出来看,发现里面还是存在着力量。记者问他拍完《江姐》后有没有重新反思一下到底喜欢样板戏里的什么,张元沉吟了一下说“现在喜欢的应该是里面黑白分明的人物关系。”为什么现在来拍《江姐》的问题,张元说他已经说过很多次,对他来说,现在正是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张元说,如果说他是这部戏的导演,还不如说他是这个戏的复制者,他复制了25年前我们曾经有过的情感和表达方式。在今天这个时代,这样做更有意义——江姐对比了信仰危机的现在,面对不了解中国革命史的西方人,他把江姐比喻为圣女贞德。
张元说他对有理想和有思想的人都有一种崇敬的心情:“你是一个有理想的人,那么你对一个同样有理想的人难道能没有崇敬之心吗?”问张元会不会像江姐那样为自己的理想献身,他说他的时间和感情都已经献给了自己的工作。他的理想是平等、自由和每个人都能有尊严,但不认为自己的电影能对自己的理想起什么作用。他没有原则的原因是电影实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著名的网络社区西祠上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关于电影的讨论,其中张元的名字被提及,有人说他已经明白了,有人说他已经堕落了。但在张元眼里,电影是另外一种景象:“电影还有什么社会意义呢?现在大家都在看盗版碟,可以不出家门。这样已经导致了你没有选择,你不需要花时间,你不要花钱,就可以非常轻松地解决看电影的问题。有的人家里有上千张碟,都昏沉沉地放在家里,这时候你还有什么可珍惜的呢?一部电影可以让你作呕,可是下一部电影纯情动人,而且你可以随时开始看,随时停掉。这时候电影还影响了你什么?那些强调艺术有社会意义的,都是些希望艺术有权力的人。”
十几年过去了,张元说他丧失了很多东西,同时也得到了很多东西。在拍《妈妈》时,他特别简单而自然地拍完了这部电影,没有任何的疲惫。现在做电影,要反复地跟工作人员讨论,要有设计,工作的感觉更强了。第一部电影时,张元还是一个完全的艺术爱好者(他说即使这时候,也没有想过要通过自己的电影改变什么,因为根本不知道观众是谁),到了今天已经变成了非常职业化的一个导演。

《疯狂英语》体现了张元在他几乎所有作品中的一贯风格,以导演的克制将被拍摄对象尽可能地记录在胶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