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195)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张清华 晓玮 田七 土拨鼠)
拖鞋革命
张清华 图 谢峰
天气越来越热,拖鞋开始大行其道。前几天,我所在的公司特意重申了一条规定:所有员工一律不得穿拖鞋进办公大楼,若有违反者,逮住一次罚款一百元。
类似现象我曾见过多次。读中学时,校保卫科干事就经常提着那把园丁修剪花木用的大剪刀跑到教室里搞突然袭击,每发现一只拖鞋,二话不说,一剪了之。
拖鞋为何如此可憎,以致人人喊打?我想大概与其所代表的服饰文化有关。清人徐珂曾说:“拖,曳也。拖鞋,鞋之无后跟者也。任意曳之,取其轻便也。”这种“任意曳之”的定义,正反映出拖鞋无拘无束的休闲精神。
正因为道理如此浅显,我那些普遍受过高等教育的同事才听不进去。就在今天早上,在公司大门口,我亲眼看见我的两位女同事,为逃避楼内保安的检查,一位利索地解下头上的橡皮筋,三下五除二就把脚上的拖鞋改装成了一双凉鞋,业务十分熟练。另一位短发而没有橡皮筋,但她姿态曼妙地从坤包里取出口红,在她那细腻的脚踝处划上一道眩目的彩虹,训练似乎更加有素。我觉得她们的举动正好印证了当年毛委员的两句话,一句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另一句是:“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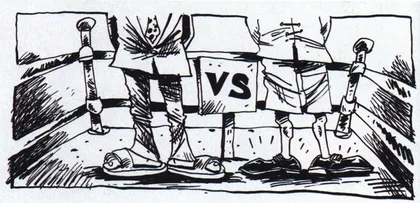
毕竟,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命力永远是最强的。拖鞋并没有在沉默中灭亡,而是开始了反抗。“五一”期间外出旅游,碰到过不少背包旅行者,在他们的行囊中,除了以往必备的洗漱用具之外,我还惊讶地看到了一双双骄傲的拖鞋。受他们启发,我在某风景区为朋友们购纪念品的时候,合弃了那些华而不实的工艺品,买回了一双双竹制的拖鞋。据他们说,拖鞋是除了内衣之外最能给人以贴心关怀的礼物。
在2001年1月的金球奖颁奖晚会上,丹泽尔·华盛顿穿着一双拖鞋迈上领奖台。令人稍感遗憾的是,他的那双拖鞋竟价值200美元,而且还绣着饰物!
不要以为这只是史泰龙的影片《越空战警》中才会出现的装扮,现实生活中我就曾亲眼见到过。是在武汉大学校园里,6月底学生拍毕业照的时候,我的一位师兄穿着他寒窗苦读十九载才换回的那一身硕士服,天知道他出于什么动机,当时竟趿着一双人字形塑料拖鞋。不过说老实话,那一刻我内心里仍然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那一身装扮像极了魏晋时期那些服了五石散的名士,望上去隐隐然有一股仙气。可是他的笑容又太过做作,那僵硬的表情好似给那股仙气贴了个大大的标签:跳楼价,三折。
根治美国人的足球冷淡症
晓玮
美国《体育画报》的资深记者Grant Wahl曾说过:“在美国做一个足球迷,就好像是小学教室里的那个小胖墩。”言下之意,无人理睬不算,还要被同学百般嘲笑。该记者写这篇文字是为足球报道在《体育画报》里的低下地位鸣不平。
美国大众,这里特指的是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对足球冷淡的原因大致如下:其一,看着一群名字古怪的小个子煞有介事地满场子追球,吊足胃口可就是不进球,这种一个半小时竟可能一球未进的情形有商业欺骗嫌疑。其二,足球不能用手,只能用脚和头的规则滑稽得就像开车只能用鼻子和膝盖一样可笑。美国是个讲求效率的国家,不能容忍这种不采取最有效手段达到目标的行为。其三,不少观点保守的美国人认为喜欢足球的美国人有同性恋嫌疑,近年来这种观念虽有收敛,但是如一美国人自称足球迷的话,“SOCCER FAGS这个不雅绰号仍然会在听者的脑海里风驰电掣般地闪现一下。当然,美国男足在世界上基本属替人提鞋的那个档次,这个事实可能也令事事争先的美国人有些郁闷。
针对以上病因,可考虑下如此药根治美国人的足球冷淡症:其一,参照美式足球修改足球球门造型和尺寸,并对守门员的高矮宽窄进行限制,由此还可以减少热衷制订修改规则的美国人,在足球规则上的缺乏话语权所产生的焦虑感。其二,美国女评论家Camille Paglia曾在《沙龙》杂志的专栏上写道:“观摩世界杯后,我对本国男青年印象在一夜之间发生巨变,他们摇晃着从举重房里练出来的虎背熊腰蹒跚而过,那种迟钝和缺乏匀称简直无法和足球小子比。足球小子令人目眩的脚技,灵动的臀部,悠闲的双臂,闪电的冲刺及虚晃一枪时所带来的流畅美感是只有舞蹈演员才具备的。”这种别样优雅的男性体形在女性流行文化评论家推介下,必将引起广大美国女性严重关注。其三,《大西洋月刊》曾载一文探讨美国女足领先世界的原因,作者援引1999年女足世界杯冠军美国队候补门将TRACY DUCAR的见解,“美国女足傲视群雄是因为美国在女权运动上走在世界前列”。看来美国民权组织可以考虑发动男权运动的可能性。其四,早些年,美国人不喜欢“非美国”这个词汇,所以足球被打入异类。可现在,所有打上异国情调标签的东西都成为时髦。比如混合了亚洲风味的西餐,所谓的FUSION菜式是城里新开的高级餐馆的招牌菜,所以说不定足球这个本来对身高体重场地器材要求不高的平民运动,反倒可以借着这股新时尚的东风,在民粹主义一向成不了气候的美国一举成为一项精英运动。这样一来,足球在美国就再也不愁没人玩,缺人看,少钱赚,非美国了。
在天堂里你怎么干?
田七
这样的房子是给谁住的?住进海南博鳌蓝色海岸的别墅里就会有这个疑问。这么说不仅是房间里有浓重的涂料气味,主要是房间里没有什么物件。我想起那个中国股市大庄家吕梁在装修他的大本营时说的一个要求:浪费空间。
在博鳌这个地方,空间好像是足够的。据说博鳌村长蒋晓松拿下整个42平方公里的地方,每亩才花了4000元人民币。折算到我走进的别墅的每平方米(当然不知道别墅的开发商潘石屹又掏了多少钱),脚底下还是觉得它仍然不会太昂贵起来。
老潘不但把屋子盖得不小,物件摆放得不多,还特别透明。以至于晚上冲凉洗澡的时候,发现隔着窗户就是邻居和对岸朋友的阳台……不好不洗也不好大冲大洗,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见我别别扭扭的屁股。后来听人解释,这是新的居住方式:其实并没有人那么在意我的屁股是光着还是穿着,把这个心理障碍解除了,居住的空间就增大了。简直完全玄妙的理论。
蒋晓松买下的地和博鳌镇之间是没有间隔的,于是老旧的民房和新建别墅比肩而立,经常有住在别墅里的房客穿着薄底拖鞋到旧民房里买烟买酒,然后再狂奔回去。
看见蒋晓松是在亚洲论坛的闭幕新闻发布会上,开始花白的头发和矜持地抿着嘴——一个辛苦人儿样。隔着万泉河在蒋村长的金海岸酒店对门,中远置地独资在东岛开发的亚洲论坛新会址正紧锣密鼓建设中。这就是说,明年在论坛开会期间,蒋村长从今年的地主位置上又要变换一下角色了,不知道今年村长是否在会议期间可以赚个钵满。也许博鳌论坛起来以后,人多了蒋晓松手上的地才能卖得更好。
老潘也说他的蓝色海岸一期别墅卖得差不多,大部分业主又把屋子的经营权委托给了老潘,让老潘帮着赚钱。算一下账发现老潘卖了房子又“买”下屋子经营权,也蛮玄妙的。
亚洲论坛散会后,聚集的人群一走而空,博鳌更像个天堂了,风景好并且人迹稀少。临走前几个朋友没地儿可去,在阳台上学习英语,掌握英汉翻译技巧。比如“How are you”翻成“怎么是你”,“How old are you”翻译成“怎么老是你”。那么“How do you do”怎么翻译呢?“怎么干你干”还是“你怎么干”?在博鳌语境里这句话比较明确,翻译成“在天堂里你怎么干?”
黑泽明的《寻枪》
土拨鼠 图 谢峰
也许是代际意识不发达的缘故,我对所有振臂一呼便宣布改朝换代的事都抱怀疑态度。最近看了陆川导演的《寻枪》后,更坚定了这一立场。
《寻枪》当然是近年来不错的一部国产片,情节吸引人,影像风格突出。但我对它还是有很多不满意。就说姜文的表演,我总觉得电影中姜文尽管衣着打扮、形体语言都到了位,但他的眼睛还是出卖了他。这双眼睛里有太多审视,太多想法,太多的理念,泄露了他不是吃那个环境的饭长出来的。拿20年前积累的观影经验打个比方,姜文的眼神儿,使他就像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一打眼就能看出是“我们的人”,气度不凡,与他周围的人看上去几乎就像两个星球上的人。
在影像风格上,我想盖依·里奇导演的《两杆老烟枪》和《偷拐抢骗》的华丽和速度肯定启发过陆川,所以我并不觉得格外新鲜,我只能说陆川把好东西学到手了。
但叫我最不满意的还不是这些。我最不满意的是,《寻枪》没有感动我。我看电影的标准非常狭隘:要么叫我感动,要么叫我大笑。很抱歉,《寻枪》在这两方面都没叫我得到充分满足。在一些场面和对话里,《寻枪》展示了类似小品的智慧和噱头,但就整体而言还不够打动我。
在这种感受下,当影片刚刚公映就有报纸用超粗黑的字体在那里欢呼“第六代导演终结第五代导演”时,就令我格外“友邦惊诧”:这才哪儿到哪儿呀?全国不就才几百个观众刚刚看到电影吗?他们不还没有发言吗?再说了,就算《寻枪》已经拍得尽善尽美了,那报道的角度也没必要这么选择吧,仿佛导演们拍片子不是因为对电影的热爱,反而是出于彼此间将对方放倒的目的,而电影不过是决斗的武器罢了。何必将与电影有关的事弄成你死我活的江湖呢?
黑泽明拍过一部与《寻枪》同样主题的片子,片名叫《流浪狗》,是1949年拍的,黑白片,讲的也是一个警察把枪弄丢了然后寻枪的故事。这个警察叫木村,由三船敏郎扮演。片子到最后,案犯也是在剩下3颗子弹的情况下被逮到了,在历尽辛苦并且胳膊中了一枪后,木村终于把枪找了回来。影片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演得很棒,特别是那个探长佐藤和仅露几分钟面的中年女贼。半个世纪前的片子了,图像免不了斑驳模糊,黑泽明拍此片时似乎还没有成名,他也没有机会利用现代的发达技术拍出眩目的影像,但这部影片是令人难忘的,因为它除了有一个好故事之外,演员们演绎得真是漂亮,不留痕迹地就能叫你感受到生命之轻、存在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