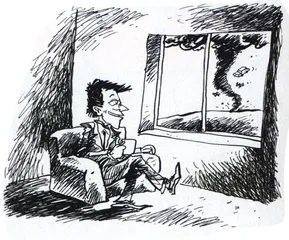生活圆桌(190)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杨不过 包包 阿萝 阿干)
真实电视
杨不过 图 谢峰
住在广州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看到许多内地闻所未闻或需要买DVD才能看到的电视节目,比如《生还者》、《百万富翁》,还有我最喜欢的美国主旋律电视剧,像《纵横四海》、《白宫风云》之类。
最近我又迷上了一个还没看过的新节目《LOST》,一位做娱乐记者的朋友向我讲述的时候唾沫星子乱飞的程度使我确信这个NBC出品的节目的吸引力。它走的是《生还者》一类真实电视的路子:参赛的六个人互不相识,被组合成三对,每个人发给两天的食物,然后被蒙上眼睛送到一个荒山野岭。这地方可能是马达加斯加,或者是新巴布亚几内亚之类只在地理课本上听说过的地方。然后,游戏真正开始了:两个人必须尽快确定自己身在何处,并想尽办法赶紧回到原地。只要能在其他人之前找到回家的路,20万美元就归你了。至于怎么弄到回家的钱,靠什么吃喝,那就看各人的本事了。
20万!我很农民地惊叹道。这可是我一辈子也赚不到的数目啊,别人玩似的就到手了。既然不能参加,每周能看别人在电视上折腾也是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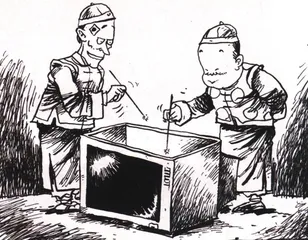
记得有条消息一度嚷嚷得挺厉害,说是深圳也在搞一个类似法国《阁楼故事》的节目,要向全国招募一批人,把他们关在屋子里三个月不准出门一步——干什么?搞创作!
据导演说,如果参加者在三个月期限之内能创作出什么作品,就可以拿到数十万元的奖金云云。乍一听我还挺兴奋,觉得内地节目抄袭终于抄出了名堂。可一细想,我的天,一个大活人,一间房子,有吃有睡,整天皱眉思考,要么奋笔疾书,忧国忧民,或者画两笔谁也不懂冒充后野兽派,狠角色无非把自己身上的肉割几块下来美其名曰行为艺术……值得千万观众巴巴地看几个月吗?
别说我俗,这一类的节目,好玩的无非是男女之间争风吃醋——最好还是俊男美女——或者小团体里几个人一边相互合作一边不忘你争我斗,观众置身局外却对一切全知全能,这才叫过瘾。劳动人民在现实生活里做牛做马,看自己掏钱买来的电视机还不允许爽一把?你在那边厢假模假式表演崇高,何苦来着。
小白的边城
包包
小白长得很黑,而且很胖很矮,在上中学时候,小白就自认为是嫁不出去的姑娘。所以,别的女孩子读情书,小白就读书,各种各样的书。小白看过后还喜欢说书,从《三侠五义》到《笑傲江湖》,从《永别了,武器》到《在水一方》,古今中外,雅俗共赏。我曾是她的同桌,作过她忠实的听众。小白在一节枯燥无味的物理课开始说《边城》,被老师狠狠瞪了几眼,小白就不作声地手写。所以,当我得知《边城》的故事梗概时,小白的笔记本上已经布满了与物理无关的潦草文字。下课铃响的时候,小白享受地说:“童话,三十年代的童话。我好喜欢它!”那一年,小白十六岁。
小白的父亲是位摄影记者,两年后的一个暑假,小白跟着父亲去了一趟凤凰古城,在途中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和一张照片。明信片上是沈从文的墓志铭:“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照片是小白自己的,站在沈从文的故居前,黄昏斑驳的光线斜射在小白黑黝黝的笑脸上,怎么看都是傻傻的。小白在照片背面很工整地题了一阙《沁园春》,我大致记得最后一句是:“在湘西,看水意深沉,彩霞满天。”小白回来的时候特地给我带了一本简装本《边城》。当时正值高三,我就随手搁在了书架上。
我在江南认真阅读小说《边城》时,小白己去了遥远的北国哈尔滨,在哈工大读国际贸易。那时候的小白擅写长信,恨不得将身边的一切人和看过的一切书都一骨脑儿地告诉我,偶尔还会寄来一些她在哈尔滨的各类报刊上发表、署名“黑黑”的文章。隔着天海地北,我似乎还是看到了小白那种纯真、浪漫、朦胧的孩子气,就像我第一遍读《边城》时感觉到的“翠翠”。
到了大大方方恋爱的年纪,我先提及这个小白绝口不提的话题。小白的回信言词认真而忧郁。小白在信上说,这么多年来,以为自己因为出类拔萃而充满自信。但当爱情来临的时候,却彻底发现外表的缺陷就像一道鸿沟,自己根本无法跨越。她有所保留的不置可否,让那个她其实心爱的男生终于失望,转而投向其他人的怀抱。小自在信上还说,在失恋后的某一个夜晚,她又读了一遍《边城》,这一次,从童话中她读出了隔膜,那种在纯朴温情背后深藏着的可怕隔膜。
大学毕业后,小白留学去了英国。我们之间的联系由信件渐渐转为电子邮件,传递越来越快,篇辐越来越短,间隔越来越长,直至中断。据说小白还去了意大利,又去了法国,一个个欧洲的国家就像是一个个陷阱,小白去了,然后失去消息。
去年过年前意外地接到了一个电话,居然是小白,当时她正陪一个学中文的英国人在重游湘西。电话那头是小白愉悦的声音,说会再在沈从文的故居前拍张傻乎乎的照片寄给我,让我好好端详十年的岁月都在她的脸上留下了什么痕迹。
照片至今没有收到,却看到了小白“仿佛有什么地方有了个看不见的缺口,始终无法填补起来”。
不知小白后来有没有再读《边城》,如果有,她会不会读出那本书中最深沉的东西。
那就是孤独。
兔子
阿萝
前两天心情不好,总念着“茕茕白兔,东走西顾”。后来有个朋友对我说,那是个怨妇写的,你别信它。以前一直记得这句话出自嵇康,引用的时候颇觉自己哀而不伤大有魏晋风流,结果一查,居然最可靠的出处是窦玄妻。从晋名士变成汉怨妇,这个夫子自况况得露了马脚。
不过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件事情也将我对兔子这种动物最后的一点脉脉温情彻底清除。我不喜兔子由来已久。我曾经奇怪过:像我这样一个看着电视上“可爱的小白兔”之类动画片、用小白兔儿童牙膏长大的人,为什么反而会对这种至少在国内一直被定义为活泼可爱之楷模的动物抱有如此深的成见。后来我想起了那些千篇一律甜腻腻的女声配音,弱智的兔子一家,粗糙的动画形象;还想起了拿起小白兔牙膏就意味着不能再吃米花糖,并且要带着满嘴好像永远都冲洗不干净的石灰粉一样的摩擦剂味道上床睡觉。想起了这些,与兔子有关的童年回忆就全都成了负数。
小时候,某一年姥姥不知受了谁的蛊惑,说是养兔能“发家致富”,就在院子里养了两对。结果很快这种动物的疯狂繁殖能力让姥姥家变成了兔子的天下。一次去姥姥家,刚走到院子中,就被一群兔子团团包围,个个龇着大牙瞪着血红的眼睛看着我,吓得小孩儿立时哇哇大哭,慌乱中摔了一跤,惨被无数兔子脚践踏。某年我参加数学奥赛,试卷B面第一道题就是经典的“鸡兔同笼”,童年惨痛回忆顿时跳将出来,使我该次考试成绩一塌糊涂。
大学时住在我上铺的姐姐有个很宠她的男朋友,常常给她买些小玩意儿。不过某次鲜花糖果毛绒玩具不知为何竟变成了一对活蹦乱跳的大兔子,那一对兔子伉俪情深,夫唱妇随,上床上桌子上架子,绝不后人,而且极具开拓者圈地精神,跳到哪里,尿就撒到哪里。偏巧我是个过敏性鼻炎患者,没过半天,兔毛加尿臊就让我面红耳赤鼻塞流泪,难过得什么似的。我的几个养猫的同事中午常常会互相控诉猫毛肆虐之苦,然而同兔子比起来,电影中的话实为至理名言:一只小猫,有啥可怕。
后来那对兔子因为吃了太多的胡萝卜圆白菜双双做了饱死鬼,从此我总算不用听着它们咬箱子磨牙夜夜不能寐,虽然它们临终时死不瞑目口吐白沫满身恶臭,让我做了一个多星期的噩梦。
我惟一喜欢的一个兔子形象,就是《龙珠》里面那个胖乎乎穿着长袍马褂的兔子团首领。面对自己不喜欢又无计可施的人的时候,我常常会希望自己像它一样,“呼”的一下把面前的人变成一根大胡萝卜,然后三口两口,吃个干净。
乱子爱好者
阿干 图 谢峰
星期五单位开例会,我去晚了。理由:“我今天坐公共汽车上班,半路车坏了,大家都不愿意下来,以为很快车就能重新开了,但车一直没有好……”接着我就跟大家说以上说法是假的,其实我一个月以来都没有坐过公交车。
虽然我说的第一个理由是假的,但它在我的想象中存在多时。每次我偶尔没有什么急事坐公交车时,总盼望能出点什么小意外。比如熄火了,而且就在车流量极大的十字路口,然后全车人都下来推车,司机着急地打电话。我甚至觉得那时候大家脸上一定是笑眯眯的——二三,哎咳哟,推车忙。被交通折磨坏了的大家总算看到交通也被折磨了一回。
大学有个女同学,貌美且聪明,总是能说出我的心里话。有一次她喜滋滋地说:“我就是喜欢出乱子。”说这话时我们正在上一节6月份的无聊物理课,一位男同学睡得过于享受,口水流到笔记本上,物理老师叫他起来,结果他站起来时脸颊上还粘着一页纸。同学们轰然大笑。
日后我越想她这话,就越觉得说到了我的本性上。生活太有规矩没有意外就过于单调了。但必须承认我不太喜欢出大乱子,比如拖延工作被领导开除了,我也从来不挤到人群里看车祸、吵架。《红楼梦》看过两次,有一节印象非常之深,几个学童跟薛蟠的两个娈童争斗起来,另几个年幼的就在一边打太平拳。我想我就是那种打太平拳的。在一定范围内的乱子总是我最好的提神剂。
我还有个爱好,就是爱看花絮。每到举办世界杯奥运会奥斯卡时,我最爱看花边新闻,基本上是积极搜寻花絮被动得知最后结果的样子。因为花絮在我眼里就是乱子和小意外,没有了它们,一切活动都是单调。
每次看成龙的电影,我都等不及要看结尾部分。成龙电影的结尾字幕总会记录下他的失败,他在里头不断失手受伤。电影里那个英雄可远没有这个人肉凡胎让我喜欢。有人把花絮当研究电影的资料看,而我纯粹是为满足好奇心。我花大价钱买过一张D18的《终结者2》(也叫T2),里面花絮多得简直比正片还长。这部电影一向以技术的完美著称,但看完花絮我才发现如果没有其他杂七杂八东西,完美就不会存在。比如施瓦辛格穿的那件皮衣,我万想不到,幕后工作者准备了几十件同款式的皮衣,然后按照剧情需要折磨成不同的受损程度,让施瓦辛格按戏穿衣。演员表里应该也加上“皮衣一群”。完美的背后其实铺着一层层、堆着一堆堆的乱子。生活让我们兴味盎然的也是这些小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