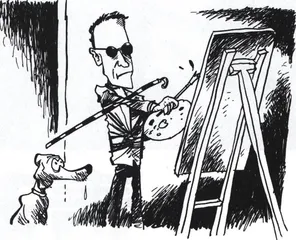生活圆桌(189)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田芸 莫幼群 邓迪 苏从)
人类动物园
田芸 图 谢峰
第一次接触戴斯蒙·莫里斯是在六七年前,我痛苦万状地翻遍那个摆满琼瑶小说的旧书摊,终于找到了一本名叫《观人术》小破书,捧回家细细把玩三遍,爱不释手。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里面女人裙子长短的那段论述。他说,经济萧条时女人的裙子就会变长,而等到经济态势一片大好的时候,女人们的裙子也就会相应的一往无前地短上去,因为人和动物一样都有追寻庇护的天性,而好的经济恰恰是能给女人庇护,让她们感觉安全的重要条件。当时觉得他写的东西很好玩儿,跟其他板起面孔自命清高强调人的精神性的社科类图书不太一样。莫里斯想说的不是人作为人的特性,而是人作为一种动物,和大象河马黑猩猩一样拥有的那种共性。
身为一个动物学家,莫里斯这位牛人的兴趣点好像并不在“动物”身上,他要说的是人,而且姿态谦卑。“我们也许一厢情愿自以为是堕落红尘的天使,但实际上我们只是站直了身子的猴子。”若干年后我看到了莫里斯的另一本书,《人这种动物》(The human animal),在书的封面上他这样写道。在坚持讨论人的动物性的同时,莫里斯好像还进行了进一步思考。这一次他给予了人的动物性一个终极的概括,就是那种存在于所有物种身上的传宗接代的本能。他说到,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人类失去了皮毛,母亲身上没有了可供孩子紧紧攀附的东西,这样不利于那些可怜的小人儿在险恶环境中存活成长。所以,为再次获得与母体的亲密联系,婴儿们不得不使出魅力战术——用纯洁的微笑来打动母亲的心,使母亲再不能够忍心撇下他们。这就是人类笑容的最初来源,也是母亲和孩子之间微妙关系最初的原型。莫里斯就是这样试图用最简单的理由来解释人身上存在的一切复杂的感情和行为,所有一切在他的眼里已经还原到了物种延续的意义上去,所有人们自以为高尚的音乐、美术等种种事业,在他眼里都不啻为这个偌大的人类动物园里的小小游戏而已。

关于这个进化了几千年的人类动物园,我却还是感到有一点不可理解:当人们努力的挺直腰板,深以“驼背”为丑的时候,没有人再会想到,弓着腰,面朝黄土前行,这曾经是我们祖先在直立行走之前的一个天性。
你所唾弃的正是你曾经拥有的。
狂人狂语
莫幼群
我平日爱收集一些狂人狂语,读起来有一种快感,就仿佛是吹出硕大泡泡糖的小孩,觉得世界尽在自己掌握中了。
据梁实秋回忆,那时梁启超去大学演讲,开场白往往是两句话,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然后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真是见过谦虚的,但没见过这么谦虚的。
章太炎素有“章疯子”之称。一次他上街买书,回去时叫了一辆三轮车,但却始终说不出自己的住所在哪里,想必是忘了。于是只好告诉车夫:“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人个个都知道我的住处,你难道不知道吗?”车夫摇摇头,只得把他拉回原处。相形之下,毕加索的运气永远是那么好。1927年的一天,毕加索在巴黎地铁站的人群中,发现了一个天蓝色眼睛、浅黄色头发的女学生,他上前一把抓住她的胳膊,肆无忌惮地说:“我是毕加索,我和你将在一起做一番伟大的事业。”经过6个月的交往,少女终于向毕加索投降了。或许口气越大,就越能征服女性。英国作家劳伦斯这样对有妇之夫弗丽达说:“我将会改变这个世界未来一千年的历史进程。”而他的“勾引”计划也同样得逞了。
叔本华一向以狂著称,但最不买账的就是他的母亲。其母倒也不是凡角,而是19世纪末期德国文坛十分走红的女作家,地位大约与今天的池莉相当。她从来就不相信儿子会成为名人,主要是因为她不相信一家会出两个天才。两个人最终彻底决裂,叔本华愤而搬出了母亲的家,临走前他对母亲说道:“你在历史上将因我而被人记住。”狂语后来果真变成现实。叔本华的私淑弟子尼采继承了乃师的这种狂劲。在论证“上帝死了”时,尼采说:“世界上没有上帝——如果有,我无法忍受我不是上帝。”狂中带有几分周星驰式的无厘头味道。
至于莫扎特,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天才,他自己也不否认这一点,因此当时就有人认为他“浑身上下都是骄傲”。莫扎特喜欢收集人家恭维他的话,详详细细地在给别人的信里报告。这不免显得有几分孩子气,大概他至死还是未长大的神童。他在一封信中这样说:“高尼兹亲王对大公爵提起我的时候,说这样的人世界上一百年只能出现一次。”其实,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小莫实在过于谦虚,一百年太短,如果要加一个期限,我想是一万年。
说到莫扎特,不能不提另一个大音乐家威尔第。威尔第年轻时十分狂放,所有前辈都不在话下,但随着年岁逐渐增大,才认识到自己的局限。他普有如下一番妙论:“20岁时,我只说我;30岁时,我改说我和莫扎特;40岁时,我说莫扎特和我;而50岁以后我只说莫扎特了。”这实际上也反映了许多狂人的共同心态:年轻时常发狂语,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标新立异,吸引看客;年长出名之后,反倒诚惶诚恐起来,有了那么一点历史的与宇宙的眼光,觉得在浩瀚的历史和广袤的宇宙中,个人永远只是一个“虎克的小点”。
圈a
邓迪
现在一不留神就能听到“圈a”这个词儿,这种不中不洋的词汇必然是中国特色,当然,也是中国人英语普及程度不高造成的。
记得刚上网那阵儿,觉得挺新鲜,有个邮箱地址逮着谁就告诉谁,但每次通报地址时总会遇到小小的麻烦,就是邮件中的“@”问题。所以只能用汉语来描述一下:“abc的a外面加一个圆圈。”生怕对方写错了之后发不出信。但即便这样,麻烦还是不断,你碰到一个英语好的人,电脑要是不熟悉也一样要命。一次,在电话里给一个英语颇好的人留邮箱地址,自然就会用英语表示,把“@”读成“at”,但邮件迟迟没有发过来,正在准备打电话询问,对方先把电话打了过来:“你的邮箱地址不对啊,发了半天都给退回来了。”我让他重复一下我的地址,发现没错,连英语发音都很标准,于是对方又重试数次,皆以失败告终,最后不得不以传真方式来结束,并在传真上写了一句话:“谁说网络给人带来方便了?”很久之后,遇到这个朋友,谈到那次失败的邮件操作时,我才知道,他把“@”写成了“at”,难怪发不出去。
但是碰见外语不好的人,你用中国话同样也解释不清楚,还有一次,在电话里给人留邮件地址,为了能让对方明白,我就把“at”说成了“圈a”,过了一会儿,他说:“a我在键盘上找到了,那个圈在哪里?”
这都是五六年前刚刚上网时遇到的事情,现在不太可能再发生了,但凡接触了几天电脑的人现在都知道“圈a”是什么意思了。但这种不太彻底的汉化有时念起来总有点不伦不类,一次,听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播报一个网址时,说的都挺顺溜的,“我们的网址是:www点×××××点com,我们的邮箱是××××圈a×××点com。”可听着怎么就那么别扭。
现在都提倡语言规范化,但有网络存在,你就别指望语言使用规范化,这是好事坏事暂且不必定论,反正语言是要发展的,既然形容女人平胸的词汇“太平公主”都可以进入词典,还有什么语言不能被列入词典的“正式项目”呢。网络语言是最容易流传和最活跃的,词典早晚都会适应网络发展。去年修订的《新华词典》已经把“T恤衫”、“PC机”收录进去,相信不远的将来,它还会把“圈a”收录进去,并且会做出这样的解释:“圈a,即@,读成at,表示电子邮件中某人所在某个服务器的邮箱指向的简称,也可以叫做‘a外面加一个圆圈’。”
大教堂
苏从 图 谢峰
雷蒙德·卡佛的小说中,一开始最震撼我的是《大教堂》。叙述的是男主人公的妻子原来给一个瞎子打工,当他的朗读员。她工作的最后一天,瞎子要求摸摸她的脸,以后她就通过磁带与他保持联系。瞎子后来与一个黑人在一个教堂举行了只有牧师与牧师太太参加的婚礼,后来他太太死于乳腺癌。小说描写的是瞎子到男主人公家里旅居的一晚上,先是妻子与瞎子谈他们“十年间发生的事情”,“我”在中间。然后“我”在被冷落间打开电视,打断了其谈话,转成“我”与瞎子谈,妻子困倦地在中间,后来干脆睡着了。这时有一个细节:妻子睡着睡衣滑下去,露出“一条生动的大腿”,我赶紧把它盖好。小说结尾,因为电视里在介绍大教堂,瞎子要求描述大教堂,当“我”讲不下去时,瞎子要求拿来纸笔,用手把着我在纸上画。然后让闭上眼,闭着眼继续画。最后当“我”睁眼时,明明是一座大教堂耸立在那里。我还记得80年代末,我第一次读到这里时,被震撼得真有点毛骨悚然。
后来琢磨这小说的味道,我读到的是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妻子对瞎子抚摸她的感觉,那是牢记在她心里的手指在轻轻滑动的感觉。第二个细节,“我”对瞎子逝去的女人的感叹。
他说她从不知她在她所爱的人的人眼里是什么样,他从来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她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生活。这时候你感觉最后大教堂的出现就当然极有分量:他明明看到了大教堂却实际什么也触摸不到,他明明什么也看不见却什么都在眼前。闭上与睁开,其实世上有许多事本来是颠倒的。我读到这小说有一个拙劣的翻译版本,专门在最后用了一个我感觉“超然物外”的说明。
实际我读这篇小说,被震撼的是关于传播的内涵。一个瞎子心里凝聚着的教堂,那么容易地就传播到了原来与瞎子没有任何关系的第三者眼前,而且作为第三者与瞎子之间的传播点——妻子也成了放大这种传播力度的工具。当丈夫在瞎子把着手画大教堂时,她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从她所不同寄附的两个截然相反的男人神情中看到了让她震动的东西。在传播中,两人的角色有可能被替换了。最后,大教堂其实只是一个笨拙的道具,我读到的这是一个错位的故事:情感错位,角色错位,最后角色错位又产生位移,这其实是世界的常态。故事与内涵尽在错位之中,我们正是在错位之中找到了各自的距离与位置,并使一切关系可以健康地维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