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知,我无能,我一无所有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崔峤)

格哈德·里希特(法新/AF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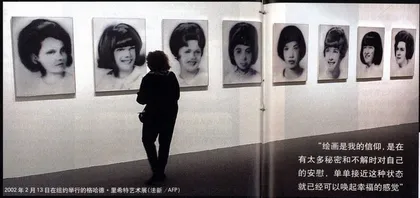
2002年2月13日在纽约举行的格哈德·里希特艺术展(法新/AFP)
里希特的口头禅是:“我无知,我无能,我一无所有。”事实上却截然相反,经常被人称为“变色蜥蜴”,因为他从来都和任何流派保持距离,拒绝被俘虏定位,同时在对外部的沉默艺术里孜孜不倦。他在科隆别墅区的大房子被邻居们称为碉堡:竟没有一扇窗户,这正是他的性格。里希特在作品里追求的不完全是真实,而是一种来自自身的断裂。尽管他身受其苦,却并没有告别它。他拒绝理想完美、真实主观、构造色彩关系等任何总结他表达模式的定义,认为风格是有粗暴含义的词,只有希特勒、斯大林才有自己的风格。
40年的绘画作品给人大开大阂和深不可测之感:他智力过人,游刃有余于不同的流派风格和方法论之间:波普艺术、新浪漫主义、抽象主义、概念艺术、照相现实、表现主义、新表现主义……他作品的恒量就在于不断相对变化的相加。不过他不是形式主义者,也从不是那种兴致勃勃塑造时髦的人。他怀疑感情洋溢的冲动本能,认为艺术应该严肃地表达现实,跨越分割,是通往世界的前哨和隐蔽自我认识的保护所。分析和表现,具象和抽象,蕴含历史和抹却痕迹,同时代德国艺术家中没有人像里希特这样深地体会双重标准的矛盾性。艺术的社会性其实并不在它的政治态度,而在它与社会相对立时所蕴含的固有的原动力。他正因此毫无疑问地是这个时代的代言人。权威的德国《艺术》杂志曾在世纪之交邀请120名世界博物馆馆长评选全世界最伟大的当代艺术家,众口一词的架上绘画艺术“状元”就是里希特。里希特1996年曾获47届威尼斯双年展大奖、“艺术界的诺贝尔奖”日本国家艺术大赏。70大寿之际,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正为他举办超级规模的回顾展,之后将在芝加哥、旧金山、华盛顿等地巡回展出。
里希特生于30年代的东德城市德累斯顿,学过会计和俄语,直到16岁立志当画家,考入艺术学院接受严格“正确”的画法灌输,忙碌于斯大林头像和政治宣传画。1959年去西德被卡塞尔文件大展作品中的艺术自由震动,1961年30岁时候,里希特逃到西德杜塞尔多夫,整整一年疯狂追补从前被忽略的念头作画,又在一个决定性的夜晚把从前所有的作品烧了个精光。他一无所有,却把自己彻底解放了出来。东德的生活经历使他以后一旦觉察到偶像崇拜或者大众集体陶醉的气味就会自动后退,尤其讨厌把作品沦为宣言工具,把个人摆布成“文化现象”的艺术家:博伊斯、伊门多夫、哈克之流。
“有一幅关于夏天下午的照片挂在墙上一年,我能感到当时空气里特别热,寂静,孩子身上好闻的幸福味道,左边的阴影又好像在伺机侵蚀这些美好、少见的光影搭配对比,总是有那么些感觉让我愿意把他们画在画布上。”60年代早期,里希特强调绘画过程和写实的形象:他会把自己拍摄的照片或杂志剪贴作为大幅油画的底本,游弋的彩色风景和夜晚云朵,闪烁颤动的郁金香花束,身着纳粹军装的叔叔,浑浊笔触下的蜡烛和死人头像经常出现在他的构思中。里希特认为摄影是最客观的“第二自然”:“任何媒介的篡改都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前提。我需要的是客观的摄影作品来纠正我本人的偏见和先入为主。如果画一个自然风景,就会开始用我的美学看法改变它。如果画一张照片,可以忘记所有潜在的观点和标准,不去照顾我个人的意愿,这样我才会丰富。”他笔下的人物画总在淡淡的雾里,没有嘈杂和刻意的表情手势,却有一种不可言说的让人长时间注视的感性,这感性又隐在模糊的后面欲言又止。最近两年的作品《S和孩子》、《自我肖像》系列回归人物:小宝贝莫利斯第一次独立作画的场景成了哈哈镜:竟有来自于父亲年纪的恐惧死亡的惊慌眼神!莫利斯在自己身上乱抹的红色汁液不仅象征着诞生的血色,更是里希特反映世界虚无的著名颜色。


格哈德·里希特的作品
始于1977年的抽象画创作对里希特更容易些,“抽象画像呼吸和走路一样,原则上每天都可以画”。他的抽象画面看起来非常美,迷恋彩色的伤痕和层叠的虚无悲伤,保持着它们自己的沉默,仿佛只是一些过去了的,不再重返的记忆,却总会让人在流动的思绪中回想起什么。油彩被用大小不同的铲刀拖曳,刮开鲜艳或者苍白的没有归属感的虚构空间,滑动的颜色、斑点、沉淀看上去更像疯狂而参差不齐的乐谱。德国文化的一个独特使命就是发掘原始的、精神性图像的意义,里希特用机械客观的方式清除掉“每一丝主观与精神的残渣”,从而保持一种中立与匿名的态度。纳粹纵火焚烧过的德国国会大楼一进门左手,就能拜见里希特高22米的通天作品“旗帜”,它带点怀疑论和超然于世的虚无主义:平滑反光的单色色块玻璃拼合而成,德国国旗的颜色黑色-红色-金色组合以纵向排列。把国旗从图腾膜拜的象征性抽离成最空洞的形式,爱国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都不过是个人投射的主观联想,会随观者的立场而有不同的理解。不过它最终还是免不了被争议:绿党的国会副议长称他为“拥护民族主义的江湖庸医”。
1988年是里希特艺术生涯中决定性的转折点:15幅灰泥浮雕画系列作品《1977年10月18日》完成,被《纽约时报》赞誉为“视觉艺术史上惟一的严肃尝试”。作品的标题是极左派的德国红军派恐怖分子头目的葬礼日期。红军派恐怖分子团伙在70年代制造了一系列爆炸、暗杀和绑票劫案等暴行,团伙头目后来神秘死于德国高级监狱内,死因至今不明,被怀疑与警察和法庭报复有关,史称“德国之秋”。里希特把那些惨不忍睹的肢体碎片或关乎生死的特别镜头和新闻照片作为蓝本,画面笼罩着一种哀伤压抑悲悯的情绪,以最适合于表达对宏大宣言拒绝的黑、灰二色涂抹,显得模糊,有时甚至难以分辨。里希特曾困惑地写道:“教条理想主义恐怖分子的死亡以及在这前后所有相连的事件,都显示出一种极端的丑陋和荒谬。他们不是特定的左派或右派意识形态的牺牲品,而是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的强权偶像崇拜本身的牺牲品。任何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信仰都是不必要的,威胁生命的。抗议大多数人必须在不能忍受的环境里继续生活,抗议必须为此付出生命的恐惧和荒唐。”里希特的批评激起社会各派的狂潮,左派骂他殉道,右派怕作品成为怀念死者提及国家强权的敏感标志。
今天钉在里希特写字台后面墙上的是一些“9·11”的照片和报纸剪贴:美国士兵在阿富汗的年轻粉红面孔,世贸中心废墟上的美国国旗。里希特和他的许多朋友从东德逃亡到西方后曾经迷惑于不知所措的个人体验,使他们对“9·11”产生另外的认识,有的更持同情态度。1966年,里希特憧憬过:“除了牧师和哲学家,艺术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不过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大师却对美的意义产生了怀疑,“20世纪的宏篇大论不要再喋喋不休,但愿人类真正能捕捉到内心里的真实。认为我们可以随意远离现实生活中非人的丑陋,不过是一种幻觉。人类的罪行充斥世界的事实是如此确凿,以至于让我感到绝望”。他不介意别人批评他保守主义,他看重家庭、道德、天主教。虽然抗拒所有形式的祈祷,仍然虔诚相信基督拯救人类的希望和艺术的力量:艺术能够安慰和鼓舞人类,跨越所有的内心矛盾,总有那么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