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什么都不是平白无故的
作者:舒可文(文 / 舒可文)
“蝶恋花”系列之一
俸振杰在一段时间内画了一批属于艳俗艺术的作品。在艺术圈内,艳俗艺术也许是一种有逻辑根据和某一种集体性的倾向,但是在圈外,它对流行文化反讽和批判的寓意并不那么容易被消化。好的情况可能是让人觉得很逗笑,其效力至多像流行于办公桌之间和网上论坛中的小笑话,更糟的情景是观众像看一些电视剧,完全不以为然。之后,艳谷艺术作为一种倾向性的艺术状态被提及的频率明显下降,一个原因可能是其中可开发的空间并不宽裕,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流行文化瞬间即变的秉性,反讽流行也不免成了一种流行时尚的转基因物种,所以在这个状态里得到定位的艺术家还得各自努力各奔前程。
俸振杰的原始动机也许并不完全在对流行样式的模仿嘲讽,而是他深感其中无法抗拒的魅力,所以,他才能在后来的画面上有了越来越多的题材。
说起他最开始的创作,他说他有一个好奇:民间艺术和流行文化在表面上似乎都有色彩鲜艳的倾向;从文化地位看,谁都不把它当成“正儿八经”的主流文化,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但是,他们都受到大多数人的喜爱,为什么它们会有那么大的魅力能够影响着大多数人的审美观念呢?从创作“解剖”系列开始,他说,“我试图对流行文化进行剖析,想以此来解开内心里的困惑。其实从感情上来说,我似乎很看不起,可是又好像无法抗拒其魅力!”
他的老师王林在评价他那时候的作品时说,他从分析鲁本斯笔下那些肉感而不无神性的女人人手,开始解析城市生活中各种面孔。“因为是师生的缘故,俸振杰的作品从头到尾我都读过,成熟的、不成熟的,乃至幼稚的。但和一般青年画家有别,他的创作一开始就有一种非常肯定的东西,有时达到偏执的程度。过去他画流行歌星,画英雄人物,画身边的普通人,但不是去表现周遭的生活状态,而是以一种施虐的心理,剥开笔下人物的表皮,暴露出各种走向的肌肉。他说,在铺天盖地的流行文化中,在温暖地浸泡人却又让人窒息的日常生活之内,俸振杰感到不安,感到躁动,于是画中便只剩下对现实的报复——只是偶尔在想起大自然时,他的笔才变得温柔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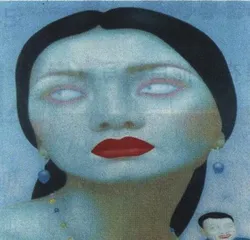
“中国肖像”中的一幅
这点温柔给他带来很多好处,也许是他非常重要的创作源泉。虽然在他自己的经验里,在他对各种面孔的解剖中,一种人生的偶然感及由此而发的不恭之情油然而生,但他在“报复”那种令他困惑的各种面孔时,仍然能控制着与他们/她们的距离。按王林的说法是:他“既不赞美人也不亵渎人”,后面的画面才有持续的空间和进展。
所以在后来的画面上前一阶段的那种满幅刺激的色彩,热闹的氛围,叙事性的服饰与形象少见了,多了微妙的内心状态的琢磨。如果说前一阶段的作品是以表面的浮华艳丽来指责人物内心的空洞与虚荣,那么现在的作品则是以简单的形象浓缩的色彩来琢磨人物的内心景况,“辣妹”、“中国”等一些列肖像都在做这样的努力。好像他终于清楚了,图像文化造就的众多的明星形象,及其塑造的流行趣味并不能简单地嘲笑了之。
“谁出名都不是平白无故的”,这是徐静蕾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说的;在俸振杰这里就应该说,“流行什么都不是平白无故的”。在他的“酷”系列里和现在正在引起注意的“蝶恋花”系列里,他从经典中的形象、好莱坞趣味、民间艺术以及曾经的时尚里,抽取出一类性感信息放在一个平台上。这是一个最直观的角度,就是在混淆时间距离的拼叉中加入了时间的宽容和信息的容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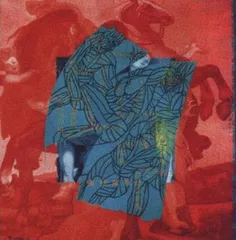
很早时画的“解剖”系列
在“酷”系列里,性感是关于身体的,世艺网艺术总监朱其说:“俸振杰与很多表现受全球主义流行文化影响的视觉画面不同的是,他着意刻画了她们的表情,体现出她们所接受的当代消费文化不仅是一种物质经验,也是一种关于审美的意识形态。虽然不是一个个现实的女性形象,却是一种全球化时代的性感”。他将她们的身体变成侏儒形体,嘴唇紧闭,心旌神摇,对于自己的魅力自信而又得意。她们戴着碧绿的墨镜、绿唇甚至裸身挂着对比色的彩色领带做出类似《古墓丽影》中劳拉的“酷”状。她们似乎是属于未来的,光头、裸体,没有任何历史感,没有可供辨认的与历史性相关的外衣、色彩和背景。
但从她们的身姿,偶尔能辨认出飞扬着裙子的梦露,或者马奈《草地上的午餐》中人物。背景是虚无的,身体是丰富的,审美的幻想也不是的好莱坞一揽子买卖。
“酷”系列之一,虽然貌似没有背景,但你能从中认出马奈《草地上的午餐》
“蝶恋花”是从上海的老月份牌化生而来的,这个系列里,画面变成了一种更温存的观察。俸振杰说,他在书店看到这么一本上海老月份牌的画册,买回来之后他就忍不住地和他自己画的那种现代性感形象做对比,他承认他不知道这中间到底有哪些是共同的,那些不同又是怎么变化的。
现在,他早已经不急于讽刺和夸大其辞地嘲笑了,所以在这些作品中,他别无选择地采取了一种人类学家的观察记录的方式——让现代的性感人体置身于老月份牌的环境之中,两个时代里的两种时尚代言人相互揣摩,在对方的谨慎审视下,时尚退居二位,那种被符号化的人被包装的人都想起了自己的身体与情感,双方都腼腆起来。或者像法国人常常把一个著名的印地安酋长请到巴黎,看看他的反应那样,他把两种时髦形象的物质背景调换一下,让一个后现代女人体站在一株兰花前,那个月份牌上的卷发女人有了一台电视机。
有意思的是,在俸振杰的画笔下,所有人物的相互打量和自我遐想都充分地在画面里完成,而不再那么依赖于艺术家挺身而出的表态,反而通过画面流露出他对流行趣味越来越审慎的利用。表态的任务最好留给罗兰巴特,我们要看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