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快乐抽风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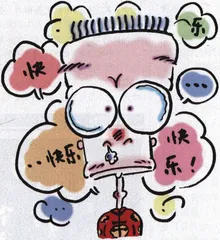
谢天谢地,这个年终于过去了。
当然不是嫌假期太长,除了唐装,让我不快乐的主要是那些没完没了的“祝你快乐”。事实上,从去年圣诞开始,紧接元旦,“快乐”的祝贺就一路未曾消停过。从传统的阖家上门,到电话拜年、电子贺卡、手机短信,到处都有相干和不相干的人不厌其烦地祝你快乐,透过各种媒体,一切平台。农历年是祝贺的高潮,据“中国移动”称,腊月三十和正月初一,仅北京一地,就向1000多万个手机号码发出了超过1亿条拜年信息。情形的确是很热烈啊,至少,中国移动在用不着检查这一亿条手机短信的情况下就以常识来确认了它们的内容。“快乐”之所以会在今年春节达到表达和传递上的高潮,除了年节本身的原因之外,靠的是二零零一年“快乐主义”一浪高过一浪的的推动。在过去一年里,从快乐足球、快乐下岗、快乐考试,到快乐围棋、快乐英语、快乐科技以及快乐洗澡,“快乐”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时髦的关键词。甚至还有人花钱刊登广告,别的不说,没头没脑就单问一句——“你快乐吗?”
柏拉图说:“智者说话,是因为他有话要说;愚人说话,则是因为他想说。”当然,一个基本明白事理并且略知人情世故的常人,很难去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别人的善意。好话谁不想听?谁又不想快乐并且不痛?问题是,被好话问候得多了,人一样会大大地闹心。这种事情跟搔痒有一点相似,英国的精神分析师亚当·菲利浦指出:会给对方带来某种原始快感的搔痒若不能适可而止,“痒的感觉将过于强烈而导致快感转为厌恶感……搔痒与性行为不同,搔痒并没有高潮,若不适时停止,就会转变为羞辱”。
早在苏格拉底/伊壁鸠鲁的时代,人生的“快乐原则”(Hedonism)即已得到了哲学上的确立:快乐是与生俱来的东西,也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即使某人某一群体在特定时间内对这一原则的主动或被动的背离,目的仍是追求终极的快乐。故追求快乐和躲避痛苦,乃人生之两大规定动作,不用教,不证自明。事实上,亚理斯蒂普斯在论证“快乐原则”的时候根本没有花多大气力,甚至犯不上去建立一套严格的哲学体系,他只是祭出老师苏格拉底的辩证法,请对手提出一个“以不追求快乐为目的之行为”的实例,就可以安心回家睡个午觉了。缺乏雅典风度的弗洛伊德后来也为此提供了若干“科学”的佐证,他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提到,快乐是属于“本我”范畴的心理机构,最主要目的,即避开痛苦、产生快乐。“本我”只遵循快乐原则而不理会现实原则。当然,它“偶尔会引起非道德性、非论理性的行为,没有向往一个目标的统一性”。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对于快乐的不厌其烦的唠叨,就是把一个原先就“是”或者天然就“在”且早就有了答案的问题再一次提出来,再以逼供信的方式企图使之重新变成一个问题。世上大多数不知适可而止的愚昧以及因此而导致的歇斯底里,基本方式莫不如此。再者,那些相干或不相干的人,有事没事就公开与你的“本我”对话,大声拿你的ID说事,你烦不烦?长此以往,天性乐观的,也难免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快乐到这步田地,悲观的,就会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即使从经济学的现实角度出发,对快乐的关注是否与经济成长有关,一国国民的“快乐水准”是否随人均财富的增加而增加,至今仍未有明确的定论。据牛津大学对“经济与快乐之追求”的研讨显示,尽管超福利社会如北欧诸国的国民快乐程度一向排在“全球快乐榜之首”,但是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几十倍,而“快乐程度”却与后者相若。美、日、法三国的长期统计资料都显示,近几十年来,人均收入水平增加多倍,但快乐水平却只在同一水平线上波动。因此有学者相信,财富只能解决快乐差异的2%,不过,在人均年收入5000美元以下的条件下,财富与快乐之间的正相关比尤其显著,所以,恭喜发财,我们快乐的日子还长着呢。
以前我只知道佛教国家不丹在GNP之外每年都认真地做着“国民快乐总量”的官方统计,现在我同样也不清楚美、日、法三国对国民“快乐程度”的那些长期统计资料究竟以那些指针为依据。王小波在《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这篇文章里说过,西式的物质快乐与中式的人伦快乐一旦失控,就会演变成控制论上的正反馈,自激,通俗的说就是抽风。我相信,对于快乐的数学统计以及过度关注都属于自激和抽风。子非鱼,每个人对快乐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没事还能偷着乐呢。
快乐大本营就快沦为快乐集中营,本来我想说,能让我更快乐一点的回应是“老子快不快乐,干你屁事!”但我亦深知大多数祝人快乐和问人快不快乐之行为在本质上还是为了他自己的快乐,所以情理上非照单全收不可,就当是助人为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