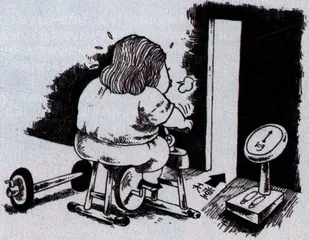生活圆桌(182)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杨不过 何冬梅 布丁 苏从)

丑男人和爱情的纯粹
杨不过图谢峰
一天,我和一个朋友一起撮饭,背景音乐是苏永康撕心裂肺的苦情歌,我对她说:我发现我变态了。我现在特别容易喜欢丑男人,比如说这个苏永康。还有一个典型是刘青云,别人都说他长得特像屠夫,可我就是喜欢他。
这是真的,毕业两年后,大学同学在饭局上向我推荐周杰伦和任达华,说这是新老男人各自的最佳代表,可我只能表情木讷地说,他们不是我的那杯茶。这使他们痛心疾首,觉得我变得越来越土。
喜欢丑男人并非心血来潮,这与一次让人痛不欲生的经历有关,在此之前我也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好色之徒。
简单地说,就是我见了一趟自己的以前爱得死去活来的人。
这是一趟想象中自己会喜欢的旧情之旅,我在最冷的时候去了北京,然后巴巴的和以前的男朋友约了个会,两个人像以前一样像模像样而又可笑地逛了宜家,我原以为寒冷的天气会让我们感触良多,毕竟我们是在冬天谈的恋爱。当年分手的时候我们说,如果你要红杏出墙的话,可千万别忘了我呀!
但一切真的是物是人非,都再也回不去了。
在这趟旅行中最让我羞愧的是,看到自己以前喜欢过的人,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天!原来他这么丑。他长着一张圆形的毫无个性的脸,不很青春但脸上还是疙疙瘩瘩。我记忆中那个风采翩翩的孩子呢,那个让我肉麻兮兮地说:便胜却人间无数……的人呢?
我们都是如此没心没肺,容易忘却。我想起了米兰·昆德拉的女主角,她靠着不断回忆丈夫脸上的痦子确认自己的历史以及辨识男人。他说,历史是遗忘与记忆的斗争,个人的历史也一样。
从宜家出来,天气还是冷哈哈的,我们飞快地分了手,全然没有什么难舍难分。忽然之间,我们成了对方漂亮衣服上一块让人羞愧的油渍。我们变得见不得人。
勾起我回忆的是他嘴角那道伤疤,听说是小时候被人砍的,不大明显,然而我当然看得出来。那条脆弱的弧线,在以前这是个性和温柔的表征,然而现在已经变丑了。
回到正常的生活中之后,我才发现这次经历对我的影响——我不再没事找事去跟隔壁办公室那个令人赏心悦目的男同事搭话了,因为忽然之间发现相貌是那样的靠不住。我想男人还是喜欢美女的,不过普通的男人一定赞赏我这样的想法。
南行记
何冬梅
我的香港朋友可能是肚子里的油水多了需要刮刮肠子,楞告诉我越南菜有多美味。我这人听风就见雨,立刻幻想着美味,报了旅行团登上了去南宁的飞机。等中途在武汉停机40分钟不让下机,我便开始无限后悔。
在南宁和北海除了吃饭就是赶路,光旅不游。一路颠簸总算到了越南,以为可以撒丫子观光了,结果导游告诉我们只能边赶路边看。从边境东兴到越南下龙280公里的山路要走5小时,窄小的道路一直呈S形,一路仿佛坐着海盗船摇得每个人的脸色铁青。细雨中我们的车和对面的轿车在拐弯处拼命对吻,两个司机蹭地一跃而起站着踩刹车,尖叫着在相差几厘米处停下来。在下龙湾草草住了一宿,一夜听越南的鸡鸣狗叫猪哼哼,以及摩托的轰隆声,清晨睁着惺忪微肿的双眼照镜子,怎么看都觉得自己像个苦难的越南女人。另一个嘴欠的朋友说在越南中国人可以找着做大款的感觉,可万通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东西在河内要比北京贵好几倍。越南民风还算淳朴,没有强买强卖。但导游带我们拐弯抹角去的黑店却太夸张了。我在街头花20人民币买的小梳子这里标价650人民币。车上一位男士连车都没下,我们夸他有经验,他说越南人民黑不过他的女同学,一块仿长城的砖头让京郊的老农搁猪圈里沤了两年,刨出来当文物卖给旅行团里一日本老头,这个姑娘边数钱边在心里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在河内住的酒店是法式风格,鹅黄色的建筑在绿色芭蕉的掩映下于夜色中倒有点浪漫,男人们在街头从越南小女孩手里花1元人民币买上一支玫瑰。从落地长窗望下去几只老鼠悠闲自得地在路灯下漫步,仿佛也在过情人节。吃的饭糟透了,除了米粉几乎没什么可吃的,大肥猪肉带着毛毛就上桌了,整天就是圆白菜,素得像没搁油。醋在越南用青柠檬代替,好端端的鱼愣是炸得跟截木头一般。两个天津人半夜满世界找方便面,一帮胃亏肉的人则进行精神会餐,东来顺全聚德肯德鸡麦当劳全让我们想了个遍,我们日夜渴盼着回到祖国大陆的怀抱。
大年初六我们沿着来的路线返回,在左右摇摆的车里沿途体味越南风情。不能去西贡比较遗憾,据说混血美女如云。越南男女比例为1∶7,女人得哄着男人玩,卖东西种田全是女人干,男人则是白天休息晚上干活。一夫一妻制并且实行计划生育,一户能要两个孩子。房子通常建三层高,门脸窄进深长,怪里怪气。没有公寓,一家一户,谁有钱谁的房子就大。但家家户户都特别干净,值得中国人民学习。想想这趟痛苦游每天坐车5小时以上,最恐怖的一天在羊肠山道上走了12个小时,把所有玩的时间加在一块(含导游带我们去黑店的时间)共计15个小时,基本上就在疲于奔命,倒是应验了我出门旅游的根本目的:减肥。
9又3/4站台
布丁
我在大学里选修了所有和儿童文学有关的课程,我倾向于认为并不存在儿童文学这一门类。所有童话故事都是些拒绝长大的家伙们为自己写的,像《坚定的锡兵》,就是个绝望的爱情故事。我尝试着用弗洛伊德那套方法分析每个所谓“儿童文学作家”,这样做很愚蠢,也毫无价值。后来我抛弃了我的这些臆想,老老实实地承认,不管怎样,这些作品都有着极美丽的文字,比如《一个孩子的宴会》,比如《长腿叔叔》。
阅读这些作品可以净化我们那双被污七八糟的文字弄脏了的眼睛,其乐趣和看动画片差不多,当然我说的不是《蜡笔小新》那样的动画片,我说的是《秋天的小穗》那一类的。
早几年众多的诗歌流派中有一个叫作“撒娇派”,他们的宣言中有一句大意是这样的——这世界如此残酷,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撒娇。照我看,所谓儿童文学都该是撒娇派的。而我这个偶尔阅读安徒生童话的成年人也是借机会偷偷撒娇,谁让我年幼时没有躺在妈妈怀里听故事呢。
《哈利·波特》刚开始风行的时候,我对它很有抵触。想当然地认为一个畅销书作家的文字肯定不优美,还有,这个故事肯定不忧伤,好的儿童文学应当是忧伤的。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对于好故事是多么渴望,美丽的文字和忧伤的情怀固然重要,而这世界同样需要好故事。当我在电影院里看见哈利·波特像个崂山道士一样撞向石头柱子到达9又3/4站台时,忽然发现我们在这个世界呆久了,竟然遗失并忽略了所有通向另外的世界的线索与暗示,那本来是我们童年时很容易得到的东西。
我清晰地记起20多年前的一个除夕,鞭炮在黑暗的四周炸响,我捏着一个灯笼蹑手蹑脚地在一条长长的胡同里走,就好像是某种神秘事物的小守护神,静静地对自己的内心说:别怕,我带你去。那个小灯笼中也许蕴含着无限的魔法,后来呢?后来我被我姥爷灌醉了,抱着一棵大树仰望从天上向我蜂拥而来的星星,在那时,我感到自己飞向一个美丽新世界。
后来呢?后来我醉过许多次,醒来的时候依旧停留在这个烦碎的尘世。没有魔杖,也没有9又3/4站台。
窄门
苏从图谢峰
在纪德这部冗长的著名作品中,我喜欢的艺术性其实只有花香与山毛榉枯叶芬芳混合的秋意和那个充满意境的结尾:第一人称的我与朱丽叶默然无语,她乏力地倒在椅子上双手捂着脸,看样子哭了。这时一个女佣进来,点亮了油灯。我不喜欢一个向往女人身上一块手帕芳香、自称“道德上极端堕落”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对超脱尘世描述的虚伪,但我喜欢关于窄门的意境:大门通向地狱,进去的人很多;窄门通向永恒,只有少数人找得到。
关于爱情,其实自《罗密欧与朱丽叶》始,大家都在不断变换方式讲述错位的悲剧故事,改换的只不过是双方关系。纪德这部作品中的道具是爱欲与肉欲的对立:欢乐只能建立在牺牲之后,幸福要分成幸福与追求幸福的过程,而人生下来又要为追求圣洁。在这种分解中,欢乐、幸福与圣洁都成为对现在生活的追问,于是“凡渴求永恒荣耀者必放弃世俗的荣耀”,肉欲成为爱欲境界的障碍,爱欲又成为通向永恒之障碍。这是纪德窄门的基础:永恒是一种境界,幸福在对幸福的思恋而不是欢娱本身。用阿莉莎的话说就是:“假如你在我身边我就不会再思念。”人生目的就这样被一种偷换的境界强调,变成欢乐就在痛苦之中,欢乐就是痛苦的过程本身。而目的是“他们没有得到许诺给他们的东西,因为上帝给他们留了更美的东西”。
按纪德说法,窄门是地狱与天堂之间的分界,阿莉莎走进窄门的过程是一种自残,于是整个人生都变成因经历心灵蹂躏而升华,因这样的蹂躏过程而得到圣洁。问题是:如果这样走进的天堂,那么走的过程是不是“地狱”呢?阿莉莎的逻辑是:首先,在距离之中的爱才是幸福——“这样很幸福,为什么要改变幸福呢?”其次,爱情的发展也就是它的消融,“它会被削弱,因为它只存在你的记忆中”。那么,这样的爱情只能以杀死爱情作为目的——只有死的爱情才是永恒的。而纪德显然是把爱情当作目的的,这目的一个指向圣洁的意境,另一个指向肉欲的消费,而情感完全变成被目的控制的东西。这时作为两性情感交换与滋润的纽带被切断,阿莉莎与杰罗姆的恋爱实际上也就变成了她自己的爱情,对方只不过是她的爱情道具。
也许纪德要借这个构思来抨击宗教的伪善,呼唤人性。其实关于窄门的观念可能是与纪德这个设计相反的:目的可能才是窄门本身,比如天堂地狱。只有在走过目的这个窄门之后,幸福才能成为幸福本身,而不是用杀死幸福的方式来得到幸福。可惜能走过这窄门的,让自己永远生活在灿烂夏天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都在追求永恒目的中吟颂波德莱尔那有味道的诗句:“不久我们要沉入冰冷的黑暗,灿烂的夏天曾经那么短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