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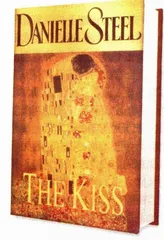 在本期的九部上榜新书中,我们看到了好几位熟悉的作家:丹妮埃尔·斯蒂尔、罗伯特·拉德勒姆、安妮·赖斯。显然,无论他们自己还是出版商,都不会放弃圣诞节前的大卖场。另一方面,也颇有几部系列长篇的续作问世,及时满足了读者的渴想。
在本期的九部上榜新书中,我们看到了好几位熟悉的作家:丹妮埃尔·斯蒂尔、罗伯特·拉德勒姆、安妮·赖斯。显然,无论他们自己还是出版商,都不会放弃圣诞节前的大卖场。另一方面,也颇有几部系列长篇的续作问世,及时满足了读者的渴想。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乔纳森·弗兰曾(Jonathan Franzen)的《纠正》。
打开该书第一页,首先就是一大段大谈“应急铃”的比喻,很有点像我国传统小说的“起兴”。不过,弗兰曾的“起兴”不是给人联想,而是直接切入故事。
话说“应急铃”响起的地方是在一个名字起得很笨的“圣·犹大”郊外社区的一栋住宅里。在里边住着的阿尔弗莱德·兰伯特已至耄耋之年,患有帕金森氏痼疾;他发疯似的将自己关进地下室。用作者的话说,那一声应急铃响,意味着“在兰伯特家中,如同在圣·犹大社区乃至全国,生活都要转入地下来过了”。
接下来是齐普·兰伯特,这个浪荡子由于和一个女生闹出绯闻而失去教职,此时正在以列文斯基的谣传为基础撰写剧本,开篇便模仿那种愚蠢的自白,谈起“都铎(按:指1485~1603年的英国都铎王朝,其后期的伊莉莎白女王时代曾有过戏剧的大繁荣,涌现了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一批剧作家)戏剧中对男性生殖器形象的焦虑”。作者省略了齐普的那段独白,只是通过他的某些小巧的对话,暗示他有写戏的能力。
读者可以把这部书看作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多代家世小说和爱情突变的传奇,又加了些偏执妄想的佐料。也可以把它看作一部既耍些花招又随潮流的作品,而且天衣无缝地模仿旧式的故事性、可读性和人物性格发展,从而诱使人们陷入无底的地缘政治精神不安的王国。事实上,作者已经借齐普之口说出了他的诀窍:将情节的发展雪藏着,一点点抖落出来,以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
小说开篇几页之后,渐入佳境。首先就是齐普那位表面上疯疯癫癫的姐妹丹妮斯的出场;而且她一露面立即就和读者有了交流,使人们和她站在一起。因为她对齐普提的问题和建议,往往代表了读者的心声。
读者的强烈渴望可能会被泼了冷水,如果指出本书的最大悬念无非是那个单一又明确的美国式问题:做母亲的能在最后一个圣诞节把全家人都召到家里来吗?当然,作家是用一系列小悬念展开小情节来吸引读者的。比如,阿尔弗莱德会不会被送进一家康复医院,进入一项据说能够重构他的头脑的新型根治计划,还是用海明威式的方式在地下室里结束自己的病痛之躯呢?丹妮斯又会有什么结局呢?这个结局是与她那出钱的后台、与他的妻子、还是与他们夫妻俩都有关呢?而齐普的今后,会不会因那剧本发财,他的已婚女友可能又与他破镜重圆,而他在给一个实际是骗子的政客当助手去立陶宛搞政变时会不会死在那里呢?还有兰伯特后代中年龄最大的加利——他是位银行家,在生物工程的股票交易中会不会发一笔大财,经不经得起他那位狡猾的妻子和那些装模作样的孩子们的折磨,还是一味地借酒浇愁呢?最后,兰伯特这家的老母亲艾妮德能够拢住这一大家子人吗?——当然,这只是作者设置的无数疑团中的一小部分,但作者制造悬念的技巧已可见一斑。当“纯文学”已经走进了没有情节、只有病态心理的人物这样的窄巷的时候,这样传统式的现实主义手法不但没有过时,反而会令人耳目一新呢。
当然,我们绝不能把弗兰曾这部新作简单地看作传统写法的复活。单单看一点就够了:评家将该书分别与克雷默、品钦、华莱士、纳博科夫乃至卡夫卡、托马斯·艾略特的作品及笔法加以比较。稍有文学常识的朋友都清楚,这些大家可没有一个是以现实主义著称的。
弗兰曾在这部小说中,在诸如命令与能量、控制与许可、传统与革新、墨守成规的老人与尚未定型的孩子等一系列对立问题上严守中立。换句话说,他只把现象摆在表面,把问题提给读者,引导大家去思考,而不急于以叙述者的旁白给出结论。其实,作家正是通过巧妙安排的琐事,来企及一种大效果,正是以令人信服的小枝节,来说明一些人们普遍关注又需要深入思考的大题目。
诚然,没有一部书能够提供我们所想要的一切,但是,像《纠正》这样一部强有力的作品,似乎只受其自身产生的美学观所左右:它创造了给出完整价值的世界的幻象,而且就在我们对它难以释手的时候,也使我们曾经阅读过的其他作品黯然失色了。恐怕,我们在一部小说所想要的一切也不过如此吧?
美国的畅销书中,惊险离奇的故事占了相当比例,涉及家庭生活的,恐怕也是婚变多于温馨。而乔纳森·弗兰曾的这部新作,却用一个家庭的框架包容了诸多的社会现象,将人们的关心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