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173)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杨坊 晨星 刘海明 艾马 莫幼群 徐迅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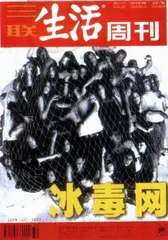
“除了毒品和恐怖活动,生活、职业、技术,似乎都处在一个更加多元和模糊的过程,有意思的是,更加艺术化和情绪化的生存状态,让摇头丸之类的所谓软毒品多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出口。”
上海 杨坊
狗尾巴的功能
武汉市的警察最近又要忙一阵了。据报载,公安局将由局领导亲自挂帅,向全市10万只无证犬宣战。为了打狗,公安局还设立了专门办公室,并下达了杀狗指示:七个城区的公安分局,除了要对街头野犬、病犬一律捕杀外,至少还要各杀没有办证的家养犬300只,其他分局也要各杀100只,这都是硬指标。为了保证完成任务无水份,又便于考核,要拿出看得见摸得着的战绩,最后将根据砍下的狗尾巴来算成绩。杀狗据说是无证犬咬人事件增多,要以此来限制无证养犬。这出发点倒也是在为民着想,但报章赫然在头版用大字标题登出“全市打狗,警方向10万只无证犬宣战”。这事倒回去20年也许没什么,可在21世纪一个向现代化发展的大城市里连砍尾巴这样的细节都要公开登出来,显然暴戾的感觉太重了一点。据警方推测,武汉市现有犬10万只,办了证的只有2200只。杀狗这事,我们即使不为这些宠物的生命操心,也要替公安局想想10万只狗杀起来得多长时间,动用多少警力,再说那么多的狗尸体、狗尾巴又该怎么处理呢?
武汉 晨星
学报的黑色幽默
一段时间以来,承德医学院竟有两种不同版本的学报:同一期学报,从封面封底、装帧设计和出版日期上看,完全相同,而内容却“绝不重复”。这样的学报,一种是公开发行的,通过邮局可以订阅,通过网络可以检索。另一种,却只有作者们人手一册,他们平时藏而不露,只是将来评定职称、晋升职务时,拿来作“敲门砖”。学报之所以自我“盗版”,是由于学报编辑们与作者达成了共识:你要出名,我要求利。堂堂的学术刊物,竟成了“自由超市”,不管垃圾稿或者拼凑稿,只要交钱,就能圆你的“发表梦”,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尤为可怕的是,该学报的自我盗版按固定的“流水线”程序作业:作者交钱、送稿;编辑部收钱、私印“克隆”学报;给作者交货。以《承德医学院学报》为例,自1993年6月到1998年6月,该学报共违规刊出了13期,有10期收取了作者占版费、审稿费15万元,其中编辑部内部人员私分了不少钱款。像这样敢于自我“克隆”的学报,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想必不成问题。如果不是有人举报的话,说不定该学报为广开财源,“彻底”解决版面不足的难题,很可能会将一期学报,出版成A、B、C、D……“号外号”学报。果如此,这样的“学报”还能叫学报吗?
河北 刘海明
“事情普遍”就评不上烈士吗
据媒体报道:“山东省昌乐县农民马清勋奋不顾身抢救不幸落入地瓜井的马清仁、马法祥父子,后来马法祥因抢救及时得以生还,而马清勋和马清仁却因在井下长时间缺氧窒息而抢救无效死亡。”民政部门优抚科的同志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介绍了批准革命烈士的有关条件:为保卫和抢救人民生命、国家和集体财产壮烈牺牲,他们说:马清勋与获救者马法祥尽管是叔侄关系,但这并不影响“评烈”。不过,因为菜井救人事件较为普遍,因此马清勋舍己救人的义举尚不够“评烈”条件。仅仅因为是这样的事很普遍就评不上烈士、享受不到烈士的待遇?这个逻辑真是怪怪的。在战争年代,有时成连成营的牺牲,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是很普遍的事?如果照这个逻辑,他们是不能被评上烈士的。再者说,“菜井救人事件较为普遍”吗?不知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
看了这个结论后,我们不能责怪现在人们越来越不喜欢舍己救人,尤其是在菜井里救人。
山东 艾马
常识与良心
《精子的死刑》一文引起了我的感慨,但我关心的不是死刑犯究竟有没有生育权,而是本案中的死刑判决本身是否准确。我十分同意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冯锐先生的观点——“如果关于这个案件的说法是真的,确实是被害人先动的手,我认为一审判他死刑太重了。”冯研究员是基于法律理论的角度这样说的,其实从普通人的常识角度也能毫不费力地得出同样结论。说得偏激点,大多数案件或许只消用常识来判断就行了,而且越是像杀人之类的重大案子越是如此。英美法系的陪审员制度,似乎正是建立在“相信常识理性”这一基础上的。一旦法院作出的判决明显偏离了普通民众的常识,肯定会招致民意的反弹。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某些法官和审判员的法律知识当然是不容置疑的,但却对常识视而不见,是不是他们的法律理性太发达,反而抑制了自己的常识理性呢?还是有其他什么别的原因?
关于良心,一千年前欧阳修父亲的故事对这个词作了很好的诠释。欧阳修的父亲做判官时,经常独自一人在夜里审理案卷。一次,欧母听到他在唉声叹气,便问他何故,他回答说:“这又是一桩被判了死罪的案子。我想从案卷中,给这个被判死罪的人找一线生机,却总是找不到。”欧母又问:“为犯了死罪的人找生机,这能行吗?”欧父说:“我尽力去寻找,而又实在找不到,做到这一步,死者和我就都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了。我总是想方设法为被判死罪的人寻找生路,而世上的官吏却千方百计要置他们于死地。这实在可叹。”他怕欧母还不明白他的意思,又说:“我不是想为那些真正该判死罪的人开脱,我是担心有草菅人命或者误判的情况发生,让一些普通老百姓冤沉海底。”欧阳修父亲之所以“良心大大的”,是因为深知“人死不能复生”——这是最大的常识。
如果一位法官或审判员既失去了常识,又没有了良心,就真不知叫人说什么好了。
合肥市 莫幼群
慈善的巨大黑洞
出现慈善黑洞是早晚的事情。今年“两会”期间,就有政协委员建议出台《慈善法》和《捐款法》,对慈善和募捐行为进行规范,使慈善机构更多地发挥扶贫济困的作用。慈善是一项事业,而且是一项以人为中心的事业,尽管看起来“核心”是“钱”。从事慈善事业的人,从广义的角度看,都是“志愿者”,像胡曼莉那样的身份,本是志愿者的角色。同样的情况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志愿者法》。法律不完善,就难以从根本上规范其行动。我们现在重视了对官员腐败监督的打击,但对慈善领域的“腐败”如何惩治实在是个“新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慈善腐败”比一般贪污受贿更具杀伤力,因为它伤害的是社会良心。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善款变成了他人的“恶款”,自己的爱心成全了他人的私欲,那么,他心中的道德金字塔就会轰然塌倒。现在,从胡曼莉头上摘除“中国母亲”的光环是容易的,但从她和她这一类人心中驱除私欲却很难。
杭州 徐迅雷
短评
叫板不是本事
近两天的报纸上,“万德福”这个名字出现频率颇高,原因是继“荣华鸡”、“红高粱”的偃旗息鼓之后,它主动担纲叫板洋快餐的重任,挑起新一轮“斗鸡”、“顶牛”类争斗。细看这些文字,不禁佩服万德福的胆识:别看“八字还没一撇”(报载其前期资金正在到位,且处于选址中),“颠覆”麦当劳似乎只是时间早晚的事。别看不细说到底卖什么货和如何确保产品质量,但滚滚的客源、超级连锁的惊人规模显然就在不远处等着。气势压人,“板”叫得也响:“炒作炒作,炒是为了好作;吹牛吹牛,吹是为了更牛”(万德福策划人语)。其实,敢在中式快餐不敌洋快餐的大趋势下跳出来充当“民族英雄”本无可厚非。不过一来跳得太猛容易闪着(尤其是舌头),二来——咱有必要非跟洋快餐叫板吗?中式快餐其实有很足的“先天”。中国几千年食文化的宝库远未被充分挖掘。一些聪明企业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宝贵特色,于是有了“老家肉饼”、“马兰拉面”、“永和豆浆”……它们没闹什么“斗鸡”、“顶牛”、“叫板”噱头,踏踏实实地抻面烙饼磨豆浆,照样宾客盈门,连锁规模也日渐壮大。 更有意思的是,虽然这边一茬茬战鼓擂得响,被设为假想敌的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却从未应战。麦当劳说:“我们的敌人是自己。”大度得一塌糊涂。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入世后,难道每进来一家洋商场、洋饭店甚至洋“三替”,我们的家乡企业就要举着“民族精神”的大旗站出来叫板,并把这叫板变成商业利益的基础?有这工夫,多跟人家学两招,比如怎么把质量搞得更规范,怎么把市场营销搞得更高明,怎么把企业形象树立得更大气。
中式快餐,还是先向自己“开战”吧!
北京 石桦
(本栏编辑:吴晓东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