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铁路的环境与民生之争
作者:巫昂(文 / 巫昂 李伟)

格尔木:从驿站到城市
早上醒来车窗外便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滩,枯黄的骆驼刺和白花花的盐块被甩在身后,景色一成不变;除了偶尔闪现的道班工人,看不见任何生灵。这里是深陷高原的柴达木盆地,不远处那片闪耀洁白光芒的地方就是国内最大的察尔汗盐湖,方圆1600平方公里,盐壳最厚处达15米。在这不毛之地的深处,还有柴达木油田。
然后就到了格尔木——沙漠南端的一个绿洲。1984年前青藏一期铁路穿越盐湖和戈壁修到了这里,在此后的17年内格尔木每年GDP增长都在21%以上,人口则翻了一倍。2001年6月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开工,格尔木再次成为一个时常被议论的城市。
格尔木城内有不少地方正在施工,道路需要拓宽,各种星级宾馆在浮出地面。出租车司机为记者寻找住处还费了些周折,因为不少宾馆从年初开始,就都被“铁路上的人”包了去。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二期从格尔木开工,实际上一年以来,参与建设的全国十四个铁路局都在这里设有总指挥部,再加上铁道部、西北勘探设计院、中科院冻土所总共近二十处指挥部,“一条街上就有好几个,你打听的是哪个?”一位当地人这样反问记者。很多四川农民听到青藏线开工的消息连夜买火车票赶往格尔木,而记者在西宁火车站候车时,就被卖烤羊腿的回族老汉认定是去讨生活的民工。
市委书记李超告诉记者,格尔木把很多土地无偿给铁道部用作货场、住宅,其中就包括市政府对面的大院——现在的铁道部总指挥部。同时格尔木也会得到60亿元投资,“5年内格尔木至少涌入移民5万人,相当于现在全市人口的1/4,常住人口的一半”。
从地理条件看,格尔木并不是个吸引人的地方,北边是数百公里的戈壁荒滩,盐比土多,草木不生;南边是绵延不绝的巍巍昆仑山挡住去路,常年大风不断,市内树木都向东南倾斜;降雨少得可怜,年均雨量只有23.6~68毫米,而蒸发量达到2386~2928毫米。不过记者还是有幸赶上了一场小雨,淋得一身泥点。
1954年以前的地图上根本找不到格尔木,只是一个泛指,是蒙语“河流密集的地方”;是格尔木河畔游移不定的18顶哈萨克牧民的帐篷。今天格尔木的后代们都会声情并茂地讲述这座城市的起源:“1954年第一野战军幕生忠将军修路至此,四野茫茫不见人烟,有人问,‘格尔木在哪儿?’慕将军随便找了块木板,往地上一插——‘格尔木就在这!’”
直到1956年格尔木才有了第一座砖石结构建筑——两层的“将军楼”。很长时期内,格尔木被人称为“帐篷城”,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个驿站,一个军用驿站。由此向南700公里到安多,向北500公里到敦煌,向西北800公里到西宁都罕见人烟。“一城百姓半城兵”,李超向记者回忆当年的城市,1957年李超随父亲的部队来到这里,“只有一条街,一路上都是兵站和军车,堆积如山的货物在此转运”。青藏公路通车后相继兴建了砖瓦厂、石灰厂、皮革厂、盐场、钾肥厂等基础设施。随着新藏、格敦(格尔木—敦煌)、青藏以及西格铁路在这里交汇,格尔木开始源源不断向外输送钾盐,目前已经垄断了国内95%的市场。柴达木深处的石油也随着70年代建成的管道运到了拉萨和内地。盐湖集团与柴达木炼油厂是格尔木最大的两家公司。
最让人惊诧的恐怕是格尔木的夜生活,台球桌架上轮子推到街边,操着各种口音的年轻人就在路边唱卡拉OK,回族人的小棚子里挤满了游人和食客,小伙子们说着各自的艳遇,深夜两三点依旧熙熙攘攘。“西宁、德令哈的领导们都爱到这里玩。”《西海都市报》记者李明说。仿佛美国西部片中的小镇,这里也洋溢着粗糙而兴奋的冲动,街头几乎看不到老人,居民的平均年龄似乎三十出头。
昆仑山—唐古拉:生态战场
从海拔2780米的格尔木到4837米的昆仑山垭口只要两小时车程,桑塔纳可以轻松地开到每小时120公里。然而让人失望的是,昆仑山并非传说中的人间仙境,却完全是一片不毛之地;车窗两侧依旧是黄沙漫漫,鸟兽不见。
“两年前在那里竖下的电线杆,如今被流沙埋成了十字架。”生态学者徐凤翔告诉记者。今天昆仑山惟一留给后人们的是著名的昆仑玉矿,冬天时常有人趴在冻住的昆仑河上爬进矿区偷玉。在山口处有一座破败的西王母小庙。小庙除了供奉西王母外,菩萨和班禅也有位置,门口还立着两个嘛尼堆——昆仑一过就进藏区了。
从昆仑山口到唐古拉山500公里,平均海拔4500米,青藏公路——名副其实地成了通天之路。公路两侧是一马平川的高山草甸,只是草种稀疏,虽经一夏的生长仍高不逾寸。冻土在阳光下融化,形成高原上一个个小湖泊。沿线雪山连绵,融水隔出条条小径,汇合后常随公路同行。这块方圆8.3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地区是世界第三大无人区,可可西里是她的地理名称,蒙语意为“美丽的少女”;人类学家称这里为“39部族”;而生态学者们都把这里叫做“三江源”。这里发源的水系养育着世界上一半的人口,常常被称为“亚洲的水塔”。
公路对草场的影响随处可见:汽车的碾压使冻土融化,形成一个个水坑,两侧沙化严重,基本寸草不生。“毕竟公路只是一条线,它对高原生态的影响微乎其微。”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平说,“更大的后果是间接的,是那些公路带来的发财梦。”
实际上记者一路上连藏羚羊的毛都没见过,更别提驾车和它们赛跑了。与此相反,我们首先撞上的竟是一队回程的淘金者:二十多人的样子,分坐两辆卡车,车上塞满了帐篷和炉灶。由于汽车爆胎,淘金者们在路边晒着太阳、抽着烟,但他们的眼睛是血红的,显然无人区的日子极为艰苦。

人海战术已不再是现代大型工程的场景了但在高原烧水煮饭仍然不容易(腾科 摄)
可可西里有黄金的传言兴起于90年代初,徐平印象深刻的是1995年进藏,“从西宁开始,1000多公里的路上都是向可可西里进发的农民,搭便车的、开卡车的还有开手扶拖拉机的”。探险家杨欣每次去三江源都见到大批的金农,“水中的含金量是很低的,但他们都用最原始的开采方法,像地毯式轰炸一样掀开草甸,引走河水,用筛子筛。这种野蛮的方式曾让长江源头第一县——曲麻莱没了水喝。”挖金子赚不到钱,金农就变成了偷猎者。
自然界千万年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在藏民心中,藏羚羊的产羔地是一个极其神秘的地方。”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扎巴多杰说,“可可西里所有的母羚羊都集中在几个水草丰美的地方。传说大雁和藏羚羊是在一起的,羊食大雁的粪便后,奶水多得顺奶头滴在土地上,又被大雁所食,它们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但现在扎巴多杰看到的确实另一番景象,“上万只羊产羔时,天上的鹰和地上的狼都尾随而至,鹰吃胎盘,狼追逐羊群,扬起阵阵尘土,这时候母羊和羊羔都唾手可得。”他用朴素的平衡观这样向记者解释这里出现的生态危机。
徐平感受最深的是,老鼠多得不得了,“我奇怪——为什么草场破坏越严重,老鼠越多,水草丰美反倒很少?当地人告诉我,草多的时候,老鼠的视线被挡,鹰和狐狸捕食相对容易,但草场退化后,双方虽然都容易暴露,但老鼠可以转身进洞,逃之夭夭。”
“青藏高原长期是一片净土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严酷的气候和闭塞的交通。”徐平说,“但畅通的公路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使侵入者可以用极低的成本牟取暴利。”目前可可西里已经成为生态保护的第一战场,但“魔”与“道”的对抗远非草原上赛马那么公平简单。杨欣曾经参加过“野牦牛”队的一次远征,“我们行程1300公里,光汽油就用去了3吨,但一个偷猎者也没抓到”。
楚玛尔河:民间保护的有力与无力
砖红色的楚玛尔河是长江上游的一条大支流,两百米长的公路大桥纵跨南北,这里也是藏羚羊每年越冬迁徙的必经之路。河道以北30公里有一排小房子——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自从野牦牛队划归可可西里保护局后,这是高原上惟一的一个民间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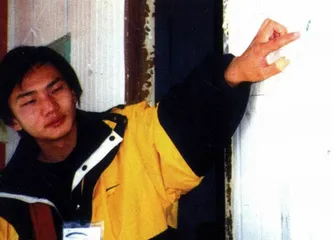
站长高兴(马飞 摄)
1997年探险家杨欣把他的日记出版,取名《长江魂》,用稿费换来了这4间房子,两间做宿舍,一间是工作室,一间最大向阳的用作展览室——挂着环保图片和羊角羊骨,还有个书报架,很多杂志都是一年以前的。屋子的显著位置挂着一张价目表:《长江源明信片》12张20元;可可西里保护动物图标一张20元;长江源画册280元……“保护站的运营就靠这些收入支撑。”现任站长高兴说。保护站有一名常驻站长,其余的是为期一月的志愿者,所有人员都不领工资,而高兴已经半年没下山了。
高兴们的日常工作就是观测动物,屋后有一座28米高的观望塔,每天写观测日记,在沿线的四川人与回民的小饭馆里张贴保护站制作的宣传画,所有宣传品都是汉、藏、英三种文字。“铁道部到这里来拿野生动物的观测报告,我们可以指出野生动物通道。”高兴告诉记者。保护站有一辆吉普,但每周只能发动一次,不能去远的地方,因为没有钱买足够的汽油。还有一部卫星电话,一般三天用一次,把日记和数据通过互联网发往成都的总部,一分钟的上网费是3元钱。湖南的志愿者乔军向记者抱怨,不远万里地跑来却不能跟野牦牛队巡山,“多一个人就要占一个座位,多带一份给养”。
即使如此,保护站依旧雄心勃勃,“现在还没有一份可可西里野生动物的详细资料。”杨欣说,“我们正在做昆仑山口到五道梁100公里内的野生动物活动习惯的数据统计。”但这一工作需要四到五年甚至更长,而他们十分需要专业人员的指点,因为至今为止,没有人知道青藏野生动物的真实状况。
五道梁、沱沱河:极限生存
“军车进藏五上四下,历时9天,现在快了,四上三下用一个星期。”司机王德强说。青藏线上最早的建筑就是这些保障运输的兵站,后来围绕兵站有了小饭馆和汽车旅店,形成了聚居区。五道梁与沱沱河沿就是最著名的两个。
“人到五道梁,哭爹又喊娘。”这是青藏线上苦得出名的地方。记者在这儿吃午饭,饭没吃完一阵冰雹就砸了下来。王德强说,他曾经送人到兵站,只上了一层楼,就头晕眼花耳鸣不止,下楼在路边喘了好久。“实际上五道梁的海拔不是最高,4500米左右。”格尔木铁路医院的医生赵跃青向记者解释,“但由于地处山口,大风不断,人的高山反应特别强。”
老板娘刘英是四川广元人,上高原已经八年了,腮上两块高原红,极像青海人,只是还保留着四川人的生意经——饭前送碟瓜子。半年前,刘英把老公也带了来。小店半个月到格尔木买一次菜,行程300公里。
向南100公里就是沱沱河沿,沱沱河河道宽广,但水流稀少,新的公路桥已经通车;按照铁道部设计,这里将修筑一座1386米的特大桥,成为长江第一桥。这个聚居点的名气不仅在于长江源头,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电话,与格尔木共享一个区号,400多公里——世界上最长的市话线路,如果要住宿的话,一般都会选择这里。
河的南岸有七八家旅店,主要是服务卡车司机的。山西老板晚上用柴油发一会儿电,以供应房上的一块霓虹灯招牌。9月底气温都在零下,屋里没有炉子,一路上主要的燃料是8元钱一袋的牦牛粪,还有黄乎乎掺着黄土的煤渣。寒冷是次要的,记者由于高山反应头痛欲裂,呼吸困难,躺在透风的屋里久久不能入睡。
青藏线上车辆繁忙,但旅店的生意并不好,没人愿意在高原过夜。

高原珍稀动物——牦牛(肖韦 摄/Fotoe)
安多、那曲:脆弱的藏北
唐古拉是青海和西藏的界山,山口海拔5231米,然而就在山口纪念碑的旁边竟有一顶小帐篷,住了一家藏民。由于语言不通,记者半天才问明白,他们是从安多县迁移过来的。记者后来从徐平处得知,由于藏区人口膨胀,很多更高、更严酷的无人区都有了居民。
汽车顺唐古拉溜坡而下,下到4700米左右就到了藏北第一县安多,说是县城,不过是江边几排房子。沿路南行135公里即到海拔4500米的羌塘高原重镇那曲,那曲藏语意为“黑河”,怒江从城边穿过,是整个藏北的繁华所在。青藏公路穿城而过,那曲地委书记公保扎西告诉记者:“未来的那曲火车站将是世界上最高的火车站。”
在街上走一圈,就会知道现在的那曲是一个什么意义上的城市。市中心是一纵一横两条街,羊群在街上大摇大摆,啃着绿化带的草皮。太阳出来后路边摆满了地摊,卖的是帽子、针线等日用品,常有藏民拎着一捆一捆的羊皮以物易物。最贵的是佛器,可以卖到一千多元,街脚处挂满了手织地毯,这是那曲目前最大的手工产业。目前90%以上的居民仍旧是牧民,而且大部分都生活在45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
原住民对那曲还有另一个称呼——“古嘎尔”,意思是帐篷,达赖时期每到夏天才会有政府官员来到那曲,住在帐篷里收税。很长时期以来,那曲一直是流放犯人的所在,环境恶劣,没有常驻官员;夏季围绕着孝登寺,会有一个短暂的盐粮市场。现在那曲还流传着一段佳话:那曲人民政府建立后,曾经悬赏种树,但至今没有人成功。当地藏民除了没见过火车外,估计很多人也从不知道树的长相。
从自然资源角度讲,那曲牧民条件远不如同样海拔的可可西里“39部族”。根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罗绒战堆的说法,“西藏各类草场的牧草单产只是青海同类草场的一半,西藏草场面积是青海的1.45倍,但牲畜总量只比青海多5%。如果和国外比,则更是天壤之别,西藏的一只羊产毛0.5公斤,而新西兰则可以产5.14公斤。在西藏养一只羊需要32亩草场,在新西兰只需1.8亩。”西藏草种稀疏、生长期缓慢,除了面积大外没有任何优势。
但即使目前这惟一的优势也将丧失殆尽。徐平走遍了藏北草原后发现了这样一些事实:很多牧民从低海拔的东部迁到了海拔更高的西部。以前一头牦牛的成熟需要5~6年,而现在需要8年,而且个头也在变小。牦牛被宰杀后,剖开胃里面一半是草一半是沙。“藏北草原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是超载放牧。”徐平说,“1960年以前藏北四十多万平方公里才养活十来万人,240万头牲畜。现在还是那片天那块地,却要负载34万人,740万头牲畜。整个那曲地区可利用草场3.87亿亩,退化沙化草场已达8000万亩左右,还在以每年15%的速度扩大,整个青藏高原的草场超载已达到60%以上。”藏北地区依旧是目前西藏最贫穷的地方,“那曲也曾经尝试搞工业,但皮革、牛绒、梳毛等工厂都没活下来。”徐平说,“没资金、没技术、没市场,只有依托青藏线的机修厂还不错。”
那曲地委书记公保扎西被人称作救灾书记,现在的那曲小灾年年有,中灾三年一次,大灾五年一次,频率是以前的一倍,每逢雪灾都有大批牲畜死亡。自然界用最简单也最直白的方式解决着人与环境的矛盾。
拉萨:工业还是旅游业
从那曲南行300多公里就是青藏铁路的终点拉萨。拉萨又称做“日光城”,但十一期间拉萨的游客却十分失望,因为七天只有一天出了太阳。“有一景叫‘拉萨夜雨’,拉萨人买伞不为挡雨只为遮阳,但现在白天也会下雨。”一位拉萨市民在茶馆中和记者闲聊。十一期间,徐凤翔也到了拉萨,出了贡嘎机场,她发现本是雪山融水的拉萨河已经开始变混,更严重的是河滩的沙子已经蔓延到山坡上,侵吞着草皮。
“除了全球变暖、环境恶化外,自然现象反常的另一个原因是拉萨已经成了一座工业城市。”徐平解释说。现在北京电视台当编导的杜培华1976年坐一辆普通客车,经过一星期土路的颠簸进了拉萨城,“那时候的拉萨几乎没有新式建筑,一色的藏居,没有现在遍布商店和摊贩的大昭寺广场。布达拉宫前一条简陋的街道直通到大昭寺,从郊外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布达拉宫,印象神圣,上空老有阳光穿过,如同一支追光灯跟在布达拉宫上方。”而现在的拉萨已经拥有电力、煤炭、机械、纺织等十个行业百余家工厂,八角街上卖的很多是工业品而非手工艺品。
但问题是,工业化并没有取得满意的成果。“在西藏办厂,办一个亏损一个,这都快成一个常识了。”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所副所长丹增纶珠告诉记者,“效益不错的只有林芝毛纺厂,那是上海的技术;再就是藏药,别的地方没有。”中央党校副教授靳薇最近所作的一份《援藏项目效益调查报告》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在105个援藏项目中大部分企业都在亏损,数额最大的昌都水泥厂3年亏了2000万元,公用设施日喀则自来水厂每年亏损200万元,即使西藏的优势项目——扎仓茶卡硼镁矿也亏损了259万元。除了交通、技术、资金等问题外,最大的困境就是没有市场。“西藏的现实情况是,87%的人口是农牧民,分散居住在高原上,而且大部分地区的农牧业还停留在运用肩挑、背驮、镰刀、锄头和二牛抬杠的手工劳动阶段——这就是说87%以上的西藏人口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藏学家格勒说,“从收入水平来看,1997年占总人口87%以上的广大西藏农牧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只有1085元,而他们大量的收入又花在宗教上。”从外部市场看,拉萨到西部最近的消费城市成都和昆明的距离都在2000公里以上,到东部任何一个消费、工业中心或是出海口,距离都超过了4000公里。
另一方面,工业给高原脆弱的环境却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拉萨西郊的居民曾抗议附近的登峰水泥厂使他们生活在灰尘之中;林芝的森林在大量消失。丹增纶珠曾亲眼看到,为了开采铬铁矿,一座座山头被削平,巨石被直接推进峡谷中的怒江。徐平将飞舞在狮泉河镇上空的塑料袋称作“怪异的风筝”……丹增考察阿里时,看见圣湖玛旁雍错边修了一座金矿,“震耳欲聋的抽水机日夜不停的将湖水引至厂区,工厂又将废料直接投到湖里,要知道玛旁雍错可是佛教、印度教、苯教朝拜的圣湖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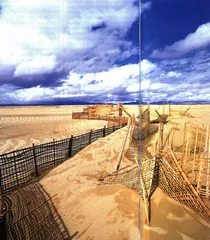
高原防沙带。美丽的高原与恶劣的环境,总让人感叹(滕科 图)
开发西藏的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重新思考什么应该是西藏的第一产业。“青藏高原只有一个,布达拉宫只有一个,喜马拉雅只有一个,这些都是不可替代的资源。”徐平说。而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如果西藏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能得到比较大的改善并具备年50万人的接待能力,中国政府能够放开西藏的旅游市场,10年后西藏的旅游业将成为仅次于大农业的第二大产业,每年可给西藏带来近4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20年以后,西藏这一只有40年历史的新兴产业将成为西藏最大的产业。40年以后,如果西藏的人口总量能控制在400万人以内,西藏完全可以依靠旅游业使其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达到现在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遗憾的是2000年进藏旅游人数是50万,而四川九寨沟的游人也是50万。
西藏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九五”期间已完成投资9081万元。记者从西藏旅游部门得到的项目明细单上,13个景区的开发投入已达到了12.8亿元:樟木口岸要建空中索道,珠峰要建眺望台,一条200公里的公路修到阿里的神山圣湖,即使是只能走牲畜的茶马古道也计划修一条350公里的观光柏油路……而旅游带来的问题可能也是触目惊心的。徐凤翔今年考察时看到的景象是:一条宽阔的四条车道公路直通纳木错,湖边的草皮被翻起,还有一个排戏的剧组留下了一地垃圾;惟一的厕所还被锁起来供导演用。而在生态保护站的大本营林芝,很多林区胡乱圈地,为了拉到项目谎报树龄。旅游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基础开发的破坏力,大量旅游者涌入使藏区简陋的城镇不堪重负。“那曲河边有很多废旧塑料袋,就像北方的农村一样,阿里首府狮泉河原先有一片红柳林,现在没了,人口的增加都烧掉了。”徐平说,“实际上,除了拉萨和林芝,西藏的其他地方都没有雨水排泄系统,大部分城市都只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处理垃圾和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