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夏季的渥勃根湖》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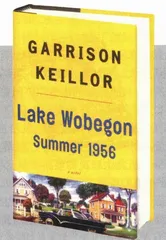
本期上榜新书虽有七部之多,我们在这里先介绍一部,那就是加里森·凯勒的《1956年夏季的渥勃根湖》。
故事开始不久,作者就对从童年到成年的突然转变做了一番精彩的描绘:“我在11岁以前是个非常好的男孩,“名叫加里的叙述者这样讲,”大家都这么说……人们常常把我指给别的孩子,拿我当作一个模范。‘你为什么表现不像加里呢?瞧瞧人家,他在祈祷会上一点不像被网住的鸟一样,动来动去的,他坐得笔直,好好地听,并且能从中学到点东西。”
“随后,在1953年的一天,爸爸告诉我把一口袋垃圾倒进垃圾箱,我脱口而出:‘噢,见鬼去吧,’……我听到我的这句话,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简直就像打喷嚏似的,自个就憋不住迸出来了,‘噢,见鬼去吧’。一团漆黑一下子就笼罩了大地。”
11岁就成年,是早了一点;不过,正如加里自己提醒我们的,他是早熟的。到他长到14岁那年夏天——这正是全书点题的时间——他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十几岁的少年,成年人通常着迷的事情他已应有尽有了;随着性成熟,他对姐姐、父母都有了新的内心想法,他参加体育活动、热衷滚石乐,如此等等。用加里自己承认的说法,他在与人打交道时不在行,在身体上却给排除到了该去的地方。而最糟糕的是,他的样子看着“如同被变成男孩的树蛙,但变得并不完整”。一句话,他是让人讨厌的蠢才。
目前西方有一种趋势,所有的媒体都乐于报道十几岁少年的我行我素;这种有关少年成长的小说其实也不少。单以加里森·凯勒而论,早在他未写小说前,就创作和主持过一个公共电台的节目,名叫《草原之家的一个伙伴》,深受欢迎,场景就是凯勒杜撰的明尼苏达州的叫渥勃根湖的城镇。如今这里又成了加里的家乡,自是能让读者对这已然不陌生的地方,再增加一个成长中的男孩的身影。
加里是个极其敏感的男孩,他一心想长大,到时为《纽约人》杂志撰稿。然而他毕竟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正因如此,他总是一味喋喋不休地谈论他自己,而绝少提及渥勃根湖,反倒是大谈特谈他与其表妹凯特关系的破裂,因为凯特爱上了当地棒球队的本垒手明星。还有人们更不一定要听的他对当地摇滚乐队“小摆设”发表的种种议论。
当然,《1956年夏季的渥勃根湖》确实写出了一些令人难忘的时刻。例如,加里有很长一段时间忘了他自己,为我们洋洋洒洒地回忆,回起他早年在祖父的农场上度过的一个夏季,当时他父亲在军队服役,母亲则在纽约城上班。再如,“小摆设”乐队在7月4日美国国庆典礼上的演出,那真是个狂欢的时刻,当时“他们拖着最后的大弦音,然后又抑扬有致地转到下一个音键——人群要是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北欧成分的话,他们一定会跳起来、高声尖叫并且分散成一团一伙的了,可是他们既然都是些聪明人,就按着旋律轻轻鼓掌,直等到‘小摆设’演唱完那支歌曲,才又鼓起掌来,演出结束了,这才到了欢呼的时刻”。
这段描写完全可以看作直接取自作者的那个单人表演节目《草原之家的一个伙伴》。在那个类似我国小说连续广播或单口相声的电台节目中,凯勒每周一次给大家播放连续故事,不时插进一些令人捧腹的笑话,竟然有了一批着迷的听众,到时非听不可。但在这部小说中,读者却难免要看着钟表,来等候加里长大。
两相对比,评家有一段中肯的论述,对我们如何看待听广播和读小说(尤其是在当前这个人人忙碌的时代)颇有启发。一位评家认为,凯勒的连续广播之所以大受欢迎,而他的小说却显得冗长(约17万字,至少长于当年同类描写青年少成长的《麦田的守望者》),其原因在于:首先是凯勒的那富于音乐性的男低音,柔和且善表达,动听悦耳,而小说却缺乏这种备受欢迎的感染力;再者,听广播时人们可以同时做别的事情,在厨房做饭、等水烧开,甚至可以在驱车购物的路上,在聆听来自渥勃根湖的趣闻轶事的同时,开心地一笑。而阅读文学作品时则只能专心致志,难以一心二用。如果故事情节枯燥,读者便很难被吸引了。
加里森·凯勒先生是否有类似威廉·福克纳把家乡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镇虚拟为杰弗逊镇,从而写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的宏愿,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对自己杜撰的明尼苏达州的渥勃根湖的确情有独钟。他在成功地在电台播放了《草原之家的一个伙伴》之后,在这本《1956年夏季的渥勃根湖》小说问世之前,还出版过一部《寻找渥勃根湖》。那是一本图文并茂的照片集,前言和文字说明由凯勒写出,而质朴动人的黑白照片则出自摄影家理查德·欧森尼乌斯之手。这部优美的影集展现了明尼苏达州的城镇、农场和草原的风貌,加之凯勒富于魅力的文字,确实引人遐想。恐怕正是出于播讲和影集的成功,才激发了作者在此背景上再写一个孩子成长的小说:让自然景观衬托人的生存和人性的发展,让人的目光看出自然的优美与雅静,构成一幅自然与人的真实画卷。 文学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