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求诸野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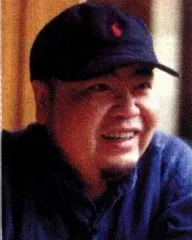

吃野菜这事,看来也已经被罗致到了“崇尚自然,返朴归真”的门下,并且与“住在郊区”和“野外生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成为时尚产业里的朝阳。然而,那些爱吃野生动物的人不知会不会觉得自己多少有点冤:为什么进食野生植物是时髦,是健康,是绿色,而进食野生动物者就成了过街老鼠,惨遭千夫所指呢?
即使这些“过街老鼠”自个儿并不这么觉着,我也会替他们抱打不平。就饮食行为而言,进食野菜和进食野生动物一样,都具有“食野味”的心理动机。站在生态保护的角度,吃野菜固然尚未能直接导致某一物种的灭绝,却有可能对生态造成更为严重的破坏。目前各地所开发野菜大多是以利用现有的野生资源为主,而市场上居高不下的野菜需求则已开始对个别地区的天然植被、尤其是盛产沙葱、野韭、蕨类、百合、桔梗、苦菜、黄花、蘑菇等多种野菜的草场形成致命的威胁。此外,因有多种野菜的生长期较长,例如餐馆里常见的桔梗,其生长期长达三至五年,若不加限制地大举采伐,不仅资源很快会消耗怠尽,生态环境的前景更是岌岌可危。发菜曾经就是一种我们酷爱的典型的野菜,结果怎么样?大家心照。
在“绿色观念”的感召之下,还有一些城市居民已不再满足于在餐馆里吃,超市里买,甚至还举家出动,亲自到郊外的绿地去挖。据报道,今年春天,在济南市的大小公园里竟有人“拿着塑料袋和小铁铲,在草坪里挖荠菜。据他们讲,这里的荠菜很‘鲜’,比在市场上买的味儿还‘正宗’”。另一则不幸的消息是:云南某地王姓村民因在野地里发现一种“长得像野菜的东西”,遂“摘了不少带回家中,拌上白面炸成面饼”。一小时后,吃过面饼的八人相继被毒翻在地,送到医院,才发现误将大麻做了野菜。
当然,为了捍卫我们所热爱的绿色生活和我们在口舌上的不懈的追求,已有一些研究机构对多种野菜品种进行了筛选和驯化,据称很快就可以有人工培植的“野菜”大量应市了。不过,我很怀疑此等“野菜”终究是骗不了精明的消费者的。已经有不少“菌友”对哪家餐馆卖的是真正的“野”山菌而哪家卖的又是人工培植的“假野山菌”了如指掌,并且以此来指导他们的消费行为。因此,我悲观地认为人工培植“野菜”的命运也将是一样,即使逃过了人民群众的法眼,终究也躲不过“法舌”的审判。毕竟,我们追求的就是一个“野”字。
一般来讲,进食野菜是一种被迫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不出以下两种情况:第一,饥荒;第二,赌气。
每遇饥荒,哀鸿遍野,灾民们但求裹腹,别说是有汁有叶的绿色野菜,就是树皮也得无怨无悔地咽到肚子里去。除了饥荒之外,青黄不接的时候,野菜亦是一种习惯性的“救荒本草”。虽然也能活命(当然也有不少饥民因吃了有毒野菜后而毙命),终究是活得“面有菜色”,总而言之,那只是一种不得已而食之的权宜之菜。
第二种情况,通常指的就是著名的伯夷和叔齐这哥俩。为了和周武王赌气,不但发了誓不食周粟,而且一气之下跑到山里躲了起来。吃什么呢?既然做了“野人”,当然得吃些野菜,于是靠山吃山,采薇而食,并做《采薇歌》为进食之背景音乐。薇是什么?《尔雅》说那东西就是蕨,也就是我们今天在饭馆里经常吃到的所谓“野生蕨菜”,通常是凉拌。历来也都有人坚持薇是薇,蕨是蕨,不过,这些考证都是基于首阳二老的忠贞程度,与吃食无关,对于我等来说,管它是蕨是薇,“野”的就好。
当然,包括蕨、荠、鱼腥草、香椿及马兰头在内的有一些野菜还是可以吃的,最起码并不难吃,不过终究是不得已而为之,“得已者”则偶尔一尝不妨,至于用搞运动的方式去吃野菜,甚至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地到郊外或公园的草地里去DIY,那就是做作。其实这种风俗过去也是有的,事见周作人《故乡的野菜》:“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关于荠菜向来颇有风雅的传说,不过这似乎以吴地为主。《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齐菜花。谚云:三春戴养花,桃李羞繁华。’……但浙东人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
今之野菜爱好者不仅馋痨,亦也大有附庸“绿色”之风雅的意思,但毕竟已是时过境迁,“集体采薇”即使一时破坏不了生态,却也非常地有碍观瞻。这种事现在也就算了,最多也就是“挖社会主义草地”,要搁“文革”那会儿,怎么着也得给丫扣上个“抹黑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帽子戴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