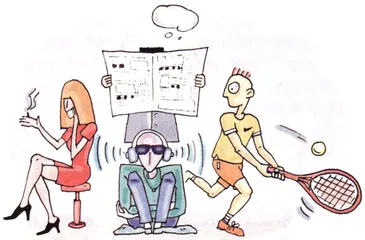关于小资的小学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小资”,许多年以前和许多年以后都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它的兴衰过程也惊人地相似:红极一时,紧接着就更多地被用来骂人,例句:“说谁呢你?你丫才小资!你全家都小资!”
“小资”基本上是一名词,但现在也经常地被用来作形容词,例句:“这个小资很小资”。作为一个缩略语“小资”的完整的读法是“小资产阶级”,既资产,又阶级,严肃得很。所以,这个来自法文的名词在上世纪初被译成中文之后,一直都在革命的语境和斗争的泥浆里残酷地打滚。关于“小资”的最权威定性和分析,是毛主席在1925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中国社会里的小资产阶级。
怎么样,还可以接受吧,但也别高兴得太早,因为毛主席同时还指出,手工业主和自耕农也属于中国的小资阶级。郁闷吗?尽管如此,就中国家庭成员在身份上的多元性而言,“你全家都小资”在这个意义上还是完全有成立的可能的。
事隔将近一个世纪,毛主席在1925年对于小资的分析仍然是基本有效的,由“学生界和中小学教员”构成的小知识阶层现在仍是我国小资阶层的中坚。当然,毕竟是年代久远,其中难免会有个别名词有更新的必要,例如“小员司、小事务员”之类,换成今天的话语,就应该统称为“白领”。至于多半都没有读过玛格丽特·杜拉或者村上春树,也不喜欢听约翰·列侬,不爱看王家卫的自耕农,为什么竟也跻身于小资阶层?You ask me,me ask who?
其实,小资与其说是一个阶级,不如视其为一种状态,换句话说,当“小资产阶级”被读写成“小资产阶级”时,它就是一个阶级;而当“小资产阶级”被缩略为“小资”的时候,它更多的就是指一种状态,一种情调。从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来看,毛主席认为,一切小资产阶级都是革命“最接近的朋友”,这说明毛主席并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毕生都仇恨小资。事实上,毛主席仇视的是小资的情调,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事不对人的,小资情调才是革命斗争的大敌,是一种“最臭”的“情调”,臭过“农民脚上粘的牛屎”。此外,小资情调也被形容为“一条尾巴”,而且是一条经常“翘”起来,很难不翘,很难割除但是又必须割掉的“尾巴”。例如,毛主席就曾经骂过江青:“小资产阶级尾巴没割尽。”
虽然也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尾巴”的意思,但是前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的表达没有这样优雅了。我曾在一本野史中读到,高岗在东北局的一次干部大会上提醒大家要时时刻刻注意克服自己身上的小资情调时这样说:“小资情调就像一根鸡巴,动不动就硬了起来。”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尾巴没割尽”的人,感觉上会有点像一个没有剃光头发的出家人或者一个没有阉净的宦官。在今天这样一个和平年代,一个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年代,一个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的年代,一个城乡差异逐渐缩小的年代,一个知识经济的年代,所谓“小资产阶级”其实已与一个人的资产、身家以及由前者所决定的政治立场无关,“小资情调”也更多地转变为一种消费方式和消费形态,概念化的“情调”正在转变为对现实生活和自我的“调情”。这种消费型态的惟一作用是明确小资和非小资之间的识别,划清小资和非小资之间的界线,小资必穿的服饰及其品牌,小资必看的电影及其DVD,小资必下的馆子,小资必上的网站,小资的必读书,小资必看的电视频道,等等。必须承认,这些东西都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强制性。只是小资情调中最重要的一项,即“小资必泡的马子”,却是非常的乏善可陈,因为小资必泡的马子,通常都是另一个性别的小资。
尽管我们通常都很好大,但是“小资”却实在不宜“搞大”。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小资”是一种相对安全的状态:有一点资产,不多,但是绝不像“大资”那样以剥削它人为乐为生,可以选择被剥削,也可以选择自己剥削自己。美学家鲍姆嘉通有这样一句名言:小就是美。看来在资产阶级的问题上,这个原则也一样通用,资是小的美。无论如何,千万不要像香港的中产阶级那样,亚洲金融风暴之后,这些有车有楼的资产阶级的正资产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负资产,自己也因而变成了“负资产阶级”,如果说他们还有翻身的机会,毫无疑问,那就必须从“小资产阶级”重新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