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164)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何冬梅 闻亦 李大丙 武嘟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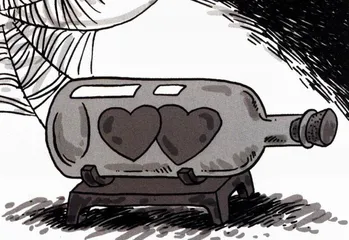
他和她
何冬梅 图 谢峰
他和她已相识八年,抗战都够了,但两个人依然是朋友,没有多一步,也没有少一步,比朋友近点,离恋人远点。这八年间,他结婚出国,她离异分居,期间有三年的时间声讯全无,谁也没有刻意联络过谁。北京这样大,他和她却没有对方的住址与电话,就这样,淡淡地,偶尔会想到对方。
春天时候,在国贸地下的精品店,她看见了他,他高高的胳膊上吊着一个眉清目秀的长发女子。她想躲开,他却看见了她,惊奇地叫了一声她的名字。三年弹指一挥间,他没有什么变化,她却从一个热衷于幻想和做白日梦的女孩变成一个眼光犀利眼神坚定的少妇。匆忙间他丢下手机号,而她却没有想记住。
就这样又过去了。夏天时候,她在三里屯的一个酒吧里若有所思地等人,他进来了。酒吧里流淌着《卡萨布兰卡》的旋律,她记得男主角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的酒馆,她却走进了我的。”有时候缘份这东西是不能不信的。他和她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这以后他和她吃过几次饭,喝过几回茶,大家分毫不提各自的私生活,仿佛小心翼翼地绕开脚下的地雷。其实相遇了也本没有什么,只是两个人坐在车里,在漆黑的夜里,在飞驰的高速公路上,默然无语,只觉得气氛怪怪的。她能看见他眼里的亮光,他也能看见她的。但是他和她什么都没有说。
秋天开始的时候,他就多次袭击她凌晨的梦境,毫无道理可言。而凌晨总是她最脆弱的时候,免不了偶尔会落几滴清泪。但转瞬即逝,她依然会神采飞扬地去公司,没有人能够看见她的梦,也就没有人能看见她的苦。
他和她去过一次商场,售货的小姐眼毒,看出他和她的默契,以为他们是恋人,只有他们两个知道,实在是连对方的手都没有拉过。在这样一个污浊的世界里,他和她都是冰雪聪明,懂得把幸福留在想象里会更美妙。她也知道萌芽里的爱用不着伤筋动骨,拔刀见刃。但到底是心有不甘,偶尔也会情不自禁,压抑着,沉闷着,梦里的相见多少令人伤感。小女子莫文蔚在那厢唱道:“等一世为看一眼,如何又算贪,得不到,也不甘,怨亦难……”
她一直记得张爱玲的小品《爱》,她一直有这样的一种冲动,想把这篇小品复印下来,传真给他,什么也不说,就这样就足够了。
Bra当道
闻亦
胸历来是个禁区,Bra就是女人身体的最后一道防线。最精简、最概括的表述应该是这样的。
可问题并没那么简单。面对乳房,人们很难不受到与生物倾向一致的形象诱惑。而Bra作为乳房一部分的附属物被引入文化的轨道,它就绝不仅仅是哺乳器官或是欲望表达这么坦白,其深暗的程度会没完没了地加深。
从文化功能学来解释,Bra的设计,是为了表现对男性的“遮蔽”和“拒斥”,而Bra的魅力又在于“表现”和“显露”。遮蔽、表现,投怀送抱、置之不理,相逢、别离……这些都是看似矛盾的现实和词语暗寓了巨大的诱惑在里头。能够兼容地表达出这种矛盾,这是服装设计中最具难度的地方。而Bra几乎同时完成了这些含义,制造寸步之间肉体的距离,释放了身体真实而暧昧的诱惑。
Bra的神奇正在于,它真正发掘出了也让女性自己意识到了“乳房”的戏剧性力量。
现在的状况是:身体形象有了更突出地位并无所不在,被欲望纠缠不休的乳房,在被当作自己的消费对象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注视目光。与此同时,窥视的机会也随时可寻。就有人搜集舒淇、李丽珍出道时的三级片,然后,用X光镜的眼光去透视在广告和影片首映的新闻发布会上熠熠生辉的这些女人。
于是,专门有人拿Bra说事。陈庆嘉及梁柏坚像模像样地作了个Bra秀《绝世好Bra》。极尽铺张地用了上千个品牌的Bra作道具。人们对这部片子的诉求点是不一样的:女人关心的是,两个男人在Bra堆里的表现;而大多数男人的问题是,刘嘉玲和GIGI会不会以Bra出镜。两性之间对隐私窥视的互相期待被消费文化的制造者所利用。
片子很扯淡的地方是反复强调Bra品质质地的差异,有让人很反感的广告痕迹。我始终不相信两片布能够创造出上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差别。这可能要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来想象:Bra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产物,它的所有形态都讲述着其社会身份,只有在此思路下Bra具有了政治性,劳动阶级和有闲阶层才有了不同的身体标识和审美倾向。
要是按福柯的路数,就会把Bra说成是分类知识和权力的产物。不过也有另一种语境可以进行合理性的解释:《纽约邮报》报道,一家专门拍卖好莱坞影星及美国体坛运动明星纪念品的网站,推出了麦当娜早年出道时穿过的性感黑色蕾丝Bra,当天便有高达5000人次的网友造访,麦当娜的胸罩16日以1200美元开出,次日价格便飙到1453美元,20日竟以13800美元成交,是起拍价格的10倍之多。而天价Bra和质地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主要是因为记录了麦当娜的“汗渍与粉底印”。
到英国去
李大丙
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有本不起眼的小说叫《到莫斯科去》,大意是一帮有为青年去苏联求索革命的真理。当代文学中同样有篇不起眼的小说叫《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是讲一帮人怎么要去美国留学。估摸着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写“到英国去”,讲雅思考试和伦敦,讲英国乡村和苏格兰高地。
前两天有个兄弟打电话告别,说他要去英国留学了,担心那边不安全,“打起仗来别受什么恐怖袭击”,还担心疯牛病和口蹄疫,越说越热闹那么危险的地方还去干嘛?要说这帮假洋鬼子装孙子,那是踏出国门就开始的。回来之后有人病情加重,一哥们儿说他最受不了的是街头那些红底白字的标语。没事儿就扯几尺红布,白色方框字,多漂亮的东西,可他看了不舒服。
有个妹妹在瑞士留学,当年办出去的时候就是学酒店管理,也就是报纸上老揭露的那种野鸡学校。到那儿学了半年,就给发到中国餐馆里打工,好几年了,她就一直在端盘子,打工之余学德语,学完德语学法语,就是不肯回来。我打电话跟她说,就她这条件回北京也算个人才,我们这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会英法德语,还有当年的经济学位,怎么也是白领,干吗在那儿端盘子。这位妹妹说了,尊重知识没错儿,但尊重劳动更重要,我在这里的餐馆听不到大声喧哗,每个客人都细声细气,我不觉得低人一等。尊重人才也不错,可尊重人是首要的,我在这里认识的都是贫下中农,可他们每个人都很快乐。她说,她在瑞士端盘子不同于河南姑娘在北京端盘子,她愿意保留自由舒心的权利。
有个文艺女青年,当年投身艺术事业没顾得上好好学英语,如今信誓旦旦要考雅思,从《新概念》第二册学起,坚持了半年多背下96课课文。我问她是不是想看看《风雨故园后》拍的那个英国,看看格林《布莱赖硬糖》里描绘的海滩,看看诺丁山。没料到文艺女青年根本没这些想法,她说工作8年,有枯竭的感觉,人都被榨干了,干什么都没兴趣,所以不妨到英国看看,寻找生命第二春。
另一个商界男青年不去英国,张罗着移民加拿大,问他这边赚钱好好的,干吗要去那地广人稀的地方,他说他要为自己的下半辈子打算了,在那边投资在那边交税,享受那边的福利。
瑞士那个妹妹,在餐馆里接待过一帮来自祖国的干部,去那里考察的,她说看见这些人就暂时还不想回来。也许有一天,我有20万块闲钱,也跑到英国去学莎士比亚的戏剧。值得庆幸的是,这梦想不难实现,想走的时候也就走了。
火车带着车票来
武嘟嘟 图 谢峰
我父母非常喜欢听《常回家看看》,可我总觉得歌手在重复“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时像唐僧念紧箍咒,头疼得很。不是我不想回家,而是火车票问题。家长喜欢过节全家人挤挤挨挨地坐在饭桌边上,所以几乎每个节日我都要回老家,大小不论。以前有男朋友时还好说,他踢足球的,身高力壮,喜欢跟人口角时“呼”站起来俯视着对方。每次买车票,他在里头挤我在外头看,总能买到。现在没有男朋友了,我得自己买票了。
“十一”到了,楼下的小订票点繁荣起来,里头的服务人员也高傲好多,最爱说的话是“没有了,都没有了”。我只好等了两天才回家。到家时爸不在,说是给我买回去的车票了。自然是没有买到。为了让我安心,爸去找了一个票贩子,还另找了一个作后备。后一个票贩子跟我们说没有必要找前面那个人了,他没有本事。我是让后一个票贩子领进火车站的。
我以前也跟票贩子打过交道,手续很简单,我给他钱,他给我票。但这个票贩子的做事方式完全不一样,她是个短头发女人,跟我保证肯定有票,但在火车上,而且她已经先交了钱。我怎么都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她说不清楚,但保证先给我票再收钱。她带着我从一个“闲人免进”的小门进去,然后对我说:“你跟在我后面走,但不要跟我说话。”
我在站台上站着,她在5米远的地方。我在等她,显然她在等别人。一会果然有人来,是一个长头发女人,拿着手机。两个人说了几句话,然后一齐等另外的人。我周围拿拖着行李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性质显然跟我一样,因为他们不错眼珠地盯着那两个女人。
火车就要进站了,我还没有看到车票,不禁很是心慌。两个女人倒是一副神闲气定。火车轰轰隆隆进了站,我不知道往哪头走,该上哪节车厢。正在困惑,两个女人不见了,裹进一堆人中,中间是一个穿着铁路制服攥着一把车票的人,是那种手写的。我忽然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火车到站前,列车先统计有多少个空铺位,根据票贩子提供的需求量(一定是通过手机)事先把票开了,车一停把票立即给票贩子,票贩子立即给我。我捏着票上车,为他们这种繁琐的手续多交了40块钱(我知道不对,但我要回去上班)。
这样的发现让我格外不快活,以至对面铺位的老头给我表演对好魔方的六个面时,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就看见一片黄,一片绿,真是眼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