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消费主义的九十年代 辛酸的乐观主义 一个人的90年代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艾丁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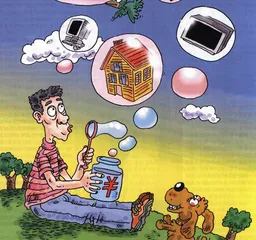
(漫画:谢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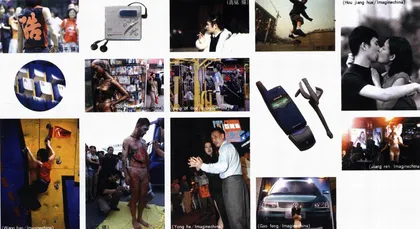
据我所知,“90年代回顾”这个题目是《三联生活周刊》为他创刊7周年纪念准备的封面故事,因为“9·11”纽约恐怖事件,它被挤到了里面。然而通过纽约恐怖事件,则可以从一个侧面来打量我们这些年的变化。9月23日的报纸上,有这样一条新闻,说中国正成为经济上的避风港,国际资本觉得这里安全,少受外界风波的影响。9月11日那天晚上,我太太看完电视新闻问的一句话就是:“咱还换美元吗?”第二天,北京外汇市场上美元没跌,还略有上升,专家们说这是我们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造成的。专家们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全球股市都下跌,唯有沪深两市挺平稳,中国入世是怎样一个利好消息。可他们说的这些我似懂非懂,我只知道一个哥们儿在9月12日早上去买了齐鲁石化的股票,他说,美国一折腾,石油价格就得上涨,石油企业的股票就会升。当然,我这里想说的也不是理财问题,我只是感觉到我们正越来越多地成为经济动物。
5月,沪深两地的资本市值超过香港,中国大陆从而成为亚洲第二大资本市场,仅次于东京。英国《经济学家》网络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大陆股市规模大只是个神话,里面有许多不可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中国大陆中小投资者也没想象中那么多,起码有3000万个账户是假的。这篇文章还给我们开出了药方,怎样监管怎样完善。对这些我也不感兴趣,金钱游戏的参与者都相信自己的技能,他们知道游戏场哪些地方是歪的,向哪儿歪,歪到什么程度,这就得了。我不炒股,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我傻我懒,炒股的人不管英国《经济学家》怎么说,他们看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消息。
不过,我理解外国人的冲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过:“贸易是一些平等的人们之间的职业。”可外国人做买卖也不是为了促进平等,权力在我们这里算最有价值的商品,哪个外国公司不是来利用这一事实而是要来改变这一事实的?
1993年,上海大众的一个经理彼得·托普说过:“中国的劳动力是不值钱的。”没错,我们在21世纪将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财富像它过去一样牢牢地植根于劳力劳动、苦力司机、苦力店员和苦力产品的买者。这也许就是中国经济飞跃的一条最重要的理由。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始,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9%,世界银行预测,照这种增长率,到2002年,如果中国不是最繁荣的,那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这数字和预测都可以调整,谁也解释不清楚些许的高速意味着什么,但总而言之,我把它称为“乐观主义”。它只传达一个声音:我们要走向富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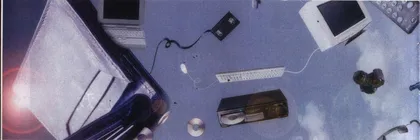
北京申办奥运会时有个口号叫“申奥有我一份”,申办成功后,各种“北京要富了”的分析此起彼伏。有一天晚上我跟几个朋友喝啤酒的时候把那口号改成了“奥运有我一份”,那意思是北京要花那么多钱,要流动那么多钱,我怎么能花差花差挣上一笔?外国人恶意地评价说我们“在许多方面像印度的经济,是行政管理的经济,这种经济注定叫看门人富起来,而以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牺牲作为代价”。他们说,这一体制的刺激是明显的:如果你无法避免去生产,就必须去生产。你得自担风险去消费。但如果你能够的话,就去做一个看门人。
我有个朋友在银行的信贷部门工作,不知道能不能算个“看门人”,他大概是个科级或处级干部,他说:“我的两个前任都已经进去了。”外国人挺玄乎地说什么“看门人”,跟他们该怎么解释“进去了”——就是进监狱了,搞腐败结果被反腐败了。有意思的是我也不关心反腐败,抓一个就抓一个,还有更大的。经济市民社会要确立起来,是相信自己不当看门人也能“有我一份”,这可能是苦哈哈挣来的,但有这样的机会就足以让我们庆幸。我们忙着抓这个机会,而对于制度缺陷忽略开来,这就是乐观主义。如果我们自怜自艾一点儿,我们说这叫作“辛酸的乐观主义”。
这样絮叨了半天,我才总算找到一个词汇来描述90年代的情感。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特意翻出来《伊甸园之门》,这本书讲60年代美国文化,作者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感。合上这本书,我想了想自己——90年代初,我从大学毕业,按常理说,我那时候该停留着一些所谓的理想主义激情(隔了这些年,我也忘了那时有没有这东西),按照讲故事的逻辑,这些理想主义激情该逐渐消亡(我也不记得它是怎样消亡的了)。然而,消亡的东西有什么好刺激的。我只记得1993年给我的刺激,那一年北京街头忽啦啦出现了一大群地摊儿,“下海”和“第二职业”成了热门语汇,这两个词如今也生疏了,可那些“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般的地摊还在我脑子里闪现。大家都要做买卖了,可谁也没什么俏货,所以地摊上最常见的商品就是拖鞋,满北京的拖鞋那才叫直观叫刺激。
顺着这800万双拖鞋,我才记起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想起上海也被划为沿海开放城市,想起1992年政府才批准“下海”运动,想起1993年一群经济学家提出了“股份合作制”。也就是说“第一次使财产权的多种形式合法化,但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任何形式的财产权”。1994年呢?我就记得世界杯决赛巴乔把点球踢飞了,中国足球搞了个“江山”会议,职业体育、足球俱乐部、市场化这些东西粉墨登场。
“新的时代到了,再也没人闹了。”大家越来越自觉地采取一种实用主义态度。
“我们正走向温和宁静的沙漠,在那里,人类将不再有道德激情和精神烦闷……人将不再是堂吉诃德或是浮士德,他们将成为自动化文明世界驯服的仆从……人的气息将为饱食后的虚无主义所代替。”这种知识分子的抱怨看起来像无病呻吟。裹挟在90年代这十年的一大主题就是更多的人在实际地关注,如何才能成为精神贫乏的中产阶级。事实上,没有谁有资格过问别人的思想,用一种乌托邦的腔调麻醉别人。如果说个人财富的积累是最实在的,那么别的东西自然可以被怀疑,我们的种种不幸就在于怀疑的东西太少,太容易信服于某种思想体系与权威。虚无的90年代至少让我们明晰了一个概念——财产,以及财产背后附带的种种权利,这个权利意识不觉醒,别的启蒙就是隔靴搔痒。
说到这里,90年代似乎又可用“实用主义”或“虚无主义”来描述,但我还是觉得“辛酸的乐观主义”更恰当,它表明一种“向前看”的态度。这个社会将变得更美好一点儿,个人的机会似乎更多一点儿,大家好像更平等一点儿,我们有理由乐观,但念及我们无力改变的丑恶与不平等,念及正义与自由还没有伸张,一股辛酸之感涌上心头。 九十年代经济消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