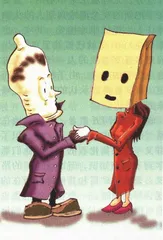思想工作:戴套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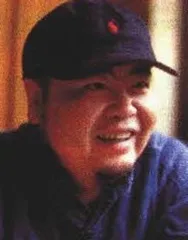
除了“下班回家”、“上饭馆点龙虾”及“给小姐留号儿”之外,民间语文“四大傻”的第二项,便是“手机戴套”。隐藏在“四大傻”里面的玄机,并不尽限于音韵和修辞,其中第一、三项和第二、四项各为一组,隔行呼应,也就是说,将“上饭馆点龙虾”跟“给小姐留号儿”编列在同一组别,系因其在行为上都具有奢侈、铺张或张扬的特征,并且是破坏游戏规则的。而“回家”与“戴套”之所以同组同构,显然是由于其行为上共同的收缩性和保护性,是相对内敛并且遵从游戏规则的。
两组截然相反的行为方式之所以被归纳为“傻”——即社会化的行为禁忌,也许并不在于张扬和内敛之间高度的对立和紧张关系,而是因张扬和内敛在尺度把握上的失当,即不恰当的张扬和过度的内敛。集体性、程式化的失当,构成了一切俗套的共同本质。当然,与人类的天性相比,过度的内敛总是显得尤为特殊,不然的话,莫罗亚可能就不至于把普鲁斯特的那种天才而奇特的写作方式称之为“逆向的哥白尼式革命”。因此,有许多品行端正兼且举止得体的认真人士在听过了“四大傻”之后最不服气之处,都集中在自己从来不给小姐“留号儿”的手机,何以一套就俗了呢?
保护几乎是套子的惟一功能,但是,这种套路其实是一个变量,在不同的参数下会显现出不同的意义。物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套子对被套主体不仅起到了防尘、防水、防磨擦这“三防”作用,与此同时,其对主体所能起到的“强调”作用通常还会暂时遮蔽了保护的初衷,更像是一种将价值向外延伸的饰物,在手机套之前后,我们已经有过钢笔套,包书的牛皮纸,罩着黑白电视机的绣花绒布套,大气层之于地球,建议中的玻璃钢罩之于颓坏中的乐山大佛,等等,一套一套的。
又如,按照我的习惯,在这个段落里必定是不会放过契诃夫的,在全中国只有汝龙和沈宏非两人读过契诃夫的假定前提之下,恰到好处地对《套中人》进行援引以及套用,就可以使本文增值。
套在玻璃瓶下半截的那种网状玻璃丝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个案:它的隔热功能要保护的不是套子内部的玻璃瓶而是外在于玻璃瓶的手,此外,玻璃瓶的这项“穿衣戴套工程”还在根本上改变了那个玻璃瓶的性质和用途,使它从一个空置的、被撕去表面标签的废弃的咖啡粉或奶粉瓶,复活为国营企事业单位的职员和北京出租车司机都乐于在上班时间使用的茶杯。
无论如何,资源一旦过剩,套的保护功能及其增值意义便同时随之衰减,甚至反过来逐渐转变为对价值和意义的阻断乃至贬抑。例如避孕套这种以隔离快感的方式保证了这种快感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性的套性装置。就手机而言,在手机设计师和生产商不断推出炫而又炫的质材和面板,以及相当数量的手机持有者频繁换机的大趋势下坚持戴套,未免就体现出一种将手机及其外部界面视为需要保护的“贵重物品”的悭吝而落伍的价值观。同样道理,在这个时候我要是再提那个无论天气好坏,出门“总是穿着套鞋,带着雨伞,穿着暖和的棉大衣”并且把雨伞、怀表和小折刀都装在“灰色的麂皮套子里”的那个“姓别里科夫的希腊语教师”,无疑就俗套到家了。
以上这一套煞有介事只是为了自圆其说罢了,实际上绝大部分随社会风尚而变化的行为禁忌皆难以及时而准确地把握,它随时随地给你下套并且无须自证。关于禁忌,罗素说它“是那么一种道德,给出一套规矩,规定某些事情你一定不能做,却并不讲明理由。有时候能够找到理由,有时候根本找不到理由,但无论如何,这些规矩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而且这些事情你是绝对不能做的”。这就是说,具备了道德形式的套也就同时具备了道德的强制性和动词的能动性。上星期五,我刚在深圳的一家以服务著称的餐厅里坐下,小姐就殷切而麻利地用一个半透明塑胶套把我搁在桌上的手机(已除套!)密密实实地套将起来,说是保护它免受油烟和菜汁的污染。我还没来得及对此表示认同,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另一笑意盈盈的小姐抄起一串亮闪闪的不锈钢锁链(套子的线性延展),三下两下就把我放在另一张椅子上的公事包牢牢地锁在了椅背之上,不用问,这一次是出于对消费者财物安全的关怀。面对全套刑具,我实在是很想告诉她们说:“请把我也套起来然后反绑在椅子上吧,说不定我会兴奋得胃口狂开呢?”本来我真的是想点龙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