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比如美食家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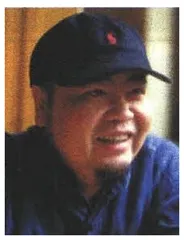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世有美食,却从来就没有什么美食家,也不靠写食主义。
孟子日:“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大也。”所谓“饮食之人”,说的就是“美食家”,或者被别的“饮食之人”视为美食家的人。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人人都看不起美食家,因为他们是一小撮以牺牲大我来成全小我的自私自利的贱人。”
我们的社会可以有实业家、科学家、阴谋家、野心家以及道学家,却不能有美食家。以“养小”为特征的饮食审美活动是“我”字当头的。在每一个“有我之境”里,包括饮食在内的审美都是一种不具普遍意义的个别的经验。虽然对某一术业的专攻都有可能使某人成“家”或者至少成其一家之言,但是饮食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项基本内容,并不足以为成“家”提供有说服力的支持。兔子是动物里的首席美食家,因为它们的口腔里生长着17000个味蕾,比人类还多出将近一倍。不过这种天赋除了娱乐了兔子自己,使其成为最挑食并且也是最容易被饿死的动物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意义,更谈不上给其他的兔子或者吃兔子的人做出了什么贡献。
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不厌恶饮食并且能够正常进食的人都是美食家,当然,每个人也只能充当自己的美食家。许多读书人都曾经从不同的渠道得知“饕餮”的出处,但是说到“美食家”这个词,我敢打赌,90%以上的知道分子,皆是在读了小说家陆文夫先生刊发在1983年第1期《收获》杂志上那篇同名小说之后,才第一次知道中文里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名词,人世间原来还有这样一种专家。尽管80年代初期的读者无不为小说中的美食家朱自冶那种于个人乃至集体经验之中堪称稀有的精馔而震惊,不过在当时的主流话语下,《美食家》的故事始终是以“建国以来几个历史阶段的‘左’倾危害和经验教训”来做其政治正确之背景的。将近20年之后重读《美食家》,我仍然为陆文夫精美的文笔而折服,不过对朱自冶的命运却产生了一种“重新认识”,我觉得一个美食家的悲剧也许并不完全是时代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人的悲剧。换句话说,即使“朱鸿兴”出品的那一碗教朱自冶魂牵梦萦的“头汤面”在前若干年中免受了极左路线之害,后来的工业化、快餐化和全球化照样会把朱自冶击败;即使工业化和全球化未能击败朱自冶,一切的“美食家”最终还是会败在衰败的胃口、脱落的牙齿以及枯萎的味蕾之下。一个人只能做自己的美食家,并且也只能让自己把自己打败。
我个人之所以极度讨厌“美食家”这个词及其所指的那些人,还有一个关键因素,这就是所谓的美食家大都是一些百般挑剔之人。就绝大部分的术业而言,挑剔无疑是精益求精的代名词,同时也更是美食家之所以成为美食家的一种重要行为准则。当然,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对食品的挑剔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无可厚非,而一个美食家的挑剔,往往只是为了再一次验证自己的“专业对口”而已。此外,美食家和像我这样的“美食作家”也不是一路人,前者是真吃,后者是佯吃。在这个意义上,“美食作家”其实更接近于“美女作家”,两“美”之间虽然都是身体写作,却依然存在着上半截和下半截的原则性分别。

我想说的是,在众多的消费品当中,食物其实是一种十分特殊的东西,毕竟这是一种天赐之物,只要是吃不死人,在餐桌前我宁愿祷告也不想挑衅。至于那些美食家们,挑剔了一辈子,最后不还是纷纷以“大味必淡”来自欺欺人吗?这真是史上最大的一宗扯淡,真真淡出个鸟来。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转贴之前,谨容我作此简短声明:别人我管不了,今后谁再称我为美食家,我就会抛出这个段子自卫,不管你是男是女:一美食家上饭店去吃烤鸭。鸭至,厨师未及片斩,美食家止之,略观其色,凑近鸭屁股狂嗅一番,即招来店主质问:“此乃北京填鸭乎?”店主答:“是。”美食家怒不可遏:“非也,此乃江苏麻鸭是也!”
心中有鬼,店主唯唯,少顷,烤鸭一具复至。美食家略观其色,凑近鸭屁股狂嗅,复又招来店主质问:“勿欺我,此乃广东之番鸭!”
店主大骇,终于以正宗北京填鸭飨客,美食家再度观色嗅味,方才满意大嚼。此刻,店小二一边脱裤子一边怯生生地上前求教道:“客官,小的自幼父母双亡,流落街头,向不知自家籍贯,客官神通广大,可否略加指点则个。” 饮食美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