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趁早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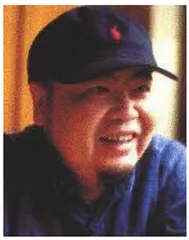 国留学
国留学
定于每年7月7日的高考日一成不变,出的年龄却是一降再降。在全国各地的海外留学展现场,到处都能见到拖儿带女的父母,这种情景要是出现在响彻着“莫让年华付水流”这一时代最强音的上世纪70年代末期,说不定会有人为这些生了孩子还不忘充实自己的父母而感动。
据报章披露的不完全统计,近4年来出国留学的少年连续以40%左右的速度增长,到2005年将突破10万大关。其中以广东省的留学生低龄化最为普遍,1999年度中小学生留洋人数达万余人,占全省自费留学比例的50%左右,年龄最小的留学生才5岁,涉及费用超过人民币10亿元。
低龄留学其实并不新潮,最多也就是一种复古,在中国,这事在一百多年前就有过了,跟解放小脚妇女差不多同步。中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正式向海外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就是由30名年龄在12到15岁之间的小孩子组成的一支童子军。不过那次公开招选尽管属百分之百的公费公派,民间的反响却一点也不热烈,说“惨烈”还差不多,因为家长和政府一样,都把这种行前要签下生死状的出国留学视为畏途。那种情境,实在是有一点像80年代深、沪首发原始股,事后证明升值了几十倍的股票,当时就愣是没人敢买,就是半买半送也不愿意碰。少数敢于尝试的人,大概都把此举当作个人对国家建设所做的无私奉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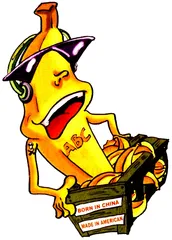
留学生低龄化的利弊,坊间众说纷纭。说好的认为,这样做可以使孩子尽早摆脱国内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有助于增强他们日后在事业上的竞争力,教育从娃娃抓起,无可厚非;说不好的则认为,此举一来容易造成幼童们严重的文化认同困惑,同时给国家造成了巨额外汇流失,相比之下,作为独生子女的“小皇帝”们普遍低下的生活自理能力倒是还在其次。
事实上,文化认同问题乃绝大部分家长们共同的矛盾,在此之前,台、港两地已有无数悲哀甚至悲惨的前车颠覆于欧美各地。做家长的一方面鼓励儿童们尽早吸纳西方文化,同时又苦心孤诣地逼迫其承袭中国传统。遗憾的是,一颗小小的脑袋怎么可能创造出学贯中西的奇迹以及领会到中体西用的奥妙呢?撇开资讯和认知上的差距不谈,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家长和一百多年后的中国家长所担心的其实还是同一个问题:生怕自己生出来的正宗中国孩子变成假洋鬼子。当然,担心的又何止是家长,当清廷惊见那批换上了美式服装中国儿童像美国人一样打棒球、踢足球、溜冰、骑脚踏车,甚至胆大包天地剪了辫子之后,便采取了一项断然措施:于1881年9月6日招回全部留美幼童。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流产的“海归”就这样诞生了,当然,也没有带来一美元的风险投资。
我倒是觉得,做家长的既然替未成年的子女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就大可不必为此而自寻烦恼。别说是黄皮白心的假洋鬼子,就是一个不小心做成了白皮白心真洋鬼子,又有什么大不了呢?在道德含义的利空出尽之后,留学正在变成一种家庭式的投资理财行为,不管种出来的香蕉是黄皮白皮,只要能吃,只要好吃,就是一条好蕉。不过话说回来,国的早出和晚出,学的高留和低留,最好根据各家各户的具体情形而定,不宜演变成一场年龄上的恶性竞争,长此以往,只怕有一天会应验了空姐在飞机上经常教导我们的那句话:“要帮助别人戴好氧气面罩,应该先帮自己戴好”——届时,只怕做家长的都在急着把自己先弄出国门,把小孩直接生在国外,看看谁比谁早当留学生!
个人一向坚信,爱国和出国都不分先后,也不认同在出国留学的问题上搞年龄竞赛,更不担心每年因此而外流的上百亿元会造成又一次变相的庚子赔款,我甚至四处放话,今后就让我的女儿在北大清华凑合凑合算了。不过说归说,表态归表态,每一次到幼儿园去接上小班的女儿回家,望着她无忧无虑的小脸蛋,我的担忧就愈发深重起来:我那苦命的孩子啊,你知不知道,许多年以后,当你踏入社会谋求一份办公室普通文员的职务时,会有八个同胞与你竞争上岗,其中包括两个哥廷根的博士,三个哈佛的MBA以及三个牛津的硕士,届时老爸我若不把你栽培成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你就喝西北风去罢。
这当然只是一种赌气的说法,但是未来会怎样,Who Knows?事实上,经过对《穷爸爸,富爸爸》的反复研读,我已经测算出尽早把孩子送出去是一项绝对划得来的投资,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后代的竞争力,更关乎我个人的人生规划。而且在我成功地提前退休之前,还可以吹吹我家的哈佛女孩,骂骂国内的教育制度,弄好了出几本书,再不济也混几个稿费,回报率相当不俗。 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