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问题:考土豆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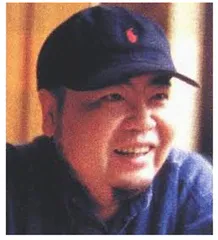
我国不仅是地球上的头号人口大国,也以近7000万亩的种植面积成为头号土豆大国。
若不是土豆躲在地里既不显眼兼且样子难看,“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只怕早已改做“漫山遍野的土豆高粱”。
最近有农科专家在报上指出,由于缺乏现代化的储藏设备和方法,每年有占总产量25%~30%的土豆因此而损失掉,剩余部分的综合经济效益也很不理想。什么是土豆的综合经济效益?以北京的麦当劳为例,一包120克的薯条售价为7.5元,生产这包薯条只需250克鲜薯,在产地的价值仅为0.15元,这意味着深加工使土豆升值了50倍。专家们据此算了一笔账:若将我国土豆1.82亿吨总产量中的60%用于深加工,则每吨的价值将会从1000元飙升至5000元。各位观众:土豆的升值总额就是——5000亿元,大约相当于中国股票总市值的1/9,同时3.5倍于本年度的中国军费预算。
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就可以浇灌多少多少亩干旱的禾苗,每人每月供献一节牙膏皮,就可以让越共游击队击毙多少多少个美国大兵——作为一个受这种教育长大的薯条爱好者,读到上述消息时的欢欣鼓舞可想而知。不过,5000亿人民币即60%的炸薯条比率,却是参照西方国家通常达40%的土豆深加工率估算出来的。西方人与土豆之间的“惊情四百年”,得出的就是40%这个数值。
带着对于欧洲殖民者完全异质的印加文化背景,土豆在1565年首次被引进欧洲时,是作为一件礼物呈交到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手上的。在随后的几年里,主要是在欧洲各地的植物园里被当作异域稀有植物展出。18世纪之前,欧洲人普遍觉得马铃薯的形状古怪、可怖而且不祥,更不知道应该怎么吃以及哪个部分可以吃。此外,由于土豆与番茄同属茄科,外形又似勃起的阴茎,一度在欧洲被当做催情剂使用。不过,这种名符其实的“草根”食物,以其顽强的适应性和高产、高淀粉质、易饱涨、可久贮、煮食快捷,而且在地底生长,不易遭到破坏及盗窃等等先天性的优越,在帮助欧洲人捱过了史上数次重大饥荒和战乱的同时也造成了人口爆炸。Larry Zuckerman在《马铃薯——改变历史的贫民美馔》一书中写道: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这样的土豆高产地区,1750至1850年间人口增长了三倍,至于平民阶层的成长又比其他阶层来得迅速,相信与土豆的廉价有关。无论如何,这正是工业革命的物质基础。
1845年,一种引致马铃薯枯萎病的真菌首次侵袭爱尔兰,令大批土豆变黑并且枯死,酿成长达5年的饥荒,夺命近200万,亦驱使同样数目的饥民向北美迁移。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土豆也就没有今日的美国。当然美国在100年后也对土豆作出了加倍的回报。如果说土豆的大量种植曾间接促成了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勃兴,那么200年后,土豆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浪潮中,再一次以薯条和薯片的变身而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对土豆的油炸以及“条片化”改造,不仅造成了能量和热量的激增,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50倍的自我增值。
土豆移居中国的确切时代暂不可考,但可以相信的是,土豆和16世纪由埃塞俄比亚经缅甸传入中国的高粱以及葡萄牙人于同期经澳门引进的玉米和白薯一样,对中国的人口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床下”作用。从16世纪到17世纪,中国人口在8000万的基数上开始激增,乾隆六年,为1.4341亿,乾隆六十年,翻番至2.97亿。马戛尔尼勋爵因而写道:“美洲的发现与航海活动给中国带来了也许同欧洲一样多的好处。”
不过与美国每年人均吃下——140磅的纪录相比,中国的马铃薯消耗量仍属偏低。土豆在中国至今仍被视为一道菜而非主食。不仅是一道菜,而且是一道“不怎么样”的菜,南北出品,大体上皆乏善可陈。土豆在我国的这种处境,还可能与其一直无缘获得某种正面的文化意义有关。同具外来者身份的高粱虽亦未能入主餐桌,却因独一无二的文化象征性而得到了高度尊崇。一般相信,现在的中国高粱乃自赤道非洲引进,不过仍有史学家坚称在黄土高原上存在着中国人自己的高粱之独立谱系,证据是西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是情感因素,但是就足球而言,尽管国际上公认中国人在基督诞生前二百年就玩过类似的游戏,但毕竟不是现代的足球,更不可能为我们留下一个历史悠久、战迹彪炳的名叫“皇家高太尉”的足球俱乐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