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自省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嘟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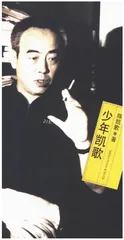
陈凯歌在电影里经常探讨的一些问题源自他少年时期的经历
准确说《少年凯歌》不是本新书,最初它应日本讲谈社之邀而写,台湾远流出版社很早就出过繁体字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1年在大陆首次出版该书。导演出书而不谈自己的电影是很少见的事,陈凯歌此书只选取了其个人成长经历的一个片段,大约从上世纪60年代中到70年代初,有10年的样子,当时正值“文革”时期。
陈凯歌的文字功底非常好,这是《少年凯歌》给人的第一印象,好得甚至有点让人吃惊。这一方面得益于家教,他小时候曾在母亲教育下背过大量古诗词,直到“可以成百行地背诵排律”。除此之外,陈凯歌酷爱读书。看《少年凯歌》,经常会有精彩的词句跳出来,比如一位姓刀的队长“刀一样走过来”。在描述复杂的体验时,他亦能找到精准的表达方式。陈凯歌曾经跟一群少年殴打过一名所谓“耍流氓”的少年,他打人的目的是为了成为集体中的一员。多年以后,他仍然清楚得记得当时的感受:“我两眼发黑,浮起一圈一圈的金色,手上的感觉像打在一匹马背上。”在众多名人传记白开水式的叙述氛围中,陈凯歌的文字更显突出。但也许是在语言上下了太大工夫,读起来很明显觉出不轻松,能充分感觉一种中年人沉重的自我深刻意识,刻意为之的痕迹也稍重。
陈凯歌在这本小册子里要充分表达心里那个沉重的结,他在“文革”时出于怯懦和着急表明革命立场打了自己父亲一个耳光,在红卫兵抄家时候又没有勇气帮助站了三个小时的母亲。这体现为一种深刻的自我折磨的罪恶感。后来他在《霸王别姬》中曾艺术重现这个背叛的场景:杨小楼为了活下去出卖了程蝶衣和自己的老婆。陈凯歌在这本小册子里告诉大家,是这十年经历的人和事使他能从更高的角度考虑人和社会,尤其是人。人一软弱,他的精神一旦受到伤害,就用自我扭曲的方式愈合。陈凯歌是一个极善自我表达的人,他的这十年自述强化了戏剧冲突,给予社会冲突中的个人命运更强烈的理性思考。这本小册子通过社会背景中的个人定位来描述个人的思路历程,在这种思路历程中来展现那个多少有点放大的自己。熟悉陈凯歌的人都熟悉他善于把任何一件日常小事放到一个历史哲学的大语境中去叙述的习惯,而且这种叙述多有文学化的渲染。这本小册子的文学价值也应该高于历史与哲学的价值,所以从文学角度去读解,恐怕更具趣味。
北京电影学院有个传统,本校毕业的学生拍出作品来都要拿回学校放映,并跟师生见面交流。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也曾遵从这一传统。放映当晚北京电影学院的“天堂影院”人满为患。放映完毕,有学生提出异议,陈凯歌的回答照常不令人满意,因为他的回答总像是在为自己的电影辩解。陈凯歌爱护《荆轲刺秦王》的答案包含在一句对该片的批评中:《荆轲刺秦王》里所有的人都像是陈凯歌的化身,他借这些人的口说自己想说的话。但也许他的话过于深刻,感受到的东西太多,想说的也太多了,观众听不下去。电影形式不太适合做说话的工具,在《少年凯歌》里他说得痛快,读者在找到一种体察方式后也会看得痛快。
陈凯歌现在已经到好莱坞拍电影了,不知道他将怎样在好莱坞电影中安置内心深处的深刻自省。 大导演少年凯歌荆轲刺秦王陈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