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2H》的争议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于)

《2H》中的马晋三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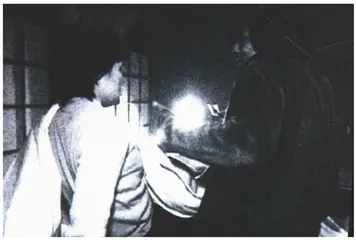
剧照
2001年6月18日到6月24日,北京电影学院的日本留学生发起举办了日本独立电影放映周。《2H》在所有展映的影片里显得很特别:它是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拍摄的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的故事。
很难说《2H》是部日本电影还是中国电影,它在1999年戛纳电影节的经历似乎表明没有人愿意认养。中国各媒体有不少关于当年戛纳盛况的报道,仔细介绍了国外电影和演员,但没有关于《2H》的只字片语,尽管它得了“最佳亚洲电影奖”。日本媒介也没有说什么,只在获奖名单上列出了它的名字,后面有个括弧里说明:这是部日本电影,但可能是弄错了。制片人张怡写了一篇文章给日本各大媒体,质疑到底什么样的电影才能算是日本电影(一般情况下,应该按出品公司所在国确定影片国籍,投资《2H》的龙影公司是张怡他们在日本注册的)。她说并不是一定要争日本电影这个名分,而是不满意部分日本人的态度。有个日本记者说出了背后原因:如果张怡不叫张怡,李樱(《2H》的导演)不叫李樱,而是换作麦克尔·李什么的,日本人可能就不是这个态度了。
关于《2H》的争论不止于此,在北京电影学院放映后,它引起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应。新浪论坛“影行天下”有个小小的论战,有的网友称《2H》给放映周完美地结了尾,它是这次电影周最满足人们想象的电影,那些只看了20分钟就提前退场的观众肯定会后悔。《2H》受到部分观众的欢迎是事实,谁也无法否认影片结束后长达一分钟的掌声和观众踊跃的提问。但有的观众从另外的角度读解,“先鼓掌的人的掌声把睡觉的人吵醒了,先后两次掌声,各半分钟,听起来就像是长达一分钟了”。睡着的人肯定对影片内容跟长度的比例不满意。有观众建议修改成四五十分钟的长度,有的观众则说电影提前20分钟结束最合适。有的意见直接奔导演李樱,认为李樱在影片中的探索失败,没有处理好这么精彩的一个人物马晋三先生。
《2H》有一种混合风格,它既像纪录片又像剧情片。这正是李樱探索的方向:在《2H》中用剧情片手法拍摄纪录片。影片除了真实记载下马晋三先生平日的生活外,很多处也可以看出导演的介入——导演甚至有意安排情节的发展方向。这部打破纪录片与情节片界限的新品种影片是1998在山形国际纪录片节上惟一一部代表日本参赛的作品,它有很高的得奖呼声,但没有得到奖项。向来以逼近真实为最高追求的传统纪录片观念目前还不能接受《2H》。其实,在每一部纪录片史中均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美国纪录片大师佛拉哈迪生前就经常使用搬演的手段,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北方的纳努克》也应该是最著名的导演介入的例子:他要爱斯基摩人纳努克放弃正常的生活习惯去配合拍摄,结果后来纳努克饿死了。记录与虚构在电影史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想划清楚彼此之间的界限,《2H》显然试图站在这条界限上,或者根本无视这条界限。
《2H》的故事
马晋三先生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根据李樱的父亲写的一篇文章中记载,马老先生出生于云南省,18岁赴日本留学,回国后追随孙中山先生。他在黄埔军校任教官时与周恩来相交甚好。解放后马晋三去了香港。1953年周恩来总理建议他去日本做被释放战犯的工作。马晋三欣然前往,在日本一直住到1998年去世。《2H》拍摄的是马老先生去世前一年的生活,正式投拍前李樱跟张怡准备了8年。
镜头前马晋三老人的生活很单调,平日里经常一个人看电视,有时吹吹不成调的箫。画家小熊多年来每个周末都去看老人,每次走的时候老人都依依不舍地挽留。两人渐渐有了爱情与亲情外的第三种感情。可能是年龄缘故,小熊很想要一个孩子,为了给私人生活腾出空间,她请了个中国留学生做老人的保姆。老人感到了冷落和伤害,跟小熊吵了一架。小熊说以后再也不去老人那里了。老人去世后,小熊拉着老人露在被单外的手痛哭。
老人很少提到自己辉煌的过去,他给导演看了自己得的勋章,导演说老人总算给历史留下了点什么,老人却说,给你看这些东西的目的就是让你知道这些什么都不是。看透一切的老人皈依了基督教。
《2H》是个奇怪的名字,它可以理解为两个小时(TWO HOURS,《2H》的长度为120分钟),也可以把H看成人类(HUMEN)这个词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