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宽广如海》到《源起》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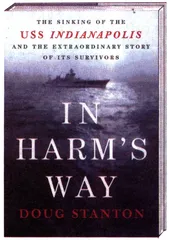
本期新书虽然不少,但还有更引起我们兴趣的书目。
首先是“英文版的《圣经》形成了英美两国的语言、政治和文化”。做出这一论述的是两部作品:由本森·鲍勃瑞克(Benson Bobrick)撰写的《宽广如海——英文〈圣经〉及其激发的革命的故事》(Wide as the Waters,The Story of the English Bible and the Revolution It Inspired)和由阿利斯塔·麦克格拉思(Alister McGrath)撰写的《源起——詹姆斯国王钦定本〈圣经〉的故事,以及该书如何改变了一个国家、一种语言和一种文化》(In the Beginning,The Story of the King James Bible and How It Changed a Nation,a Language and a Culture)。
要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固然要以古希腊和罗马为其源头,但要弄清其近现代史,就不能不认识当年称雄于世、号称“日不没国”的大英帝国及其北美殖民地——当今首屈一指的强国——美利坚合众国。稍谙世界史的人都知道:就漫长的世界史而论,不消说美国,就连其原先的宗主国英国,也只能称作“后起之秀”。
当欧洲大陆上“文艺复兴”的曙光从意大利升起,荷兰人已经人手一册《圣经读本》的时候,英伦三岛上的居民还大都是文盲,甚至规范的英语尚未形成!而改变这一落后面貌,使英国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依靠英文版《圣经》的普及。文字的规范与精神的觉醒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并带动了政治的革命。
第一个把《圣经》从拉丁文译成英文的是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1324?~1384),他和大家熟悉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作者、号称“英国诗歌之父”的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0~1400)算是同时代人(后者对规范英语的形成同样功不可没,但文学作品的影响显然不如《圣经》更广泛)。威克利夫是位主张宗教改革的教士,他所领导的罗拉德教派便是反对罗马天主教的一种新基督教。由于他根据权威的圣·杰罗姆的拉丁文版本《圣经》译成的英文本成为教士们阅读、宣讲及解释教义的依据,在普及文化上所起的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1381年,贫困的牧师约翰·波尔就曾引用《圣经》来唤起农民。他用“当亚当耕耘、夏娃织布的时候,又有谁是上等人”?这句朴实的语言体现出人类生来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思想并成为当时农民起义的口号。
后来,英王詹姆斯一世(1566~1625,斯图亚特王朝第一代君主,1603~1625在位)于1611年颁布出版了依据廷德尔(William Tyndale,1492?~1536,英格兰新教殉教者)的新译文的钦定本《圣经》,其准确的译文、铿锵的语句体现了英语言的定型,数百年来始终是标准的读本。单就英语言而论,这两个译本就转用了许多希伯来语的短语(如“酸葡萄”、“永远”)并创造了许多英语新词(如:nowadays来自威克利夫,beautiful来自廷德尔)。当然詹姆斯一世再也想不到,正是他的这部钦定《圣经》后来成了1642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西方史书称“清教徒革命”)的精神武器,从而推翻了他开创的斯图亚特王朝。
尔后,移民北美殖民地的英国清教徒仍是本着《圣经》中的勤俭精神在新大陆上创家立业,后来又本着《圣经》中的平等思想发表了《独立宣言》,驱逐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起自己的合众国。
学者认为,欧洲的文化思想有三大来源,即古希伯来人的《圣经》、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和科学(“文艺复兴”就是对其重新发现和大力弘扬)和哥特人的传奇(英国民族称盎格鲁-撒克逊,即古哥特人的后裔),分别赋予了他们情感、理智和勇武三种品性。英国文艺复兴的杰出代表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所提倡的实验科学,对于建立从古典力学到现代科学的体系和理性世界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这一切奠定了英格兰强国称霸的根基。
西方的“圣经学”早已走出了“神学”的窠臼,如戴维·罗尔(David M.Rohl)所著的《时间的检验》(A Test of Time)[卷一《圣经,从神话到历史》(The Bible:From Myth to History),卷二《传说,文明的起源》(Legend,The Genesis of Civilization),我国有作家出版社译本],就考证出伊甸园不过是古希伯来人的发祥地,就在地球上的西亚等等确凿的事实。我们如果不从狭隘的宗教观念出发认识《圣经》,定会发现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意义。
另一个题目是有关去年美国竞选2000年新总统的。由于小布什上台以来在国际舞台上种种蛮横表演引起世人公愤,也引起美国国内非议,人们不由得不对去年总统竞选中的秘闻轶事做出形形色色的揭露和分析,直至怀疑佛罗里达州的计票中大有“猫腻”——其本身在美国二百年历史上即使不算“丑闻”,亦足以称为“奇闻”了。
我们不妨以“2000年美国总统的产生”为题,综览一下四部新书:达纳·密尔班克(Dana Milbank)的《破口:与阿尔·戈尔和乔治·W·布什在槽沟中的两年——2000年竞选运动追记》(Smashmouth:Two Years in the Gutter with Al Gore and George W. Bush——Notes from the 2000 Campaign Trail),焦耳·阿钦巴赫(Joel Achenbach)的《像似总统,只嫌稍小:2000竞选寻踪》(It Looks like a President,Only Smaller:Trailing Campaign 2000),贾克·忒帕(Jake Tapper)的《肮脏下流:窃取总统职位的阴谋》(Down and Dirty:The Plot to Steal the Presidency)和由《华盛顿邮报》政治小组撰写的《僵局:美国最接近的一次选举的内幕》(Deadlock:The Inside Story of America's Closest Election),当对美国式“民主”有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