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新罪名:多余还是必要?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三联生活周刊)

设立见死不救罪是否会使勇士的处境越来越尴尬?(钟敏 摄/photocome)
“性贿赂罪”:私人生活与公共权益的较量
“包括性贿赂在内的非财物贿赂罪实际上是源头犯罪,它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别的罪恶就不断涌出。”因为在“2000年江苏省刑法学研讨会”上,呼吁立法制裁“性贿赂”而广受媒介关注的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金卫东在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过程中强调:“必须把性贿赂罪在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将它纳入刑法的射程之内,不仅是因为它的社会危害性,还因为它的持续性、不明确性,沉溺其中的掌权者往往对权力失控或放弃,而行贿者利用少数的钱财就可以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
国人讳言性,性贿赂罪矛盾的焦点之一是该不该把性拿到公堂上来谈,特别是当它跟腐败紧密联系的时候,它就显示出作为边缘事物的优势来。人们更多地把那些贪官背后的性腐化问题当成街头巷议或者花边新闻,而一位法律界外的人说过:“一个法制国家,对于性的问题,不应该干预太多。”这就形成一个法律的空档,变成了在严肃案件夹缝里顽强生存的恶之花,人们小心翼翼地在法律范畴内回避了它。
“我在提出这个倡议后受到了多方的质疑和发难,反对者认为首先这是一个道德或者说私生活的问题,法律不能越过道德的界限来管制它。但事实上,性贿赂案多数是以公款实施贿赂,受贿者是以公职的名义,并不是私交吃请这样简单的社交问题,这已经不属于隐私的范围,已经侵犯了公权,那些置公共利益于不顾的隐私权肯定不应该是绝对的,法律有权过问它的种种细节。
“其次,反对者普遍认为在取证和实施操作上有很大的难度,但是既然性贿赂罪跟财物贿赂罪不同,是一个难于量化的罪行,我们就可以采用相对绝对的证据,先定下来,不完善的地方再逐步完善,法律是必须保证严肃性,但还要有前瞻性,必须起到防范和威慑犯罪的作用。”
金卫东还认为,入世以后,中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非财物贿赂的局势,我们如果不提前作好司法准备,将出现更加失控的局面。
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二处处长黄晓文根据他将近五年的一线办案经验,纯粹的性贿赂案他还没有遇到过,或许是因为在审讯中,他们通常没有刻意地去问当事人这方面的问题,而通常只问跟法律有关的问题,而且与定罪无关的问题,当事人有权拒绝回答。但是这并不代表他认为现在有必要马上对“性贿赂”立法定罪,普遍的观点似乎是认为时机未到。
京都律师事务所的田文昌律师就肯定地说:“我赞成‘性贿赂罪’通不过的说法。”他认为,法律的指定不能凭感觉感受,或者纯然出于一种需要。从立法的角度讲,把性贿赂认定为犯罪是不容易的,这其中有一个法律与道德的界限,而法律与道德有一致性也有原则性的区别。作为一切法律后盾的刑法,极端的手段只能针对极端的反社会行为。而且性贿赂很难界定罪责,在诉讼程序上也有很大困难,证据取得的可行性也很难保证。
当故意传播艾滋病成为一种罪
对设立故意传播艾滋病罪,有很多具体环节仍让法学界专家和政府官员都颇感困惑。首先艾滋病不能简单定义为性病,它有除了性行为之外的很多传播途径,包括不洁输血和使用共用注射器静脉注射吸毒。
中国上世纪90年代发现艾滋病人后,社会对他们实行的是普遍的歧视政策,除了隔离、拒绝与之交往还有就是热衷于传播对于他们品行问题的种种揣测和谣言。而后,种种恶劣的社会处境引发病人报复的心态,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些故意把他们身上这些绝望和不幸传播到别人身上的病人。
2001年9月8日晚,北京市公安局缉毒处出动警力抓捕毒贩。在抓捕过程中,一位刑警的手臂被毒贩子划伤,在审讯过程中,毒贩子供认他犯有艾滋病,受伤刑警不得不迅速采取检测和遏制措施。
将传播艾滋病列入刑法打击范畴不是法律专家通过法理推导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记者采访了专门从事艾滋病社会行为学研究的协和医科大学流行病教研室主任张孔来,他正开始着手进行一项关于艾滋病立法的国家课题研究,所以他对是否应该设立“故意传播艾滋病罪”发言的权威性不容置疑。
他的研究小组主要通过社会调查的形式,对不同群体的艾滋病状况做细致的了解和分析,并将研究结果提供给卫生部和立法部门作为制定相应法律法规的重要参照。同时,他们积极地宣传预防艾滋病传播的有效手段,比如在性服务业从业人员内普及避孕套的使用,在吸毒人员中宣传使用共用注射器的危险性等等。更多的,他们试图让社会大众明白,以往“好人不染病,染病不好人”的观念是错误的。“总之,我们在努力减少感染源和提供给现有病人更为良性的生活环境。”医生眼里,病人永远需要用宽容和救治为主的态度来对待,张孔来首先对于中国也要把故意传播艾滋病的病人绳之以法表示不解,他说:“我认为,还是要以教育为主,在原有的《传染病法》中,提到的有意传染,仅仅是处以教育,我认为最关键的是社会要善待他们,然后才是让他们知道自己很不幸,不应该将这不幸再带给其他无辜者,至于用自己的病作为报复社会和攻击别人的武器的病人,我相信不是多数。人们只看到了那些报复社会的病人,没有看到被社会舆论和自身的心理压力压迫得自杀的病人,那么,为什么不惩罚那些歧视艾滋病人的大众呢?”
一条针对绝症病人的刑罚对他们本身能起到怎么样的威慑作用,本身就是值得怀疑,更何况随之而来的是种种实施的难度。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二处处长黄晓文就认为,对这一新罪名的立法原则有两条,首先是是否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次是当事人是否有主观意愿。而立法目的不应该在于处罚个人,而是需要建立良好的医疗体制,目前,我们的财力物力还不能够具体防范艾滋病的传播,而这其实比隔离更重要。他说:“艾滋病故意传播比如抓搔撕打,或者明知自己有这病还故意没有防范措施地跟别人发生性关系,立法的难点恰恰在于实际操作的困难,因为艾滋病的特殊状况,目前司法实践部门在医疗前提下的改造普遍容易有抵触情绪,不仅大笔的医疗开支由谁来出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如何确保病人的安危和医疗条件的持续也够伤人脑子的了。”
是不是起码要等张孔来教授和他率领的研究小组的研究结果出来以后,再做决定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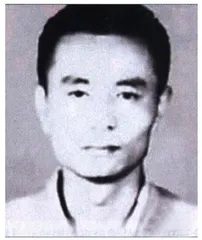
亓培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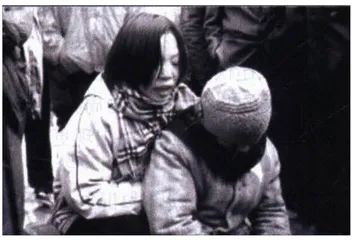
亓培玉的死亡对现行的法律和道德是一个信号(本刊资料)
见死不救罪:最终将惩罚谁
发生在安徽的一起研究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害的恶性案件再度引起人们对见死不救这个古老话题的浓厚兴趣。2001年2月4日下午4时左右,在同济大学攻读研究生的亓培玉因为一句维护社会公德的话被人一路开车追杀棍打,最终被这4人追打受伤掉入泉河致死。当时,周围观看的人不在少数,如果按照人大代表讨论中的“见死不救罪”论处的话,他们可能因为冷漠的围观被处以刑罚?刘如琦等32位代表就此提出议案,要求设立“见死不救罪”。
当然,谁受到伤害都希望勇士出现,谁遇到别人有难,都希望自己不面临痛苦的抉择,是行动还是任其发生,但到底应该由谁来挽救公民道德的底线呢?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二处处长黄晓文认为:“法律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个义士的出现不是拿着刺刀威逼的,道德是发自人们内心深处的,对见死救还是不救这样比较让人犯难的问题,还是留待公民自己去选择为宜。”
“我们起码不应该忘记侦察和追究犯罪的责任在于国家,不能强迫和要求公民对此负责。”田文昌认为,“设立见死不救罪我不赞成,现行刑法有一个不作为犯罪,但是指的是先前作为形成了一个特定的意义。”中国首例对不作为故意杀人罪判刑的案子发生在2000年6月的浙江金华,当事人李家波跟其女友同居后女友怀孕,他逼迫她流产遭到拒绝后,女友服毒自杀他又见死不救,以致怀有3个月身孕的女友不治而死。李家波被判了5年徒刑,但是正是他先前的行为导致了女友的最终死亡。
但是,一次发生在公共场所内的见死不救行为,怎么去裁定谁负有更大的责任,是根据见死不救者与事件发生现场的距离吗?而勇士在社会中遭到的挫折也是见死不救更为泛滥的原因之一,公安部奖励见义勇为人士的基金最高奖励是5万元,是以一人生命为代价的,而那些因为正义而背负终生的疾病和经济负担的勇士,事后的无穷麻烦可能要比他事前一瞬想到的要多得多。这都阻止了人们向社会公德心靠拢的勇气。
很难想象,见死不救罪会真的实行,它带来的副作用是否会使得少有的勇士越来越处境困难,公民人人畏惧与危险见面,一边是法律的制裁一边是倡导不计得失的高尚行为,当勇士甚至失去了为自己谋求事后的合法权益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