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核酸斗起来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金焱)

第一对对手:媒体VS核酸工业
“我们要被迫迎战!”这是2月22日关于“核酸问题”的我国首次行业听证会上,第一个发言者——中科院微生所的程光胜大声喊出的第一句话。
2月28日,身处京郊的程光胜再次重复这句话。他说,因为媒体发起了挑战,所以他——中国核酸产业中的一员要奋起迎战。这是被迫的,也是严肃的。在接受采访的整个过程中,他的话语始终保持了这种基调。同时,这场争战发生的双方被他设定为:一方是媒体,对立方是我国的核酸产业。后者就是他第一句话中指的“我们”。
媒体被限定为攻击者,是因为听证会当天,《南方周末》发表了大篇幅的报道《三位诺贝尔奖科学家指斥中国核酸营养品》,这一报道被理解为是有预谋的中国保健科技学会副秘书长黄明达称这是一份专门为此次听证会准备的“特别献礼”。再向前追溯,包括开这样一个听证会也是由于此前在核酸问题上“舆论导向混乱”引起的。
黄所说的舆论导向混乱是指,先是网上有文章,将核酸营养列为商业骗局一类的把戏接着新华社有一篇标题就很有杀伤力的报道《国际专家称人体不需要额外补充核酸》,据说这一报道先后被几十家媒体转载;再有就是《中国青年报》中将核酸与米粉相提并论……
争论升级为争战,是因为从事核酸研究的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些报道“对消费者的思维造成了误导、加大了政府的压力”,甚至是“对核酸产业的破坏,等于攻击我们的国家”。
记者最终被指认成争战的发动者。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的方福德总结说:媒体起的是一个很坏的作用。以网上那篇文章为例,他说:网上有言论自由,有人需要在网上发泄,但媒体的记者人为地把这些东西挑出来,转来转去,这就制造了混乱。如果媒体不理它,我国的核酸工业还是一片形势大好的。
争战前的核酸工业的形势之好,方福德说已到了需要“扼制”的地步。早在去年年底,相关各方就已估计到,过了春节后,华夏大地上很可能要打起核酸类保健品大战。但大战还在孕育之中,媒体就先出招了,媒体对核酸保健品的功用发出质疑。
媒体刚·出招,核酸工业就现出败走的倾向旺销的核酸类保健品开始被怀疑,被抛弃,销量锐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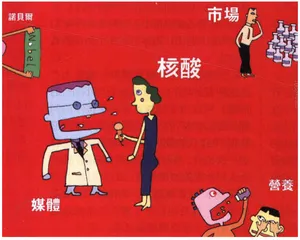
你来我往的“诺贝尔”战
面对失利,个别核酸专家变得冲动。他们分析这场争战时,发现媒体的战术是围剿一个品牌,继而否定核酸保健品。
核酸产业链条上的核酸保健品企业是个擅耍小聪明的角色,但他们玩的每个小花样都成了媒体打击的目标。比如将补充核酸的作用与“增强基因自主修复能力”扯在一起,这个立不住脚的说法被媒体集中火力痛打,就连这些为核酸产业呕心沥血的核酸专家们提及此事也为之脸红。他们称这是一种“吃猪肉就长猪肉”的逻辑,“简直就是胡扯”!
程光胜对这些商家的评价是“求利心切,唯利是图,最终自设陷阱,自掘坟墓。”
核酸专家在这场争战中有些被动,几乎是疲于应付。在“核酸事业”这样宏大的事业面前,他们甚至做出了“牺牲自己”的准备。所以这次争战中,他们几乎成了主力。而这次争战最精彩的交火应该是“诺贝尔奖”大战。
先将诺贝尔奖抛出亮相的是大连市某核酸企业。3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同该企业产生亲密关系是因为,这堆科学家都因研究核酸而获诺贝尔奖。于是,3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硬被拽进了该企业的阵营中,貌合神离地成为宣传广告中的“形象大使”。
这一拉大旗做虎皮的做法遭到媒体的奚落,在争战中这一点被当作易被攻陷的堡垒。不知是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术,媒体也抬出了诺贝尔奖科学家,其广泛性也不逊于上面的38位。包括诺贝尔医学奖、化学奖获得者和研究与“核酸营养”无关的一名瑞士诺贝尔奖获得者。
这三位抛出三枚重磅炸弹:“据我所知,没有证据表明核酸是一种营养物或有益健康”;“据我所知,我们过健康的生活并不需要额外的核酸”;最后一人对核酸产品的营养价值评价是“绝对没有”和“没有任何特殊的营养价值”。
听证会上,云集的中国核酸专家对“诺贝尔奖”这一武器给予了坚决反击。“中国专家要敢于向外国人说‘不’”,黄说。就这三句话本身,方福德反驳了三条意见,不是反驳“诺贝尔奖”科学家,而是反攻媒体——他认为这是虚假报道:一,凡是诺贝尔奖科学家,对科学的问题,自己没做过的,绝不会轻率地发表意见;二,按美国伦理规则,绝不用“指斥”的口吻说话;三,这件事涉及学术争论,但核酸同他们本身没有利害冲突,不应是他们该管的。
方对自己的判断很自信:“我敢打赌。”这种判断和他的经历也有关:“整个美国我都走遍了,不管是诺贝尔奖科学家,还是普通老百姓我什么样的没见过?对美国我熟得不得了。”
程光胜则同时向媒体和核酸产业的商家开火:诺贝尔奖科学家不管做不做核酸,只要不做核酸应用就没有发言权。他说用“诺贝尔奖”来说明问题,媒体和商家犯的是同一个错误,都很愚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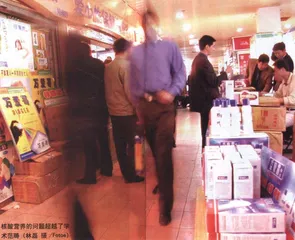
核酸营养的问题超越了学术范畴(林磊 摄/Fotoe)
核酸专家:高悬免战牌
媒体与核酸产业之战似乎暂时告一段落,双方都觉得自己该表达的都表达得很清楚了。
黄明达总结此次数位专家卷入“核酸漩涡”的教训时说:“他们没有对付媒体的经验”。像是回应这句话,方福德说他的感受是:同媒体打交道让他心有余悸,不知什么时候再被捅一刀。所以他采取了低调的办法——“不接触”。据说这也是核酸专家们一致的意见:到此为止了。
黄明达则更有耐心。他心目中的媒体记者“连中学学的东西都忘掉了”,所以他要像教小学生一样去接受这些记者的采访。
第二对对手:核酸专家VS分子生物学家
比起与媒体的第一战场,核酸专家们在第二战场上的形势全然不同。这是因为他们的对手变成了分子生物学家,这使得这一战场全没第一战场的甚嚣尘上,更为安静。核酸专家这时变守势为攻势,而且,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核酸专家:用科普做武器
黄明达说,对于核酸的应用价值,我相信80%的分子生物学家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黄的观点几乎是核酸专家们的共识。程光胜进一步指出即使是研究核酸的科学家,也不一定回答得出,因为核酸营养与应用有关,研究核酸不等于研究核酸营养。
发出这种论调的原因很简单:大多数分子生物学家对核酸营养品的额外进补问题不敢苟同。所以,本来同属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科学群体,却派生出两个阵营。
核酸专家们认为,认识不到核酸的营养价值,说明那些分子生物学家们“不懂”。黄明达直接指出,这些生物学家们“知识偏于老化,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教科书上”。
方福德的语气更和缓些。他认为产生这种观点对立有一个大同行与小同行的问题,所以对于核酸这样一个很窄的问题,只是大同行的分子生物学家们就只能依据70年代的教科书了。他至今颇为留恋一次论战,当时就核酸营养问题,他一个人对北大的四位教师,最终将其“打得落花流水”。在他看来,四位教书匠败北的原因,就是他们不了解在经典概念之后,科学上还有哪些新发现。
“其中有一个老师还说自己编写了细胞合成讲义。我说,我不需要说明你不对,我只需拿出最新的文献就够了。”结果,“我一拿出来,他们就全傻了眼”。
分子生物专家们则沉默得多。不过本刊记者接触过的几位还是有些年轻气盛:我们天天进行细胞实际操作,怎么会不懂核酸?我们每天在网上浏览国外学术论文,又怎么会只知道70年代的知识?但更多数人的沉默引发了核酸专家更大的感慨:我们发现不仅老百姓要科普,专家也要科普。我们要在科技界里面倡导知识创新!
分子生物专家:打出“科学精神”的旗帜
“科学精神”成了双方争战的另一个交锋点。但这一次,分子生物学家更为投入。北大生命科学院的白书农博士先讲了一个“美国概念”:思维是逻辑的百分之五十现象。这种现象发生的基础是先设定一个前提,然后对这个前提进行推理,推理到一半时,人的思维往往就停在这里,得出结论。因为没推理完,这个结论总不会是正确无误的,比如利益的原因等等。
“这个现象也适用于这个核酸营养问题”,白书农说。
白书农倡导的科学精神是一种理性的精神。科学只是人们认识自然的一种方式,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他看来,科学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也是试错。就核酸营养问题的争战而言,白书农说可能一种观点一下子蜂拥而起,那么三五年后就又发现了新的解释,这是理论上的试错。
也许这种更倾向于学术上的争战比第一战场节奏要缓些,但持续的时间也会更长。
战场背景:国外核酸进入中国
核酸营养的问题超越了学术的范畴,超越了炒作与反炒作的范畴,上升到了国家的高度,核酸专家们自认为不是杞人忧天。从他们充满激情的言谈中,那种隐忧几乎可以触摸得到。
华东理工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袁勤生说,这种争战关系到我国核酸产业到底要不要搞的问题。而另外一些核酸专家考虑的是境外威胁。程光胜举日本做例子:我国核酸产业水平与日本相差很多,我们的核酸营养品成本高,日本的相对就低,“日本人又一向紧盯着我们的民族工业”。
黄明达更出语惊人:这不是简单的事情,是有国外背景的。他指出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国际上的核酸营养品要大举进入中国,所以先要通过某些手段弄垮国内核酸工业。这场争战只为“洋核酸”打开中国市场做铺垫。媒体被认为是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有核酸专家直截了当地说,网上那篇文章、新华社那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有国外背景的。当然,这一理论尚不足以充分证明。但他相信,“完全有这种可能”。
从这个角度而言,核酸专家们在这次争战中始终有那么点悲壮的味道,是认定争战的热闹背后,有人要将我国的核酸产业一棍子打死,他们相信有这样的阴谋。
程光胜重提了历史上的前车之鉴:关于ATP(三磷酸腺苷)的命运,就是因为这种可补充能量的东西被认为“不需额外进补”,而阻滞了ATP产业在我国的最佳发展时期,导致现在国内2/3的市场已被国外占领。
事实上,阴谋论的生成背景以及前面叙述的种种争斗,都离不开一个核心:利润之争。
核酸产业是高额利润的产业:在去年12月召开的事关21世纪核酸产业发展战略的研讨会上,某核酸类保健品厂负责人豪气冲天地告诉方福德,去年一年该企业的销售额可能就达到了2个亿!而这个企业仅是两年多来,卫生部正式审批的8个做核酸类保健品企业中的一个。正是因为成本低,利润又极高,在基本上是几十倍的暴利诱惑下,使得做核酸营养品的企业如雨后春笋,甚至泛滥成灾。方福德描述“灾害”的程度时说,很多地方胡乱弄一下便开始生产这种高科技产品,有的干脆从国外买回来再换个包装卖出去……所以那时专家们最担心的是,这样闹下去很可能就是大家都没钱可赚。
争战的过程中,受损的首先也是核酸带来的利润额。程光胜形容说,他接触到几个这类保健品厂,他们都叫苦连天。一位专家就此推理说,有些媒体看到某某品牌卖得好,十分眼红,因此不择手段给予否定。这位专家推理“眼红”的道理时说:表面上媒体与保健品厂是两码事,但谁又知道媒体背后有没有什么产业支持呢?
其实,没有了产业化,核酸专家们存在的意义也要打些折扣。所以,核酸专家们这次体现的一致对外,一再表露的“牺牲”精神就变得更加可以理解了。黄说国家对这一项目也不是很重视,他举了其中一个专家申报基金的经过,以阐述核酸专家们的艰难。这位专家第一年向学校、第二年向省里申报基金,总之连续三年都没批。最后申请成功时,又一下子拿到了三项国家基金:自然科学基金、卫生部科技发展基金、教育部中国博士后基金。申报批与不批的不同,黄解释说:不批就立不了项,就拿不到钱。
有了历史,有了可能,加之现实的漏洞,一个核酸的阴谋论基本形成了框架。
资讯
有共识的“核酸”价值
核酸在很多方面同维生素C很相像。人类所需的营养要素包括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微量元素等,核酸不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维生素C也不是。那么想想维生素C的情况,就大致可以推导出核酸的一些应用特征了。首先,核酸在日常膳食中就能大量摄取。就像想吃维C,在猕猴桃中就能大量获得一样。其次,需要核酸的人是特定的群体,比如婴儿、手术后病人等等,而不是每个人。
谁向科普负责!
记者 金焱
核酸的补与不补,根本不是一个科学难题,但偏偏就造就出一场“战争”来。也许就因为,这既是一个商业问题又是一个科学问题,两个问题纠结在了一起。
核酸被放置在了一个商业化的现实里,更多的东西以“科学”的面目出现。比如这个核酸营养问题,说穿了还是商家吆喝“科学”时过了头,吹得过了分。这事情的真相似乎科学家们都知道。但无论是不是核酸专家,谁都不去说,谁都没有站出来,让公众分享真相。为什么?
从文化传统上,北大生命科学院瞿礼嘉博士认为中国传统中有“进补”这么一说,包括中药在内,都是这样一个道理。在传统医学理论中,这种进补或许有着某种心理暗示的作用,从而达到治疗的效果,所以补养一下,是养生之道。
面对几千年祖宗留下的东西,科学家们认为应该宽容。
从现代史的角度,科学生存的土壤又起到了某种不容忽视的作用。在西方,科学文化是一种怀疑的文化、探索的文化。这种文化又是从人文文化中衍生出来的。但有趣的是,人文文化以信仰为基础。这样两种文化相互冲突,相互依存,最终形成了西方科学家崇拜上帝又信奉理性这样一个文化现象。
而科学的概念自“五四运动”传入中国,就是以工具的形态出现的。北大生命科学院的白书农博士说,那时希望变革的人们没有工具,没有资源,于是科学和民主变成了与传统文化抗争的武器。加之整个中国的现代史都是在扼制科学所代表的理性精神。于是,在这样一个文化误区中,科学一再被神圣化、甚至成了人们判断的一个标准。
“科学”这样一个外来的东西,在这样的土壤中成长,最终长成的是一个社会大众缺乏怀疑、批判精神,科学们缺乏对科学氛围的人文关注的“科学”。
时间再向前推近一步,现实社会中有关科学的机制也因东西方不同而差别迥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科学家做科普宣传被定性为一种义务,公众有权监督科学家。在科学家的头脑中有这样一个要义:他们要对纳税人负责,要让公众知道科学真相,因为公众有权监督科学家。
中国科学家的科研经费一向是来自政府,钱是由国家出的,科学家也只需要让官员知道“科学”就行了,他们只向官员传播科学知识,大众目前还不在考虑之列。
在计划经济的时期内,或许向官员传播还算勉强,但现在的“科学”更多地走进了市场,更多地成为了商品。科学与科学家在这样一个商业化的现实里,仅仅向官员传播,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