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现了白血病成因?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金焱)

误报的前前后后
2月19日那条《“豪装”可能引发白血病》的报道大体上被界定为误报。这种共识是在相关各方反复推敲了“新闻失实”、“虚假报道”和“误报”所代表的不同含义与分量后得出的。而对于公众而言,这种判断最初是来自怀疑和忧虑。
这条非头版亦非头条的新闻引起的喧哗在北京儿童医院党委办公室的电话铃声的频繁中得以集中反映:不论家中是否“豪装”,很多人都急切地询问装修与白血病之间的必然关系;高度紧张的家长们一再恳请医院为孩子做彻底的检查;更多的媒体热衷于做进一步报道;血液专业的医生同行们则更侧重于理论上的探问……奇怪的是,涉及到的装修材料公司、装修公司一类的行业倒是鲜有声音。
疲于应付这些电话的党办负责宣传工作的侯晓菊怎么也没想到医院“保护百姓”的初衷变成这种难堪的局面。她向本刊记者讲述事情的前前后后时,十分无奈:
臧晏大夫是儿童白血病专家,她爱人是做外科肿瘤的,夫妇俩常在一起交流儿童肿瘤方面的问题。考虑到环境对孩子发病的影响,臧大夫每次出门诊时除了问类似于“发烧吗?”一类的症状问题,还要问一下“你家买新房了吗?”“装修了吗?”“装修得豪华吗?”聊天时,这种医生关注环境污染,关注环保的方式让负责对外宣传的侯晓菊眼睛一亮,“这是个很好的点”,于是她约来了《北京日报》、晚报、晨报以及新华社的记者,安排了一次集体采访。
说起来,这种集体采访几乎是一次非完全意义上的新闻发布会——该院血液中心是北京、更是全国最大的儿童血液病中心,作为学科带头人的工程院院士胡亚美出任中心主任,这些确立了其在国内相关科研水平上的绝对领先地位。这个“点”也得到了诸位记者的认同,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各自找到了“新点”。这其中,新华社对此的报道《看病问环境》则被推举为体现采访意图明确而详实的报道样本。针对引起误报争议的《“豪装”可能引发白血病》一文中“来医院看白血病的孩子中间,十分之九的家中在半年之内曾经进行了装修。医生说虽然目前他们只掌握了简单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但油漆中含有的苯和大理石石材中可能有的放射性物质,确实是引起白血病和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确凿原因”这一段落,在《看病问环境》中则陈述为:
“儿童血液病专家臧晏告诉记者,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到她的门诊就诊的十几个白血病孩子中,其家庭绝大多数在半年内有过豪华装修。同时中国儿童发展中心专门从事儿童保健的老大夫王如文,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搬进刚装修好的新家后,喉部黏膜干燥和刺激,并伴有头痛、头昏、乏力、睡眠差、皮肤发痒、哮喘和嗅觉改变等症状,世界卫生组织依据大量有关资料,将此类病症状命名为‘不良建筑综合症’。……多年从事儿童白血病临床及研究的臧大夫表示,关于豪华装修是否会直接导致儿童白血病,她们还要做更多的样本积累,以后有可能的话还要做前瞻性的健康调查及流行病学调查,但身为大夫,关注环境是应该的。”
前一则报道得到的评价是:太邪乎;后一则确实平缓从容许多。
但臧大夫被媒体推到了最前沿已经成为事实。20日记者见到她时,依然能感受到她对媒体的不满。侯晓菊解释说这样一篇报道让臧大夫很难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媒体,又一次成了麻烦的制造者。
谁的过失
误报的过失有多大?恐怕在中国目前的谴责还只停留在道德层面。从科学传播的层面,则有专家指出,这种科学发现的发布程序违规。
美国科学院、工程科学院、医学科学院三院的“公关部门”曾在1995年出版了一本《怎样当一名科学家》,第二年这本小册子的中英文对照本就出来了。北大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特意提及这本比较详细的科学家的行为规范准则:“科学无国界,这种对科学家的约束也适用于中国科学家。”
在这个中英文加起来99页的小册子中,“研究成果未经同行评议,即未在专业的学术期刊发表就通过大众媒体发布与传播”的行为,与抄袭等都被视做“不轨行为”,而且医药行业因事关重大而被提出来单独表述。
在我国,这种科学共同体的审查机制也得以贯彻。科技部新闻办王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国对科学成果发布没有直接的明文规定。但如果以国家科技成果名义发布,就需经科技部或地方政府机构审核。中科院有自主发布权,由其自己内部把关。针对个人科技成果发布则还没有任何规定。”
臧大夫自身对科学的评判或许该属于个人科技成果。但其发布过程通过了媒体,就变得不简单了。有了记者的转述,经过炒点的选择,这样一个再加工的过程就使这个评判发生了变化。按理,媒体完成的应该是提高公众理解科学的一个过程,但媒体的权力过分巨大,这个科普的过程也就变了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的刘兵更看重公众科学素养的话题,他告诉记者,无论是媒体的记者,还是普通民众,其科学素养都亟待提高,“人们普遍缺少的是对科学本身进行批判的精神”。就此次误报事件,清华大学传播系的刘建明也指出,记者在采访时,为什么不去走访更多的专家?难道仅有十几个人的数据就能说明问题吗?当然,歪曲事实的报道另当别论。
但恐慌,最起码是公众的疑虑毕竟产生了。人们有点迷惑,谁来为公众安全负责?比如说,涉及“豪华装修”的问题,建筑材料安全不安全,有没有这样一个机构站出来向社会公众说明情况?而且平日似乎也没有专职机构在定期检测,定期发布有关数据。
落实到制度安排的层面上,科学与媒体的整合也需要一系列社会规则做保障。山东大学哲学系何中华指出:对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历史后果的价值评估,对医学诊疗活动及医学决定的伦理考量,对人工环境和人工产品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延迟效应和潜在效应的评价,都需要建立专门机构来履行人文约束的职能。
这是一个大众传媒手握重权的时代,但没有高度责任感的媒体,直接受到危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
资讯
“发表和公开”的负责行为
在同行评议性杂志上发表,仍然是公布科学成果的标准方法。但其他交流方法,正微妙地改变着科学家公开和接受信息的方式。专业会议的墙报、摘要、报告和文集,时常被用来在发表全文之前报告初步成果。预印本和计算机网络增加了科学交流的容易性和速度。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新的交流方法只是遍及科学的非正式交流的枝节。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加速和改进交流与修订,就会促进科学。但是,如果发表过程,无论新的还是传统的,绕过了质量控制机制,将冒着削弱已经很好地为科学服务的公约的风险。
例如,科学家在送交同行评议前,直接将重要的有争议的结果公布。如果研究者工作有错误或其发现被新闻媒体或公众误解,科学界和公众会有不利反应。这类消息公布给新闻界的时间,应该是它已经完全通过了同行评议之后,正常地在科学杂志发表之时。
——摘自《怎样当一名科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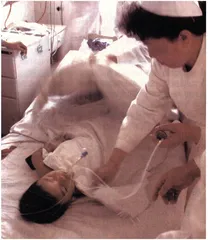
面对病人需要慎之再慎(Photocome 供图) 白血病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