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上的“电视作坊”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张春燕)
 、
、
(周辉 摄)
封钢访谈
记者:谈谈您和嘉实的简历。
封钢:我在1991年移民香港前在中央台《经济半小时》,移民香港后觉得做生意离不开本行,就和也是从中央台出去的周扬开公司制作买卖电视节目。我们公司在香港落地《新闻联播》,在内地发行《话说香港》,在香港的经历让我逐步认识到电视节目具有产品属性。1994年底回来注册嘉实,1995年正式营业,第一个节目叫《影视新干线》。之后公司发展比较顺利。
记:第一个节目的制作发行是什么情况?
封:第一个节目从策划、制作、技术、采访到开车都是我一个人。当时我自己的资金有17万,拍前十集样带需要30万,就到处借钱,借不到。我跟我父母说,我要赢了,我能还上;我要输了,我打工给你们还上。父母很支持,把养老的钱都拿出来了。节目拍出来,电视台说好,不过只能播不能给你钱。我开始寻找客户,离正式运转就两三个月,借钱买飞机票出去跟人谈判。最后宝洁公司在香港负责国际市场的朋友认为电视制作很快会成为一门新兴行业。这样嘉实做节目,广告时段宝洁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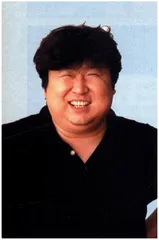
封钢
记:公司和宝洁是一种什么关系?
封:以宝洁公司的需求为先期条件,根据媒体的实际需求和情况来发展节目市场。
记:公司经营规模呢?
封:2000年公司的广告经营额在5000万,代投的宝洁公司广告有1.4亿。由于宝洁公司市场萎缩,无法跟上嘉实的发展,我们现在就开始组建全国营销队伍,做宝洁以外的业务,今年4月份开始运行,我们现在每天制作102分钟节目,相当于中央台一个大部,新闻部或经济部,我们现在有九个栏目。
记:嘉实注册的是广告公司,怎么可以经营电视节目制作发行?
封:按规定广告公司是不能经营影视制作的,而1994年的时候电视节目制作公司都不审批。我们做第一个节目十分慎重,是广电总局特批,盖了国务院的章,还跟电视台合作,走了间接渠道。去年年底,广电部会议公布将开始审批电视节目制作公司。我们非常希望尽快通过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核,得到合法地位,这对资本进入、合作、营销等等有非常多的好处。我们现在和电视台的所谓合办,是存在让利的,有经济损失。
记:您希望得到政府承认的心情很迫切?
封:市场确实需要,才有了民营电视的空间,这并不是说民营电视目前在中国成为电视媒体的主体,或占比例很大,这不可能,只是一个拾遗补缺的地位。尤其加入WTO,政府应尽快制定恢复电视节目制作公司的合法名义,甚至给以一些扶持政策。
记:公司正在做哪些发展的打算?
封:现在总是以一种变相的方式在扩张,今年年底或明年会有资本进入,那就可能要做股份制公司。扩股啊,借壳上市啊,都要学着去做。
程宏(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主任)
空间有限
目前王长田从节目内容和对电视媒体的参与程度都是边缘化的,局限在一个狭窄有限的通道里。这种制作目前来说行得通,但也十分脆弱。《幸运52》的主导权在中央台,做什么怎么做都要按照中央台的要求,风险自己承担。1999年夏骏离开中央台时正是“制播分离”呼声最高最热的时候,好些电视节目公司成立,几种体制并存,发展空间显得特别开阔。夏骏就在那个时候考虑下海足足考虑了半年,一方面看到政策形势不明朗,自由制作人和公司承包一个频道,政策风险很大;另一方面看到很好的产业前景。最后是满怀希望下海的。但是现在强调节目制作权、经营权、播出权三权不可分割,每一个环节密切联系,舆论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他们的空间和可能的空间一下缩小了。
体制外电视人是困难的,如果他们甘心于做单纯的节目制作公司的话问题不大。如果他们想要对媒体参与得更多,则没有一点迹象能表明有这种可能性。
至于加入WTO后如何抗衡国外电视媒体,广电部已经在广电系统推开集团化,进行电视台合并,内部重组、强强联合,希望建立媒体航空母舰。不管集团化的成效如何,即使在加入WTO以后,我以为体制外电视人的空间还是有限。
王长田访谈
记者:您在1999年4月以10万元筹建了光线传播,第一个栏目《中国娱乐报道》产生前后也是十分困难的,现在收视的观众已超过3.15亿?
王长田:是。1999年的经营业绩——我指利润这样实质性的东西——才几百万而已。2000年翻10倍,2001年应该翻三四倍,过一个亿吧。我们有紧迫感,正进行员工持股计划,加快引进人才。经营管理是我们的一个弱项。
记:公司结构也比以前有很大变化?
王:我们现在成立了光线电视传播有限公司、光线广告有限公司和光线时代资讯有限公司,会成为分工职能不同的独立子公司,现在还没有独立运营。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光线做成中国最具影响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娱乐和传媒公司。除了电视节目这一块,我们正做自己的网络公司,以后还要发展娱乐业,比如演出、经纪等。
记:你们和电视台也都是联合制作?
王:是的。《娱乐现场》以前叫《中国娱乐报道》,就是和北京台联合制作的,电视台有七八个人,制片人和监制都是他们的。这种分工是正常的,把关、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协调节目事宜他们都做。当然我们也只能这样做,因为我们的节目要从他们那里出口。广告利益是好商量的,我们有我们的利益,他们有他们的利益,节目做好了有共同利益。
记: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王:很难想象这么长时间我们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大问题没出过,连中等的问题也没有。我们中不少人都是从电视台出来的,政策的信息传达渠道也比较畅通。
记:资金是不是困扰你的最重要因素?还是其他?
王:资金已经不是最大因素,早期是很受困扰,没法贷款,借钱。现在资金根本不是问题,有大量资金准备进入这个行业,保守估计也有三五十个亿,光指电视节目内容这一块。起码有40家以上单位找上门跟我接触谈合作,很踊跃,但都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市场也不是大问题,目前市场处于迅速增长的状态,应该不会有大的起伏。我觉得最受困扰的还是政策的不确定性,不能说国家在限制这个行业,但国家也没有鼓励这个行业,我们在有些方面不敢下大决心。和资金的合作也不敢具体谈,要看看政策的走向。
(图片均为本刊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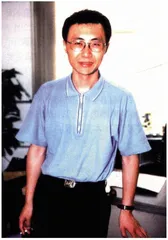 王长田
王长田
金文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收听收看中心副主任)
加强监督、规范市场
最早在1998年,中央电视台一个制作部门的负责人提出制播分离。结果《北京青年报》报道说中央台要实施制播分离,除了新闻以外中央台将只是播出机构,要大量裁员,打破铁饭碗。报道引起广电部注意并且大为生气,最后北青报向中央台道歉了事。
但随后,制播分离的讨论呼声越来越热烈,广电部也觉得这是一种趋势。去年,中央台都已经讨论出台了制播分离的方案:在三年内完成8套(影视剧频道)和5套(体育频道)的制播分离,逐步实现独立的公司化运作。
制播分离的提出和兴起,除了学习国外的电视媒体经营模式,也从中央台《东方时空》的运作中尝到了甜头。《东方时空》的正式职工有限,其余全是社会招聘,管理体制上有很大的市场化运作成分,对克服体制障碍,解决机构臃肿有启发性意义。
现在我们不说制播分离,但制播分离的运作模式还在运用和借鉴。目前的任务是要加强监管、规范市场。2001年要出台资格认证制度,制片人资格认证和主持人上岗证,都要由广电部认证,从源头上来控制。在建立规范有序的市场和有效的制度后,其他的就好办了。
资讯
缘起与发展
●1996年,北京嘉实广告文化发展公司成立并开始制作电视节目。相继推出《影视新干线》、《新闻故事》、《相约星期六》、《中国流行音乐雷霆榜》、《中国娱乐特快》等代表性节目。
●1996年6月,原《中华工商时报》记者王长田以10万元借款组织起《中国娱乐报道》,先打“市级牌”,播出台由30家迅速膨胀到200多家,激起了娱乐界千层浪花。不久又推出《世界娱乐报道》、《中国音乐风云榜》、《娱乐人物周刊》和《中国网络报道》等一系列电视栏目。
●2000年6月1日,北京银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改版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大约有上千家专业电视节目制作公司,新出现的公司每年以将近100%的速度递增。
机制与形态
身份
与自由撰稿人一样,从事专业电视制作的群体常常在拍摄人物或者新闻题材时受到对方的盘问和怀疑。他们是一群没有娘的孩子,还经常处于不见阳光的地带。他们的脖子上没有电视台的采访挂牌,也不能代表影视公司签订什么具有法律效应的合同,他们也当然不领取“三金”、“四金”。
财富
与吃皇粮的电视台一比,他们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显得相当遥远。前期的赢利不得不用作追加资本。
形式
初期以广告、文化公司名称出现,实际上从事的是电视制作。后期直接成立如制作部、广告部、技术部、媒介部等较为系统的电视制作公司。
重点题材
依次为娱乐、时尚、企业(经济)、历史、网络、地理、人文。
谋生手段
花色繁多,有时靠“打擦边球”。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其一,为某广告公司制作电视广告,宣传某产品形象。这部分收益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二,为某电视台打工,但处于体制外,他们被传媒称为“两栖人”。目前,给中央电视台打工的不少人都属于此类型。其三,包揽某电视栏目的创意、内容制作,节目免费送给电视台,然后在广告时间上与电视台分享。这种形式被普遍采用。
(摘自瘦马《产业化格局中的中国电视制作潮》) 节目制作王长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