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世同堂到夫妻生活
作者:王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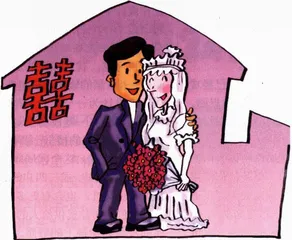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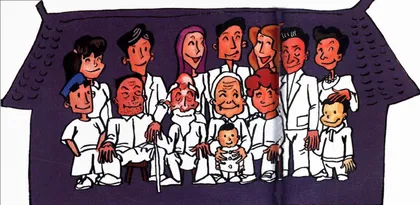
衰弱的大家庭
老人是维持赵家上下三代7家25口人最重要的纽带。因为她的健在,赵家的大人孩子都要在周六聚到北京崇文区新世界商城后面的四合院里。叔伯辈的自然在一起打打麻将,青年一辈的聊天,孩子们就在院落里追来追去疯玩。
老人已经84岁了,平日只是一个安徽的保姆陪在身边,到了夏季屋子太热、冬天太冷的时候,她才肯让儿女们依能力逐个地接到家中住上一段。在这样共同孝顺共同娱乐的日子里,大家结成了一种亲密关系:今天二舅住院了,大姨三姨的孩子们就会轮流到病房去守夜;明个大工厂裁员几个侄子面临下岗,大伙就得帮忙联系出路……困难和喜悦都是大家庭的。
老人有多大年岁了,这种大家庭的关系就在北京城里保持了多久。不过是从1980年前后,成家的儿女们各自分到房子,这个破败的四合院才显得不再那么拥挤不堪了。老人眼神已近于失明,但总算看到了第四代重孙的出世。再过几年,人去房拆,真不知道一大家子人在什么地方以什么理由固定地聚在一起。
毫无疑问,关系总会慢慢淡去。这一规律不仅发生在赵家,也发生在很多传统中国的家庭中。有调查显示,自1985年以来中国家庭的户规模一直呈明显下降趋势,至1997年,全国家庭平均户规模已由1985年的4.79人降至3.64人。“四世同堂”式的家庭结构越来越让位于一对夫妇的核心家庭,这样的变化也必然导致了住宅由内闭、独立合院方式向分户型的改变。
感情是第一位的
李银河的个案调查可能更能证实这种变化。2001年1月8日,由她撰稿的《一爷之孙》即将出版。书中以一个繁衍了6代、有着58个同姓后代的家族为观照,从夫妻、妯娌、子女等多种角度,研究了传统的大家庭如何一步步地走向分裂的过程。“在前现代化的社会里,中国扩大式的家庭或者说联合家庭是以亲子为重心的,在这个纵轴上,夫妻关系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强调的是上尊父母下为孩子,所以即使夫妻两地分居,妻子也会在家尽义务。”李银河说,“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再这样可能就悬了。核心家庭的生活模式强调夫妻为重心,以横向为轴,感情的份量就会上升,夫妻感情好不好、有没有话说都变得很重要,甚至能决定是否要继续过下去。”
离婚率、再婚率的持续上扬,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入们更尊重自己的内心,不再纠缠于对父母、儿女的道德责任。李银河另有一份关于丁克家庭的调查,“选择自愿不育这一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占第一位的是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忧虑;第二位是为了使自己生活得更轻松;第三位是为了自我实现”,更是这一事实的表达。
更为有趣的是,李银河发现,以往的传统,家庭内部长辈、上下、尊卑意识、男女有别、内外有别,等级分明,甚至都表现在居住形态之中,“四合院里,要分出老爷、太太住正房,儿子儿媳住厢房,妇女住内院,客人住外院,仆人住罩房,这些房子高度上有差别,正房最高最宽敞,处于统治地位。现在哪有这些讲究?家庭成员平等多了”。
经济实力无疑决定了一个家庭成员的权力。在按资排辈分房子的年月,年轻夫妇大都住在父母家中,到了自己挣钱买房子的时候,怎么住就自己做主了。聪明的地产商们也看到了这一点。“三代同堂,尽享天伦”是上海锦秋加州花园房地产公司打出的一个宣传口号,他们发现,很多年轻夫妇,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都希望能与父母住得近点,“锦秋加州”的户型,就加入了三代三层的设计理念——一层作客厅,二层是孩子和老人的卧室,三层留给夫妻俩。
两个人的房间
在越发看重私秘性的今天,“锦秋加州”的设计能讨巧吗?这个答案未见得乐观。
把家新落在北京万泉新新家园的刘佳琦,就是从这种模式里解脱出来的。几年前,她和公公婆婆一直住在一个小区的前后楼的两套房子里。“我自己的家永远就像是宿舍,基本的待客、吃饭都在老人那边。”刘佳琦说。由于孩子小,老人带着,一日三餐就成了一种尊敬老人、亲近孩子的必要仪式。在这种外人看来共享天伦的模式里,为着老辈人的操心和惦念,佳琦夫妇常常为有没有照顾到老人的生活方式满心的罪恶感。刘佳琦说:“我本来是个很好客的人,可是如果把朋友请到家里来,在长辈面前总得讲究礼节,这样又没意思,干脆不请朋友到家来了。”
当有实力重置房产之后,佳琦夫妇决定带着7岁的孩子搬出来。为了在文化公司忙忙碌碌晚归时不要老人操心,为了酣睡的早晨不再被老人善意地叫醒,为了和更忙碌更无序的老公有一个纯粹放松的空间,刘佳琦买了一套带楼梯的别墅。“带楼梯的屋子总会给我更多的幻想,生活好像更有趣了。”刘佳琦说,“女儿要一间,保姆有一间,我和老公一人还得有一间书房,一定得各自有一间!”
“我是喜欢舒适的人,可我老公喜欢一切中式家具,硬梆梆冷冰冰的太师椅放在客厅里,电视机还要加个木柜子,搞得我特别不爱在客厅里呆着。要是没有书房,就只能在卧室里打电脑,可我老公又不愿看到卧室里还像办公的……”佳琦说,她跟老公合用一个书房也会十分麻烦,“他是酷爱读书的人,我的东西要搁在他那里,没多久就得淹没了。我自己要有个书房,东西放哪儿都知道,而且还不被打扰。”
不被打扰的空间还包括浴室。没有了父辈们审视的目光,浴室也许是心灵的栖息地,“我非常非常看重浴室的感觉,要有很大的镜子,有踩上去柔软舒服极了的浴室垫……”
屋外还有花园。刘佳琦还在早春的3月,就迫不及待地带着女儿往地里撒花种,到了夏天,园子就是一片片的花,老公就是这片成果的赏玩者。她觉得这才像是家。
历史学家对家庭史的研究说:家庭将人划分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和行为不同的社会阶级,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直接产物。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形成,他们的家庭特点是坚持公共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的分离,增强对“内务”的关注。这种观念对文化、传统、宗教、政治制度各异的国家,几乎同样产生影响。所以有先进意识的开发商们、建筑师们在设计建造相应的居室时,都在此大动脑筋,使得居室显得对外更具备私秘性,而对内则加大开放性。使居住者的生活理念得以在此发挥,真正改变生活的面貌。
房子中的人
为夫妻带来感觉的是房子吗?抑或是我们生活的经验、我们的自由选择改变了房子中的人的相处方式?
“一直以来,房子本身的结构类型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真正对夫妻的感情质量起影响作用的是面积。跟父母住三室一厅,一对夫妻住三室一厅,或者三对夫妻分享三室一厅,那生活状态绝不会一样的。”家住龙城花园的自由撰稿人林鹤说,“两个人要想保持好的关系,必须要有足够多的弹性空间,不光是心理空间,还有居住空间,否则在一间屋子里为一盘破咸菜生了气都没处躲。现在很多观念的转变说到底就是因为有所选择。”
为了有独立的空间,学建筑出身、去过日本的地产商刘建忠把他钟情的日式榻榻米移植到家中,在餐厅与阳台结合处加上了一道推拉门,茶饭之余那里就是他静思、下棋、会好友的独立一隅;摄影师周立在装修时发掘了卧室天花板上的空间,对于阁楼的想象转换成了一个楼梯上下的工作,像妻子的厨房一样,这里是他的世界;还有人的心情在大露台上,可以张合的玻璃棚顶,成就了夏天的吧台、冬天的躺椅……一切可利用的地方都是为更有趣、更放松、更赏心悦目的家庭生活。
“其实你可以从厅与卧室的结构变化看出人们对于生活的要求的变化。”刘献忠说,“以前的房子,各个房子的门几乎都是开在厅里的,进进出出的状态一目了然,长辈就是厅里的重心。这种设计非常不好,没有什么对隐私的尊重。现在一般都把厅和其他房间分开,卧室有卧室专门的通道,不必经过厅,而厅就是会客、娱乐的地方。”
“理想的住宅还得强调功能的细化。而且有吸引力的家要提供更多可以改造的余地,那怕是一个主妇拿着一把改锥都可以让家里的环境不时变化。有了细节的变化,家就总能保持一种新鲜感。”刘献忠说。
他提到了新鲜感。所有的设计都在为新鲜感而努力,在不断变化推陈出新的今天,包括男人、女人在内。一份在51所高校进行的调查说,中国人择偶中的经济成分在加大,物质的中介因素作用正在增强。 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