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可汗》,宝莱坞导演的世界梦
作者:李东然(文 / 李东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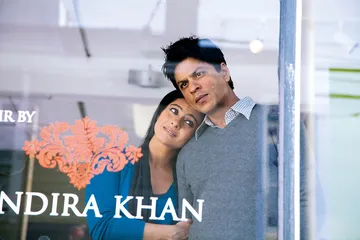 ( 电影《我的名字叫可汗》剧照 )
( 电影《我的名字叫可汗》剧照 )
来自印度的阿甘
其实故事非常简单。影片开场在美国圣弗朗西斯科机场,飞往华盛顿的主人公可汗等待接受登机安检,在后“9·11”的美国,这位长着南亚面孔,有着穆斯林姓氏,且嘴里不停诵念经文的男子,自然会得到异常严酷的“处置”,“He's clean”的结论没能让可汗赶上最后一班航班,偌大通明的深夜机场,他形单影只,漫漫前途上唯一支撑他的是要见到美国总统的坚定信念。
接下来的2小时25分钟里,围绕这段艰难的“上访”,主人公的人生故事渐次展开。出生在印度中下层市民阶层,随弟弟来到美国,自我奋斗,收获爱情,实现人生,直到“9·11”改变了一切,继子因“可汗”这个穆斯林姓氏带来的偏见而惨死,妻子无法面对丧子之痛,离开了可汗。为了挽回爱情,他必须完成妻子的要求,去告诉整个国家的人以及美国总统:“我的名字叫可汗,可我不是恐怖分子。”
化这一切腐朽为神奇的,是主人公的精神疾患——阿斯伯格症,维基百科上的定义是主要以社会交往困难,局限而异常的兴趣行为模式为特征的神经系统发育障碍性疾病。倒是有“印度汤姆·克鲁斯”之称的宝莱坞影帝沙鲁克·罕(Shahrukh Khan),也就是电影里的“可汗”给了我们一个更易懂的解释:“比如说你完全能理解‘我想飞向你’这句话的意思,这代表我深深地爱着你,想飞到你的身边。但是对于阿斯伯格症患者,他会觉得,我们不会飞啊,那你又如何能飞向我?”
有趣的是,以刻板呆滞为特征的阿斯伯格症候人群,似乎总能得到电影创作者的偏爱,比如,无论批评家,还是普通观众,不约而同地把可汗说成“印度阿甘”(《阿甘正传》),影片导演兼编剧卡伦·乔哈尔却说:“可汗并不等同于阿甘,两部电影的主人公有一定意义上的相似,但想一想,你就知道这并不是事实,阿甘是完全符合并巩固美国社会结构而存在的角色,但可汗是一个美国社会结构之外的存在。”

的确,阿甘的人生里,牢记着妈妈的话:“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打开之前你无法知道会吃到什么味道。”可汗的母亲却让可汗记住:“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好人和坏人。”这是一部站在印度人角度,解决问题面对困境的电影。“你知道,印度是一个绝大多数人口信奉宗教,且本身存在着宗教分裂的国家,宗教不仅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也根深蒂固地决定着我们的思维和判断。我自己常常觉得,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退回妈妈小时候告诉你的那最最基本的判断法则,但实际上每个人从出生,肤色、宗教、教育,我们的一生几乎都在无数偏见的影响下走过,或多或少地偏离了生命本真那最美好的轨迹,也因此丧失了爱和快乐。我很想要呈现一个人物能够毫无偏见,面对复杂的世界,也能站在原点去思考,这是非常理想化的人生状态。”卡伦·乔哈尔告诉本刊记者。
面对世界的严肃话题
导演卡伦·乔哈尔是如今宝莱坞最负盛名的电影人之一,父亲是印度著名的电影制片人,成立了大名鼎鼎的Dharma Productions制片公司。乔哈尔出生成长在孟买,最初以演员的身份入行,导演处女作《怦然心动》,就请来沙鲁克·罕和卡卓尔担任男女主角,并在当年的印度奥斯卡上大获全胜,赢得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和最佳男女配角8项大奖。从此,不仅身为导演、制片人,甚至也是当地电视名人,《永不说再见》、《花无百日红》,一部部浓情卖座的印度爱情电影火速将他推上宝莱坞最一线电影导演的位置,
虽然宝莱坞的电影年产量可达千部之多,但如“可汗”的题材,绝非电影生产的常态,乔哈尔说,催促他把想法付诸现实的是“9·11”事件。他发觉,困在文化狭隘与误解之痛中的不仅是印度,这种灾难正像是疾病一样,蔓延到了整个世界。“‘9·11’几乎可以说是瞬间把整个世界分裂成为两个极端二元对立的部分,很多生活在美国的朋友、家人,开始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诉说他们的遭遇。大部分的西方社会把伊斯兰教当做魔鬼,虽然我并不是伊斯兰教的信徒,但是这种偏见,无论从电影创作者的角度,或者是一个人的角度,都使我感到不安。”
乔哈尔笑言自己是到了一定年纪以后,风花雪月的电影就开始做得麻木。“开始思考如果不去凭我内心感觉做一部电影或者有社会责任感地去说一个故事,就没有真正对得起给予我人生成就的这个产业,这样严肃而现实的话题,本身也是让印度电影真正面对世界最好的机会。”他说。由此找到合作熟稔的编剧,专程飞到美国,走访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和数不清的村镇,拜访了当地穆斯林组织,甚至真的结识了一位患有阿斯伯格症的穆斯林男子。
“那些用石头与瓶罐丢清真寺,破坏穆斯林商店,霸凌穆斯林孩子的事情,都是真实存在的,很多真实的状况伤感到让人无法写进电影。那时我体会到,如果透过某人牺牲某样事物,向一个困惑与受伤的国家传达宽容的信息,或许能带来影响。我给剧本定下卑微淡定而平铺直叙的路子,我知道,这将是一部完全不一样的印度电影。”乔哈尔说。
电影里,可汗被美国安全机构当做恐怖分子,接受凌虐的处置,但他没有用仇恨解决问题,反而把满心的爱和善意化作行动,感化他身边的美国人。乔哈尔说:“借用可汗的卑微,我希望人们能理解,你不能要求全体人为少数人的举止负责,呈现这卑微与善意不止是希望让美国人接收宽容的讯息,也希望影响到对彼此仍存有偏见的全球印度人。我理解一部电影很难改变别人的内心与想法,但电影能引发对话,有时候,你只需要点燃火种。”
实现世界梦
“通常,印度电影难以逾越宝莱坞的定式,作为印度导演,我深知这和我们民族的内在情感方式息息相关,也并不想否认其存在价值。但是‘可汗’是一部建立在现实之上的作品,所以通常印度电影中的歌舞类浓艳表达方式我运用得相对谨慎克制,并且作为电影人,我还有另外的期待,这是一部要去面对整个世界的电影。”乔哈尔说。
为了最大化实现自己的“世界梦想”,乔哈尔做出了另一个重要选择——主动与好莱坞谋求合作。“因为我想要向整个世界传递某种信息,我想要创作一部全球化的电影,那么我觉得最便捷的方式就是通过国际化的大公司去完成运作。你知道,这几年好莱坞制片厂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计划面对新兴电影市场,孟买建起一座又一座好莱坞制片厂,我找上门去,幸运的是,我们不谋而合。”
事实上,“好莱坞与宝莱坞之间合力共赢的范例,近年来屡见不鲜,尤其叫人难忘的就是2009年奥斯卡颁奖礼上,一部故事取材于印度外交官维卡斯·斯瓦鲁普的小说《问答》的电影。影片取景在孟买街头,演员全部来自宝莱坞,且大肆渲染印度歌舞特色,制作成本仅1500万美元左右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摘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电影剪辑、最佳摄影等8个奖项,成为当年奥斯卡奖的最大赢家,其实在此之前,这部电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狂卷1亿多美元,是当之无愧的‘黑马’”。
面对“合作”,作为宝莱坞中坚一代的乔哈尔导演态度是满心的乐观:“宝莱坞的形成是植根在印度社会印度趣味之上的,适应印度社会机制的电影传统,并且我们已经很好地走过了50年,无论是观众还是创作者,我们不可能舍弃自己的电影趣味,所以好莱坞公司来到印度,在宝莱坞的中心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制片厂。但是,在我们看来,好莱坞的本土化策略也是如何适应印度宝莱坞的机制,而不是相反的方向。”“越来越多地和好莱坞的接触,因为我们看到对方体系中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比如好莱坞对剧本的钻研态度,对于电影全球化营销的掌控,并且合作提供给印度电影走向国际的突破,积极主动,因为我希望可以在合作中收获前进和成长。”■ 我的名字叫可汗名字世界导演剧情片爱情电影宝莱坞印度电影可汗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