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老外”朋友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姜波(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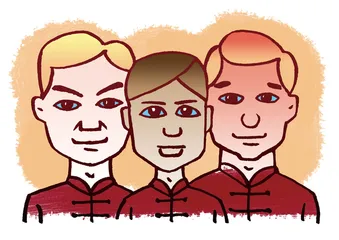
在研究所工作,担任海归科学家的助手,面对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项目,总有零星的“老外”进进出出,我出于职业道德和乐于助人的心,免不了帮他们忙这忙那,时间一长,自然成了好朋友。有时闲来无聊,想想一起共事的三个“老外”,总觉得他们的众生相在凡事皆可能的中国背景下,比中国人本身显得更有趣。
尼奥是印度人,副研究员级别,快奔40岁了,到中国已经5年,老婆女儿全都在北京陪伴。他的工资和同一级别的中国人无差,只是没有福利和保险,唯一可以享受的是在单位医务室拿药可以报销85%,但是由于他几乎不讲中文,估计也从来没有去拿过吧。有时他也抱怨一个人的收入难以支撑整个家,小孩老婆也没有福利,每到这时,我就无能为力,只能听他倾诉。他老婆才到中国时在幼儿园教英文,后来由于每到冬天忍受不了北京的大风和低温,必将请假回印度保暖,工作岌岌可危;再后来,更多“更英语国家”的“老外”纷纷到北京掘金,她的位置也就彻底被替代了,只能回家带小孩。他们的女儿生得可爱,基本上出生以后就在北京长大,上的单位幼儿园,去年还说得一口京片子,天天唱“北京欢迎你”。听说她妈妈带她回印度过冬时,每次回去都要先自闭一段时间,默默想念北京。妈妈教她画印度国旗,她却坚持认为五星红旗才是她的国旗。父母的失落之情难于言表,一致决定让她接受国际化的教育。可是在北京,国际学校的价格令人咂舌,家庭收入也很一般,名校也就不要想了,最后去了印度大使馆附属小学。最近再见,女儿越发可爱美丽,只是再跟她讲中文时,她显得有点茫然,俨然不是那个地道的北京小丫头片子了。不过好歹生活在中文的大环境中,长大后,小姑娘应该能够说着地道的中国话解决各种事情,保护不讲中文的尼奥夫妇。
马克西姆是俄罗斯人,今年才24岁,年轻俊美,而且已经拿到博士学位,让这边一大帮大龄且憔悴的博士生愤愤不平。他因为一个原定两个月的短期项目而来,哪知道他慢慢磨,尽管课题组长不甚满意,但依旧对他未来的成果充满渴望,还是不得不每三个月帮他延一次签证,一下就是两年。去年临走时,用马马虎虎的中文一字一顿地背出他的临别台词:“中国的年轻人都很努力,很勤奋。”毋庸置疑,是句大实话。他不仅在中国做科研,也颇有俄罗斯倒爷风范,回程不惜花上三天三夜搭乘远东国际列车,只为将从雅宝路批的100公斤假名牌能免费托运,拖回家乡换钱。今年春节后,北京还在飘雪,他突然出现,摇身一变成为博士后,拿着外国专家证和工作签证,又名正言顺地返回来工作,不变的是他依然很慢,依然怡然自得。想来奇怪,中国博士研究生的梦想都是去美国,而他不止一次地选择中国。后来我判断,对于只有在中国和俄罗斯有生活经验的他来说,中国人满脸自信,安居乐业,又总有很多类似秘诀的东西让他着迷和安稳,加之俄罗斯人对于美国独有的气节,中国成为他的首选,但是他也不否认应该会有一天返回俄罗斯做点什么,这大概也就是我们说的曲线救国吧。
雷恩是美国人,29岁,今年夏天拿着美国政府的资助来这儿做项目,共计三个月。一到中国,比中文更让他头大的问题就是iPhone失效,最终刷机没有成功,只能借了直板手机,买了中国SIM卡重新来过,他感叹:“我已经想不起来这种手机怎么用啦。”不过他依然每天携带iPhone。某天,他向我学习某句中文,我还在思量时,只见他使劲摸了几下屏幕,就有标准的男声发音,围上去一看,中英文词条清晰呈现在光亮亮的屏幕上。刹那间,我很惭愧,作为一个中文母语使用者竟然敌不过iPhone的速度,也让我相信这个不会讲中国话的美国人靠这个大概走遍中国没问题了。雷恩很怕这三个月转瞬即逝,一方面想做出点东西回去给美国导师交差,一方面又要挤出时间好好探访中国的大好河山,于是每晚干到零点,连续数个周末自行游玩了北戴河、青岛、上海和黄山,代价是体重比他才到中国时已经轻了3公斤。眼看三个月期限将到,由于不知道科研突破的那个奇妙时间点能不能如期将至,为保险起见,他已经在思考项目的后续发展。不过他考虑的不是让自己留下来频繁更新签证,而是他发现我们这儿的人力资源很旺盛,可以将他的工作分给这里的中国人做,而他仅仅需要写信给他的美国老师和我们的课题组长,促成他们的合作意向,这意味着双方各自可以在本国申请更多的经费,相信没有傻子想拒绝。
不知这些“老外”们会在中国待多久?是否只是匆匆过客,他们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吗?一切未知,因为在中国,一切皆有可能。■ 朋友三个老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