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晓东:看不到电影我就拍一个
作者:王小峰(文 / 王小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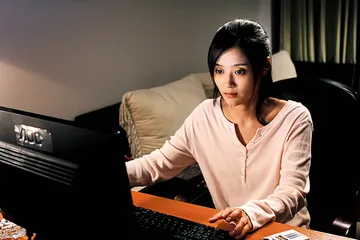 ( 电影《无形杀》剧照
)
( 电影《无形杀》剧照
)
谢晓东去美国后有件事对他触动很大。在北大上学时,学校搞西方流行音乐讲座,当时形容“披头士”乐队是“扯着嘶哑的嗓子唱着颓废的歌”。到了美国,他租了一盘“披头士”的录像带,想看看这个当初被形容的颓废乐队究竟是怎么回事。看完之后,谢晓东有点傻,约翰·列侬死的时候,当时的苏联都降半旗志哀,整个西方社会的一代人都受到了“披头士”的影响。“当时我就哭了,觉得在中国生活得太惨了,这20多年怎么活的。然后在那看了很多各种类型的电影,我当时觉得很刺激的,就是电影里面的那种构思精巧的东西,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喜欢上了电影。”谢晓东至今回忆起这段经历还有些感慨。
事实上,谢晓东在美国的经历和他最初的人生规划差不多,毕业后到药物公司做研究,研制一种叫GLIADEL的抗癌药。“我2000年看中央电视台的《科技博览》,看到我研制的那个药了,说GLIADEL上市。当时我太兴奋了。我离开美国时,这个药已经进入了美国药监局的第二阶段,就是动物实验都结束了,要进入人体实验阶段。为什么很幸运呢?因为很多研究人员在做药,但可能一辈子都做不出一个药来,而我碰到的第一个药就顺利上市了,这就很幸运。”
1993年谢晓东被美国一家公司派到中国做化工企业,这时,他还没有想过会跟电影有什么瓜葛。但是回国后他就发现,看不到电影,这让他很苦恼,那段时间正好是中国电影最没落的时候,那10年间电影非常惨淡。虽然当时还可以看到光碟,但是屏幕小,没有观众坐在一起观看的氛围。“那时候出国开会或者度假,我就拼命看电影,跟饥渴似的。说实话,当时也没有什么条件说想要自己去做电影,因为我还要创业。”谢晓东说。
谢晓东想过拍电影,但是当时没有院线,拍出来的东西怎么挣钱?没法挣钱就意味没有人给你投资。直到2004年,当私营公司可以允许从事电影发行时,谢晓东才开始试水,“我觉得只有把发行渠道弄清楚,知道市场回报的方式是什么,那么你才能跟投资人谈回报渠道是什么”。
2006年,谢晓东开始琢磨怎么去拍电影,他既是编剧,也是制片人,这在电影界还不多见。“我觉得这个市场我摸到一定规律了,能大概齐做什么。我2006年写剧本,2007年春节开始拍《一年到头》,这是第一个片子。《一年到头》以春运为背景的三组人物勾连,一个是城市民工,以装修工为代表;一个是重点高中的校长;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内科主任。涵盖了中国典型的城市三组人群,或者说三个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和民工问题。我做电影,喜欢电影是因为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说话平台,对社会的关注基本上是我的影片的唯一宗旨,所以基本上每个片子都是以一个社会大背景为主要特征的。在中国,这种电影现在非常少见。原因可能是电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边缘化了,从业人员基本上没饭吃,或者干其他行业去了。剩下这些人基本就活在这个圈子里头,很小很小一个圈子,没什么生活阅历,所以编出来的故事我认为没什么意思。这可能是我的作品和别人很不一样的地方。”
 ( 谢晓东 )
( 谢晓东 )
谈到《一年到头》,谢晓东说:“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中国社会基本上没有一个明确的宗教信仰,从历史上来讲,就没有一个真正决定因素的,或者决定性的宗教。宗教的有和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它给了人一个死以后的奖励和惩罚。中国缺乏宗教,那是什么使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整个社会几乎处于一种超稳定的状态?包括到了国外,几代人下来依然在一起,这里有一种相通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什么?这使我挺好奇。后来我发现,是亲情,这几乎是唯一的,对中国人普遍都适用的一个因素。所以我找到点了:拿春运做背景。我设置了这几组人物。民工,民工是所谓大家觉得最不需要的人,春节大家都回家了,当你们家的房子装修一半时就需要了,这时候民工成了最抢手的人。重点高中的中学校长,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上个学想要去重点高中,要花钱,要找各种关系,和这个校长要搭上边。校长看似一个无所不能的人,因为你得求着他。可是他也有求人的时候,所以我把这个校长弄成这样:他的孩子在美国打拼,这个春节要回来探亲,房子需要装修,等儿子、儿媳妇带孙子一起回来。这个时候民工就很重要了,得求着他,你千万给我完工。交房的时候,因为材料是假冒伪劣的,管道又裂了,水喷了一地,校长就崩溃了,心脏病发作,给送医院去了。这个医生面临一个问题,他的孩子要考高中,满世界找人,因为不认识重点高中的校长。正好校长给送进来了。医生同时还有一个问题,他爸爸80大寿,想见孙子,可是孙子要考高中了,他老婆死活不让去,要为孩子前途着想。他需要车票,就让民工去给他买票,就是这么一个集合体,通过这种线把他们三个群体连在一起。”
谢晓东写的第二个电影叫《无形杀》,跟网络人肉搜索有关的题材。这个故事的由来是一个网络人肉搜索事件,他说:“大家都喊人肉搜索‘小三’,谁给你的这个道德审判权了?在我们这个社会你凭什么有道德的审判权?这个事我觉得有意思,大而化之的东西就是说,当你觉得你有审判权,可以歇斯底里的时候,我觉得希特勒不就是这样么?希特勒长时间的歇斯底里,整个国家就变成了歇斯底里,德国人本来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民族,却变成一个非常感性的民族,像疯了一样。这个也是初始的一个想法。另外,对于数字化生存,我们准备好了吗?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所谓的信息化社会,仅仅十几年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间杂着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整个道德判断、行为规范全发生了一种不知所措的变化。我很关注这些,所以设计了一个故事,把故事变成一个悬疑片,然后包含了这样的关注,是这么一个过程。”
 ( 电影《一年到头》剧照 )
( 电影《一年到头》剧照 )
当然,最让谢晓东得心应手的是他今年拍的电影《我是植物人》,这个题材恰好跟他的专业有关。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中国药监局局长郑筱萸事件。“我以前是做药的,我太知道做药的艰难了,做药真是千锤百炼地筛选出来的,因为我们人体是如此复杂,某种意义上讲不可理喻。美国做一个药,背后投入是数以亿计的美元和很多年的时间,要毙掉甚至上千个药,才能出来一个药。美国每年通过的药可能也就100多个。这个数据什么意思呢?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默克公司一年的研发投入,可以把整个中国的所有药物公司给买了。2005和2006年中国通过药物的数量是一年一万多种,他们只有十几个人,就光看一个药的备选资料,12分钟也看不完,但就能通过一个药。一万多种,我们有没有这么多研发人员和研发投入?这怎么来的,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这事让我出离愤怒。2007年郑筱萸被判死刑,我觉得罪有应得。我想写这个黑幕,但写的过程中,三鹿奶粉出事了,包括整个奶粉行业。让我愤怒的东西就在于:人总有底线,你要是完全没底线这个社会太可怕了。你说孩子他什么也吃不了,他这么一小肠子、小胃,只能喝奶。然后你每天给他灌这个跟结石一样的东西进去,他什么也消化不了,这就等于杀人。再说药品,这病人之所以吃药是因为有病,他没病吃什么药?你给他吃的是假药,这跟杀人无异。在青岛,我问出租车司机,怎么看郑筱萸这事儿,他说您贪就贪点,你不给我们干好事,但是别害我们呀。这话听得我直哆嗦。”
想好了核心,还要有故事,平时谢晓东喜欢看新闻,他发现,河南产的含有苏丹红的辣椒粉不会销售到河南境内,他们卖到外省,但挣的钱他们给孩子买三鹿奶粉喝。而生产三鹿奶粉的员工告诉记者说从来不给孩子喝自己的奶粉,都是喝进口奶粉,但是吃的苏丹红辣椒粉是河南产的。这是一个互相不断加害的过程,这启发了谢晓东,《我是植物人》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轮回:一个人成了植物人,醒来以后,她的记忆部分消失了,不知道自己是谁,她再融入这个社会的过程中,需要知道自己是谁,寻找记忆的过程中,她发现了造成她成为植物人的是一种麻醉剂,她准备起诉这个药厂,在她起诉过程中记忆在逐渐恢复,有一天终于恢复记忆,发现在她变成植物人之前,就是伪造这个药品通过令的人,伪造数据,花钱买通过令的人。
谢晓东喜欢拍费力不讨好的现实题材电影,在他拍过的几部电影里,都能看到其他导演不愿触及的领域,电影没有太多的噱头,至今没有在商业上获得很大反响的电影。谢晓东说:“我从开始就没有把做电影当生意来做,我只希望它不给投资人赔钱,或者单部影片中能把钱给赚回来,所以我没有把电影作为一个企业行为。如果做企业要挣钱的话,我真的不需要这么挣钱,我自己所学的专长,挣钱的方式比这简单得多。我研究一个产品出去卖了,挣钱很直接。而电影,从剧本到拍摄到发行宣传等这一系列的东西做下来,赚点钱,我觉得太难了,也没必要。另外电影本来就需要很多的种类,我做的电影也是电影一种,这种电影在好莱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种类,所谓的现实主义或者批判现实主义影片。奥斯卡每年获奖的片子基本都属于这类。冯小刚和张艺谋他们做的影片不是我感兴趣的。”
谢晓东认为自己没有进入娱乐圈,他每天的工作时间一半在企业,一半在电影上。娱乐圈是个名利场,人本质上就是想要名和利,只有娱乐圈能给他们提供这个。“做企业,你只能有利,不能有名。你要是有了名,离死就不远了。很多的财富榜上的富豪都完蛋了,因为他又有钱又想要名。你做政客,你要有名,但不能有利,要有利的话,离死也不远了。当然在中国特例还是比较多的。只有娱乐圈可以达到这程度,但是我不是娱乐圈的人。我喜欢电影本身,因为它给我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借这个东西满足我天性中爱编故事爱发言的喜好,对社会有自己的看法,对事件有自己的看法,这是我选择做电影的一个根本的原因。那么艺术电影,所谓的在国外获奖的那些东西,更不是我所看重的东西了。”
中国现实题材电影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电影审查不易通过,现在电影投资越来越大,投资方的压力使他们在最初策划时就规避了审查风险。但谢晓东又不靠这个吃饭,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包袱。“我的每一部片子在送审之前,听到的最多一句话是‘能通过吗?’这是一个挺有趣的问题,因为中国电影审查条例没有一个特明确的线,所以大家只能揣摩。大家伙儿为了有饭吃,根据揣摩,给自己再加道箍,我比你要求那个范围还小,这不就安全了嘛。我没违反宪法,我遇到问题时都会据理力争,比如我写《业主奏鸣曲》的时候,《物权法》还没出来,拍完以后才出来,但是也通过了。我花了物业费,你就是我请来的,你得听我吆喝,是吧?这是一个根本道理,这个没法反对。这是现代社会,这是我自己的财产,我当然有权利去过问。”
但是谢晓东在送审《无形杀》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麻烦,当时的说法是,关于人肉搜索没有立法,中国电影审查里有一个规定,没有立法的领域不能成为电影题材。《无形杀》涉及了公民隐私权问题,正式颁布的法律里从来没有隐私权这三个字,所以电影不能通过。后来谢晓东开始翻找有没有类似的法律规定,终于,他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里面找到了,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谢晓东找到了“隐私权”,自然电影也通过了。
“我的片子几乎都没有被剪过,也不能说幸运,用幸运这个词就可悲了,没有被剪是因为我行事正确。后来有些领导说:谢晓东,其实你拍这些片子都特主旋律,只不过你讲故事的方式很另类。我说您错了,我这不是主旋律。他说怎么不对啊,你这不是弘扬善良正义么。我说主旋律是国家意志,是政权意志,它是一种强加式的,我说我关注的叫做普世价值观,比如说人不能偷别人的东西,是人类社会为了生存下去在族群之间和个体之间共识的,共同遵守的一种原则和价值观,这个普世价值观和主旋律有相重叠的地方,但是不一样,有大部分是完全不重叠的,所以我不是主旋律。”
《我是植物人》在审查时也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最初他们不同意把郑筱萸放进去,谢晓东坚持,如果不把他放进去,这个电影分量就轻了,在他坚持下,这部电影一刀没砍。
谢晓东说:“在英文里有个词叫Intellectual,中文给翻译成‘知识分子’,所有上过大学的都叫知识分子。我觉得中西方对这个词的理解差异非常大。在英文里,艺术家也叫Intellectual,是有思想有创新的。在这个大前提下,好莱坞的从业人员如果不关注社会,只关注从哪里挣钱,就根本混不下去。我们看到很多好莱坞的演员、导演,用各种方式表达对社会的关注。而我们中国,这种传统丧失了,我们把自己变成梨园戏子了,供有钱人玩耍。如果说中国还有知识分子,娱乐圈电影界里还有知识分子的话,应该把事业放得更宽一点,不要太拘泥于你情我爱的那点破事。”■
(实习生霍晓对本文亦有贡献) 一个谢晓东无形杀看不到中国电影一年到头我是植物人电影剧情片喜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