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T恤变形记
作者:何潇(文 / 何潇)
 ( 图2:从设计和形态上做了改变 ,把 T恤改成了一件长袍 )
( 图2:从设计和形态上做了改变 ,把 T恤改成了一件长袍 )
若不仔细看,“Project White T- Shirt”(白T恤变形展)的介绍图册一定会被人当成一本洗衣机指导手册。手册封面是一台洗衣机,其上白纸黑字地写着“Instruction Manual”。在封二的位置上,参展设计师的名字像技术参数一样排列着,页眉上,正儿八经地印着“washing machine”的字样。翻回来,定睛看了看,才发现封面洗衣机下印着一行小字:“curated by triple-major to support designers against aids”(由triple-major策划,以支持设计师抗艾滋行动)。
“洗衣机是来当伪装的,因为白T恤需要经常清洗。我用了很多洗衣的概念:洗衣手册、水洗标等等。‘伪装’的这个概念可以让日常的东西变得艺术起来。”“Project White T-Shirt”的发起人陈宇祈告诉我。来北京前,“Project White T-Shirt”在洛杉矶和东京做过展览。在洛杉矶,他将展厅伪装成洗衣房的模样,把一干展品挂在洗衣机上。“伪装”是另一种“变形”,陈宇祈最新的“伪装作品”,是开在北京一条幽僻胡同里的“药店”。门面布置成中药店的模样,名片上一本正经地写着:陈宇祈大夫。进店一看,大夫的药柜里却装满了世界各地前卫设计师设计的衣服。
与在洛杉矶举办的那次“白T恤变形记”相比,在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这次展览显得正常,最起码,它不会让人产生误入洗衣房的错觉。可展厅里布满的衣物依然是奇形怪状、难以辨认的,若不是工作人员事先介绍,说展品是出自不同国家设计师之手的T恤,参观者要猜到正确答案着实困难。
一件由比利时设计师卡罗琳·勒奇(Carolin Lerch)设计的作品,乍看是一幅白色窗帘,实际却由多件T恤交叉重叠而成的。这件“窗帘衫”甚至依然是“可穿”的:T恤袖子和领子保留着,人“穿上”它后,就像一排晾在晴空下的布偶。设计师称,“此作品对T恤与功能性物品的结合做出了提问与思考”。另一边,有一件被镶在画框里的作品,出自美国设计师布雷特·韦斯特福尔(Brett Westfall)之手,远看像手工印染,近看原是一件“T恤残骸”。布雷特在洛杉矶拥有Unholy Matrimony的品牌,手工印染做得出色,曾被川久保玲相中,出现在2008年Comme Des Garcons春夏男装系列的巴黎T台上。她的这件“T恤遗骸”确实是“入土后重生”的东西,曾经在地下埋了185天之久,设计师希望它能传达“地球有生命和作用”的信息。“从中可以看到地球的力量。作品出土后,会发现T恤被根和土完全地侵蚀了,就像是地球把T恤吃下去了一样。”陈宇祈向我解释说。
陈宇祈是中国香港人,在美国求学,毕业后在洛杉矶创立了创意机构Triple-Major。展览中也有他的作品,叫“Confu-Shirt”。衫如其名,这是一件“孔子T恤”:袖子宽且长,袖口的口袋里,放着随T恤附送的《论语》。令这件“夫子衫”发生时空穿越的是袖口的一条拉链,解开袖口拉链后,T恤便发生变形:钉到背后可变成翅膀,也可以完全拉下,将其变为斗篷或披肩。“我想的是,T恤这个东西如果在孔子的时代已经发明了,会是怎么样?一定是宽袍大袖,袖子里放一本论语。这是一个历史人物的扮演,同时也能回到一件T恤。”陈宇祈说。
 ( 图4:挪威设计师Siv Stoldal的作品“帐篷T恤” )
( 图4:挪威设计师Siv Stoldal的作品“帐篷T恤” )
“T-Shirt”第一次作为正式词汇出现在韦氏字典里,是1920年。这并不意味着被称作“T恤”的东西必须是T字形的棉质上衣。实际上,在获得这个字母形状的“标准照”之前,T恤经历了许多变种:无袖T恤、A字T恤、V领T恤……而此后,标准款T字形T恤却乏善可陈。“‘白T恤变形’这个想法我很早就有了,因为它是时装里最基本的东西。时装在生活中的意义一直在变,以前是身份的象征,现在更多的是自我表达的方法。时装的材料也在变。但有些时装的根本元素却一直没有改变,比如基本款的白T恤。从发明以来,一直以覆盖上半身的棉质布料的形态存在。”陈宇祈说。
为了看到“最基本物质形态改变的可能性”,陈宇祈给来自13个国家的31个设计师寄去了一件基本款白T恤,得到的结果出乎意料。有人制造了比基本款白T恤更基本的“变形物”。挪威设计师哈拉尔德·伦德·赫尔格森(Harald Lunde Helgesen)带来的是一件“最基本的服装”,他的做法是“消灭缝纫”。尽管白T恤被公认为最基础的时装元素之一,仍然由至少两块布组成,而哈拉尔德的T恤上却只有一块布。设计师没用一针一线,仅凭借剪裁,将其变成一件可实穿的“条纹镂空装”。“做过灯笼的人或许能明白这其中的原理,通过拉扯营造出空间,因而将一块平面的布变为立体的衣服。除了服装,这种概念也可以运用到很多其他领域。”陈宇祈说。另有一个德国设计师寄来的作品,用几条毛巾做成,“比作为平民代表服饰的T恤还要平民”。
 ( 图3:陈宇祈的作品“孔子T恤” )
( 图3:陈宇祈的作品“孔子T恤” )
“这个东西说是时装,但表达的东西不只是时装,更多是大众文化。T恤是流行文化的一个标志,因为被马龙·白兰度和詹姆斯·迪恩穿过,所以成为流行文化的偶像。”陈宇祈说。上世纪30年代,作为T恤前身的坦克背心一度成为流行内衣,但风光有限,很快在公众那里失却欢心。50年代,T恤杀回大众流行领域,表现得有型有款——这应归功于《欲望号街车》里的马龙·白兰度与《养子不教谁之过》中的詹姆斯·迪恩。尽管两人的拥趸有时会因“谁的功劳大”意见不合,但外观索然无味的白T恤自此与“性感、反叛”攀上了关系。如果说“性感”是个因人而异的说法,“反叛”的门槛则更低,只需在T恤上写写画画,就是一幅“流动的革命宣言”。
展厅里,有一件挂在墙上的T恤,来自一个名为“宣言”(Manifeste)的法国品牌。
 ( 图1:葡萄牙设计组合 White Tent 设计的作品,由两件T 恤组成,领子部分是另外一件
)
( 图1:葡萄牙设计组合 White Tent 设计的作品,由两件T 恤组成,领子部分是另外一件
)
这块T恤形状的画板是Manifeste的创办人亚历山大·达瓦(Alexandre Daval)和艺术家西里尔·塔隆(Cyril Talon)共同创作的作品,其出发点是“用绘画的基本物来表达时装的基本物”。“白T恤是最舒适便宜,又各文化共享的衣服。它不是任何设计师设计的,却拥有特定的形状和规范,这就像绘画里的白画板一样。Manifeste希望把白T恤在时装中的定义作用延伸到艺术上。”陈宇祈解释说。
有人相信宣言作为言语的力量,也有人偏好实际行动,希望T恤能“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展览中,有几件可以变成“住所”的T恤,或许是“变形”维度最大的设计,打破了“身体”与“空间”的界限。其值得赞许之处却是“实用”,与艺术家经常玩弄的纯粹概念作品不同,这是真正能穿上身的衣服。展品里有一件为“流浪者T恤”,出自中国设计师上官喆之手,功能多样,且变形后样式时髦,因而实用价值很高:使用者可以将它变成遮风挡雨的斗篷大衣、约会用的白色连衣裙、甚至无家可归时的临时帐篷。机关在一条拉链上。白天,解开衣服上的拉链,它是一件用以蔽体的外衣;夜晚,合上拉链,把衣服顶端钩在树上,衣服旋即变成一间房子,流浪者可以在里面安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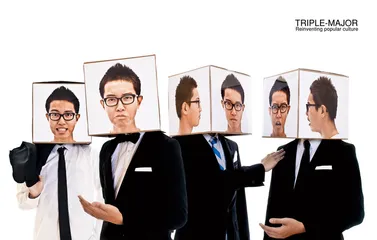 ( “Project White T-Shirt”的发起人陈宇祈 )
( “Project White T-Shirt”的发起人陈宇祈 )
无独有偶,挪威设计师斯托尔达(Siv St?ldal)的作品也是一个由T恤改造而成的帐篷。与前者相比,它更具“社群”概念,空间可以容纳三个人居住。斯托尔达的帐篷由三件T恤拼合而成。每件衣服侧面均有纽扣,三件同时扣起,就可搭建成帐篷。解开纽扣后,帐篷变成一件白T恤、一件米白T恤和一件蓝色开领衬衫——帐篷顶端的三角形转为衣服下摆,搭配两侧的纽扣,很具设计感。斯托尔达从英国圣马丁艺术学院毕业后创立了自己的品牌,最近将工作室从伦敦搬到了挪威的一个小岛上。他非常偏好用服装建构空间,曾做过一件可以将山包裹起来的巨大外衣,拆卸后,是许多件走得上T台的风衣。这件“山之风衣”出现在斯托尔达为“Project White T-Shirt”项目拍摄的作品短片里。设计师穿着“帐篷T恤”与“山之风衣”,披了清晨的阳光在宁静的岛上行走。片子采用童话剧的配音方式,他的角色是一只绵羊。■
 ( “Communi-tee”
将几张“白纸”联系在一起,“白纸”就变成了记事簿——这是来自英国伦敦的设计组合A'N'D的创意。2000年,两人结为夫妇,因为买不起婚纱,便制作了一件双人T恤“Grafit-tee”。在项目中,他们将两人世界转化成六人社区“Communi-tee”(社群),T恤用红线相连,号码从XS到XXL一应俱全。穿着者有一支共用的笔,可以在各自身上写东西。即使将来剪断连接衣服的红线,各人脱离Communi-tee生活,回忆依旧会保留下来。 )
( “Communi-tee”
将几张“白纸”联系在一起,“白纸”就变成了记事簿——这是来自英国伦敦的设计组合A'N'D的创意。2000年,两人结为夫妇,因为买不起婚纱,便制作了一件双人T恤“Grafit-tee”。在项目中,他们将两人世界转化成六人社区“Communi-tee”(社群),T恤用红线相连,号码从XS到XXL一应俱全。穿着者有一支共用的笔,可以在各自身上写东西。即使将来剪断连接衣服的红线,各人脱离Communi-tee生活,回忆依旧会保留下来。 )
 ( “捕梦网”
英国设计师卡罗莱娜(Karolina)将衣服当做讲故事的平台,她偏爱自创角色,并将其一一放进衣服里。在此项目中,她把白T恤改造成一个捕梦网,把自己做过的噩梦改造成许多小角色,装进这个网中。她的梦网里有“Say What”小鬼和坏天气“Rainly”,模样可爱,全然不似一个噩梦。 )
( “捕梦网”
英国设计师卡罗莱娜(Karolina)将衣服当做讲故事的平台,她偏爱自创角色,并将其一一放进衣服里。在此项目中,她把白T恤改造成一个捕梦网,把自己做过的噩梦改造成许多小角色,装进这个网中。她的梦网里有“Say What”小鬼和坏天气“Rainly”,模样可爱,全然不似一个噩梦。 )
 ( “人马衫”
这是一件人与马都能穿的T恤,出自德国设计组合Anntian之手,灵感来自古希腊神话里的人马兽。白T恤一直被认定为上半身的衣服,Anntian希望改变这个基本概念,与是萌生了将T恤套在马身上的想法。他们先设计了一件给马穿的T恤,后加以改造,令它可以套在人身上。条纹是他们的标志元素,悉数采用手工印刷,每件衣服都不相同。 ) t恤T恤变形记
( “人马衫”
这是一件人与马都能穿的T恤,出自德国设计组合Anntian之手,灵感来自古希腊神话里的人马兽。白T恤一直被认定为上半身的衣服,Anntian希望改变这个基本概念,与是萌生了将T恤套在马身上的想法。他们先设计了一件给马穿的T恤,后加以改造,令它可以套在人身上。条纹是他们的标志元素,悉数采用手工印刷,每件衣服都不相同。 ) t恤T恤变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