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准则与道德革命
作者:薛巍(文 / 薛巍)
 ( 安东尼·阿皮亚和他的《荣誉准则:道德革命是怎样发生的》 )
( 安东尼·阿皮亚和他的《荣誉准则:道德革命是怎样发生的》 )
荣誉分配的改变
亚里士多德推崇中庸之道,也推崇荣誉。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荣誉是那些外在的善中最大的,大度的人对荣誉和耻辱抱应有的态度,他们重视荣誉超过一切。荣誉是奉献给善良人们的德性的奖品。”但是在道德哲学家中,如今荣誉这一概念不受推崇。阿皮亚说,这是因为“它令人不安地与旧的等级制有关联,这有违我们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它诉诸的是原始的、非理性的情感因素”。但他认为,尊敬或对我们的同侪的不敬是一种特别有力的机制。所以荣誉及与它对应的羞耻尤其适合把私人的良心转化成公共道德规范。
阿皮亚在《序言》中说:“荣誉是一个当代道德哲学忽略的重要主题。荣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跟我们的社会认同一样,它把我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关注荣誉,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对待他人,让我们自己过得更幸福。以前哲学家们知道这一点,读一下蒙田、亚当·斯密或亚里士多德便知。但是,虽然尊严和自尊在当代哲学中的名声很好,与之相关的荣誉却几乎被遗忘了。现在是恢复荣誉在哲学中的地位的时候了。”他是通过对道德革命的研究发现了荣誉的价值:“作为道德激励因素,荣誉比钱更重要。我们向英勇的士兵发的不是钱,而是勋章。”阿皮亚详细考察了决斗、缠足和奴隶贸易这三种习俗,以及它们分别是如何终结的。这三种习俗的终结的相似之处组成了驯服荣誉的指导原则。
首先,这三种习俗都部分源自荣誉准则:决斗是为了保护荣誉;缠足是地位和荣誉的反映;对很多不拥有奴隶的白人来说,奴隶的存在使他们表现为不受奴役的人。决斗涉及个人的荣誉,反对缠足关涉国家荣誉,反对蓄奴则涉及阶级荣誉。其次,杰出的论证不足以阻止某种可怕的文化习俗。“不管这些不道德的习俗是如何终结的,在我看来,它都不是由于人们被新的道德论证击倒。决斗一直是蓄意谋杀的、非理性的;缠足一直是痛苦的、伤害身体的;奴隶贸易一直是对奴隶的人性尊严的侵犯。”在这些情形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国家的荣誉感的觉醒,这种觉醒会促使人们行动起来。最后,当道德论证得到荣誉分配的变化的支持时,才会发生道德革命。禁止蓄奴和奴隶贸易得益于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希望把劳动看做是光荣的,再者,它能使英国人相对于拥有奴隶的美国人来说更加光荣。
荣誉有多种复杂的形式,阿皮亚将它们分为两种。网球运动员纳达尔被人敬重,敬重是一种根据某种标准或与他人比赛的成绩来分配的一种荣誉。这种荣誉通常依赖于竞争,有高下之分。第二种荣誉依赖的是把别人认做跟自己是平等的。一个人只要被认为是属于某个群体,如警察或绅士,或人类,就能获得这种荣誉。一个人的人性就能使他享有尊敬。简单地说,敬重是你通过取得成功来获得的,尊严是你作为一个人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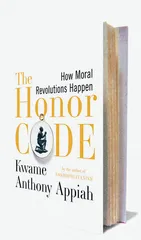
荣誉跟诚恳或信任一样,是一种中立的力量。它可以被加以引导,去鼓励平等和尊严,也可以导致不平等和暴力,如在古希腊的英雄时代,当他人的利益与英雄的荣誉要求相冲突时,英雄没有理由去照顾他人的利益——海克托尔两次选择了避免使自己感到耻辱与不光彩的行动,即使他的行动会危害他的家庭与城市也在所不惜。英雄甚至必须为了对荣誉的冒险追逐而牺牲自己的安全。
荣誉是一种重要的道德情感,因为它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我们人类需要黑格尔所说的承认,深切、持久地关心自己的地位和尊严,需要他人对我们是谁、我们的行动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需要他人承认我们是有意识的存在,并承认我们承认了他。“当你在大街上瞥一眼另一个人,你们的眼睛以相互承认对视,你们俩都表达了一种基本的人类需求,你们俩都对这一需求在一瞬间毫不费力地做出了反应。黑格尔对获得承认最著名的讨论是他在《精神现象学》中对主奴关系的考察。应该不会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废奴运动的动力源自对承认的追求。”
阿皮亚以两个生动的例子分别说明,荣誉和耻辱会给我们造成生理上的反应,所以它们能成为强大的力量。他小时候听过爱尔兰歌手杜尼坎唱的一首歌叫《昂首阔步》,歌曲中母亲对幼时的他说,走路时要昂首阔步,“荣誉心理学跟昂首阔步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笛卡儿说过:“想到过去我曾经表扬过这位作者,我就因为感到耻辱而脸红起来。”
荣誉是道德革命的核心?
在《认同伦理学》中,阿皮亚考察了对家人、种族、宗教和国家的认同会使我们感到光荣或耻辱。他进而认为,荣誉与认同也是道德革命的核心。明辨是非并不足以使我们行动起来,我们还需要荣誉感等道德情感提供行动的动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在仔细研究科学革命后对科学有了很多发现。例如,托马斯·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在研究了17世纪伽利略、哥白尼和牛顿的科学革命与晚近的量子物理之后得出了精彩的结论。科学知识的增长明显促进了技术爆炸。但推动科学的精神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理解世界。而道德最终是实践性的,道德本质上跟我们的行为有关。因此,既然革命是短时间内的巨大变化,道德革命就得涉及道德行为的迅速改变,而不只是道德情感的改变。”
1829年,英国首相威灵顿公爵与出言不逊的托利党极端分子温奇尔西伯爵进行决斗。威灵顿的子弹射偏了,温奇尔西朝天上开了一枪。如果首相在决斗中被打死将对英国的政治稳定性产生怎样的影响?但是在威灵顿所处的贵族圈子里,绅士们不担心这种小问题。但决斗还是受到批评,不到1/4世纪后,它就完全消失了。阿皮亚认为,这仅仅是由于一个简单的理由,不是诉诸理性、道德、法律或宗教,而是修正和改进了对贵族荣誉的诠释。绅士的定义变成了“一个从不施加痛苦的人”,这就意味着把决斗视为不够绅士甚至耻辱的做法。
阿皮亚还指出,决斗和缠足是精英阶层的习俗。当它们扩展到下层阶级时,就会迅速失去其身份标志的意义。到19世纪初,决斗越来越多地发生于非贵族之间,由此决斗显示不同身份的作用消失了。19世纪50年代,自由派议员理查德·科布登说:“一旦布贩子的助手也开始决斗,它在上层阶级眼中就变得声名狼藉了。现在最可笑的莫过于一个贵族或绅士在受辱时要出去跟人决斗。”
在反奴隶运动中也可以看到荣誉的作用,英格兰的商人和工人开始援引“工人的荣誉”来反对容忍奴隶的劳动。
阿皮亚提出,从历史中总结的教训可以用于解决荣誉在当代世界提出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有些国家同性恋会被终身监禁甚至处死,还有对发达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极端贫困的容忍。有一天,人们将发现,他们不仅认为旧的习俗是错的,而且旧的方式令人蒙羞。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很多人将改变他们的行为,因为旧的方式令他们感到羞耻。因此可以期望,如果我们现在能为荣誉找到恰当的位置,我们就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阿皮亚最早是于2008年初在剑桥大学的西利讲座上提出这些论点的。历史学家们对于从历史中总结出简洁的、可以应用的教训这种做法是很谨慎的,剑桥大学历史系的一些人就对阿皮亚的观点皱起眉头。
美国学者保罗·伯曼说:“我不相信他的主要论点——革新了的荣誉概念在道德革命的历史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决斗消失的原因比较容易确认。在封建时代,决斗有很符合逻辑的意义。贵族们主要是通过恐怖和威胁来统治其他所有人。贵族们通过不时地射杀或刺死一个人,来提醒自己和其他人。贵族们很可怕、很专横,会不管法律、征服、教会或道德规范的反对,待裁判摔下帽子后,凶残地为所欲为。到1830年,在英国中产阶级开始享有一些政治权力,甚至无产阶级也开始动员起来。国家更强势了。再假装个人暴怒之下的暴力行为能阻止其他人享有发言权已经没有意义了。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决斗的人发现,贵族乐于停止用枪相互威胁。反对奴隶制和缠足的运动则是更加重大的事情。这一发展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人类普遍平等的原则,其后或许还有更加深层、广大的推动因素。传教士便在中国的反缠足运动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道德革命准则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