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最佳思想
作者:薛巍(文 / 薛巍)
 ( 安东尼·格雷林 )
( 安东尼·格雷林 )
对主观性的客观研究
美国哲学家苏珊·哈克说:“过去10年真的出现了50种有趣的新哲学思想吗?我很怀疑。我猜测,一些目前很时髦的思想将会被证明不像它们看上去那么有趣、那么新。过于强调人为的创新,除了混淆没有千篇一律的思想创新方式这一事实之外,还诱使我们忘记,重大的哲学进步通常需要综合一大堆或新或旧的思想。”
哈克说,她10多年的著作中已经说明了哲学进步综合化的特点。思想的创新、意义的增长是她2003年出版的《捍卫科学:在理性的范围内》一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随着科学的进步,科学术语的意义会发生演变,这并不一定就是坏事,还能对科学的理性化做出贡献。科学的词汇需要跟现实结合起来。
苏珊本人便乐于提出新概念,如她把“基础主义”和“融贯论”拼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新词“基础融贯论”。到2007年出版《形而上学的合法性》时,她提出哲学研究是科学研究的延续,哲学研究依赖经验,虽然跟科学研究不同,哲学依赖的是通过想象得到的经验。
意义的增长能够推进哲学研究,并不是说所有的变化都是好的。有些意义的变化能推进研究,有些则会阻碍研究。好的、建设性的意义变化是旧词获得新的信息,或新词能使我们摆脱虚假的二分法;糟糕的、破坏性的意义变化是旧词获得错误的信息,或被过度延展、打碎以致失去了意义,或新的术语包含混淆,或只是为了公关。
 ( 布赖恩·科诺森 )
( 布赖恩·科诺森 )
“意义的增长”这个概念并不新。一个多世纪以前,皮尔士就写道:“在使用中和经验中,意义都在增长。像力量、法律、财富、婚姻这些词,对我们的意义跟它们对我们未开化的祖先的意义是不同的。”哈克指出,今天非历史的、后弗雷格时代的新分析哲学对意义的增长却很陌生,它解决我们熟知的问题和培育其他思想的潜力被忽略了。
哈克认为,“主观”和“客观”这两个词在现代哲学中的使用十分混乱。卡尔·波普尔一本著作的书名十分吸引人,但也误导人——《客观知识》好像成功地让很多读者以为他有一套关于客观知识的理论,而实际上他的知识论暗地里是怀疑主义的。在他看来,客观知识得不到证明,不是真的,也无需相信它。他另一个书名《科学发现的逻辑》一样误导人,因为该书的主题是不存在科学发现的逻辑。
 ( 史蒂夫·富勒 )
( 史蒂夫·富勒 )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副教授布赖恩·科诺森认为,接下来的10年中,对主观性的客观研究将改变学术领域和其他领域。西方人一直假定,客观性和主观性在不同的领域起作用。柏拉图在《菲德罗篇》中说,灵魂就像一架马车,理性是驾驭马者,激情是不听话的黑马。笛卡儿分开了灵魂和肉体。英国科学家C.P.斯诺以类似的区分分别了两种学术文化:科学崇敬客观性,人文崇敬主观性。但由于技术进步,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的鸿沟在迅速缩小。科学家开始客观地研究主观性。这里的主观性不只是指跟输入(感知)和输出(行动)有关的论题,还有跟情感和思想有关的中间过程。这些灵活、活跃的力量做诠释和驱动,把感知转化为行动。
对主观性的客观研究依赖的是数据。新技术可以把大脑的活动确定至毫米和亚秒单位。神经成像不仅可以推断人在看或者听什么东西、准备做什么,而且可以推断人要记忆什么,他们对他们想要的东西感到兴奋、内心在经历冲突,甚至在思考他们自己。目前,这些推断还很粗糙,但它们的精致程度将会提高。最终将绘制出主观体验的地图,由此确定如何改变人的行为。科学家们将破解主观活动的神经密码。“神经经济学”和“社会神经科学”都跟大脑研究有关。人们对这些研究的实际用途很感兴趣,如预测消费者的选择和改善心理疾病的诊断。这些实际应用会提出一些伦理问题及存在论问题。主观地图对我们的认识会不会多过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们对自己想认识到什么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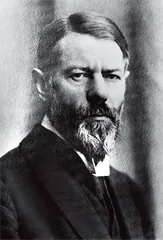 ( 马克斯·韦伯 )
( 马克斯·韦伯 )
英国伦敦大学哲学教授安东尼·格雷林指出,神经学哲学研究原则上只能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必须在更广泛的背景下理解心灵。人的性格和心灵的内容是与社会和自然背景互动的结果。个人的心灵是群体心灵和外界的输入造成的,它通过与父母、老师、社会和自然界的互动而生长。确认一个人知道什么和相信什么,描述他如何思考,就是把他看做与其他心灵的复杂关系和外界刺激的一个节点。一个心灵是多个大脑互动的结果,心灵是插入社会和自然两种环境中的大脑。在确定磁共振成像对意志、决定、情感在推理中的作用等方面的哲学含义时,要充分考虑心灵的社会性。比如,有实验表明在人还没意识到他做了一个决定之前,科学家从成像上就看出他做了什么决定。这里的决定远不是决定把自己的储蓄投资到哪里或是否接受某份工作。同样,认为道德责任是先天的,也没有考虑到道德态度在个人和社会中的变化以及它们是讨论的结果。心灵问题不会被大脑研究穷尽,不带“神经”前缀的哲学仍有工作可做。
抗议科学的兴起
英国科学史专家史蒂夫·富勒认为,过去10年间最重要的知识进步是他提出的“抗议科学”的兴起。新教改革标志着西方第一个知识民主化的努力,把宗教权威从罗马教会手中夺过来。我们现在进入了知识民主化的第二个阶段,涉及科学权威的移交,因此是抗议科学运动。
在新教的兴起过程中,印刷成了一个方便的媒介,使人们能够获取自己决定信仰什么所需的认知资源,不再需要服从地方教士的权威。《圣经》有了各国文字的方便携带的版本之后,印刷就成了大买卖。这一趋势在启蒙运动期间变得更快,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一次彻底的解放。
过去20多年间,以电脑为基础的信息技术造就了一场新的出版浪潮。这对认识权威的分配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新教兴起时出现的旧的管理各种意见和合法性主张的体制化方式——世俗国家和科学方法——正在经历合法化危机。
这些旧的解决办法本来是为了解决对《圣经》不同的诠释之间可能的暴力争执。从这方面来看,定期选举和有控制地实验有类似的功能。随着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保护和促进公民的福利,科学越来越被卷入政府的运作。因此,科学精英就是现在世俗政府的高级教士,是跟健康和环境有关的建议和公共政策的源头。
新教科学对国家和科学之间的密切关联提出挑战,主要是因为科学的权威往往会受到不负责任的机构的操控。这次相关的机构是国家新的科学院和学术杂志,它们忽略被它管制的人民的意见,希望他们自动地服从它们的权威。抗议科学的目标是恢复认知力的平衡,让接受治疗的病人更像是一位病人,而不是一台需要修理的机器。
抗议科学派知道科学在他们的生活中不可或缺。正因为如此,他们坚持要积极地关注它如何发挥作用。他们从其他地方,通常是网络获取消息,以他们自己的体验和信念背景来弥补所有的科学研究方法上的不确定性。抗议科学派坚持认为,他们有权自己决定科学问题,因为是他们要承担这些决定的结果。结果就是一种综合地对待科学的方式:接纳大部分已被接受的科学事实和理论,同时带着解释性原则和生活实践,对它们做带倾向性的阐述。
当年新教徒因为拒绝教会的权威而被天主教妖魔化为无神论者,今天的“抗议科学”也被谴责为反科学。但是,无论是新教徒还是抗议科学派,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尊重为他们的信念提供理由和证据这一要求。所以,抗议科学能够暴露现有权威的伪善——他们没有达到他们自己许诺的认知水平。所有被报道的科学欺诈都会受到抗议科学的拷问,都说明,在整个研究体系变得腐化之前,要把知识问题掌握在自己手中。
新教改革是欧洲世俗化过程的第一步,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西方精神的除魅。新教科学与这一过程的关系尚不明朗,它既对科学权威加以除魅,又给改变人们生活的科学添加了魅力。至少抗议科学认真对待这样一种观念:任何声称它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的知识都要对它的信众拥有广泛的吸引力。■ 21思想最佳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