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逝世150周年
作者:薛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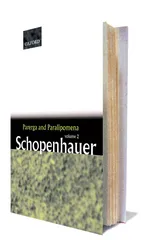
( 叔本华作品《附录和补遗》 )
世界的本质是意志
叔本华1860年9月21日在法兰克福死于肺炎。他的哲学影响了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等很多伟大的思想家,至今学者和哲学爱好者仍对他的著作很感兴趣。2007年7月,《哈泼斯》杂志虚构了一篇对叔本华的访谈,要求他向美国读者推荐暑假读物。“叔本华”说:“为了对付这个未经深思熟虑就开始耍笔杆子的时代,我们要竖起一座防波堤。一个审慎的读者应该不受无知的商业利益的瞎扯所叫卖的新书的引导。读者应该意识到,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出现了很多伟大、杰出的著作,这些著作很少会出现在畅销书榜上。现代阅读的公众蠢就蠢在,不是去寻找公认的、真实的、伟大的作品,而是本能地去找精心装扮、枯燥无味的新书。我给读者的建议是:可以去买卡尔·希尔森的新书,但也要花时间去读你出生之前出版的书,它能帮助你用不同的术语去理解世界。《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英国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说:“作为最伟大的德语散文家,叔本华的确值得一读。”但美国哲学家威尔·杜兰特说,《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的开头不是很好的起点。他在《哲学的故事》中说:“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没有扑朔迷离的康德术语,没有黑格尔的晦涩,没有斯宾诺莎的几何学方法,一切都清晰而又有条理。该书的第一句就毫不谦卑。它以世界是我的表象开头。他从康德出发,承认外部世界仅仅通过我们的感觉和表象而为我们所认识。接着是一番颇为清晰有力的唯心论的说明。但是这番说明是全书中最没有独创性的部分,最好放在末尾而不是放在开头。世界蹉跎了一代人才发现了叔本华,因为他把最差的部分放在开头,把他自己的思想藏在200页陈旧唯心论的屏障之后。”
《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刚出版时就无人问津,叔本华直到临死前两年因为出版了论说文集《附录和补遗》才成为名人。他在书中纵论女人、噪音、自杀、书籍与阅读、观相术、天才和文学形式等论题。他说:“我长期有这种看法,一个人能安静地忍受噪音的程度同他的智力成反比。”
2005年,有英国出版社把叔本华论说集《附录和补遗》中的《争论的技艺》一文单独出了一本书,题为《立于不败之地的艺术:38种赢得辩论的方法》。很多辩论和逻辑学方面的书籍都说,我们应该尽量消除逻辑错误,叔本华却要教人无论有没有理都让自己看上去是正确的,这肯定要用到诡辩。他的意志主义本体论就缺乏严格的论证,说动植物有求生意志,是“一种文学般的世界观,不是严格的本体论,与真理性认识相去甚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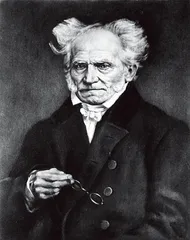 ( 哲学家叔本华 )
( 哲学家叔本华 )
叔本华这篇《争论的技艺》究竟是反讽,还是很严肃的呢?辩论的目的到底是获胜、让对方承认他们错了我们是对的,还是发现真理?叔本华是很严肃地教人诡辩术,因为他认为,希望用正确的逻辑论证说服所有的人将是徒劳的,这是人性和世界的本性使然:统治世界的不是理性和思想,而是盲目的意志。你不能期望人们是理智的,所以要想赢得辩论,就不要努力用正确的论证去说服人,而要使用以人性为立足点的心理学方面的诡计,如反诘或转守为攻。“这是高明的一着,遭到反诘,对方的论证就转而反对他自己了。例如,他宣称某某是个小孩子,你应该原谅他。你反驳道,正因为他是个小孩子,我才应该纠正他,否则他将坚持不改他的坏习惯。”
叔本华是生命哲学、直觉主义的先驱,他率先打破西方哲学的认识论优先和理性主义传统,提出世界的本质是意志而非理性。看上去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有序的世界,受物理定律和道德法则的约束,但这只是宇宙意志驱使我们这样认为。理性化的有序世界背后是纯粹的求生意志。我们陷于这种无意义的奋斗之中,徒劳地试图去满足我们的欲望。当目标实现后,我们会感到无聊,目标没有实现时我们又从头开始。因此不管欲望有没有实现,我们都会痛苦。人生就是奋斗、无聊、奋斗、无聊,一直到死亡。
 ( 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 )
( 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 )
消极虚无主义
据说叔本华从童年起就有悲观主义倾向。他回忆说:“17岁那年,我被生命的痛苦所侵袭,就像佛祖年轻时看到疾病、衰老、痛苦和死亡时的感受一样。”19岁时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天上的种子是怎样在我们这贫瘠坚硬的土地上去寻找它们的空间的?在这里必须为任何一块小地方的缺乏而争斗。通过贫困人种向人宣布出来的是需求的冷酷的审判。这一判决使这个人种为了匮乏和生命急需的东西耗尽了他的最后一点精力,阻止了他的任何更高的追求。”
每当我们听到叔本华的名字,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个阴郁、愤愤不平的悲观主义者形象。跟其他哲学家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不同的是,叔本华的这一形象非常准确,他就是一个阴郁、愤愤不平的人。但这只是对他的性格的判定,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远不只是性格问题,他还是一个悲观主义的思想家。如同自己所说,他的悲观主义不仅仅是针对特殊的个体,而且是针对所有人的,每个人都只是一个例子,他建立了整个形而上学体系为他的悲观主义做了精致的辩护。
但同为意志论者,尼采就成了乐观主义者。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每部真正的悲剧总留给我们一种超脱的慰藉,使我们感到,尽管万象流动不居,生活本身到底是牢不可破,而且可喜可爱。这点慰藉明明白白地体现为萨提儿歌队。深思熟虑的希腊人就以这种歌队来安慰自己。这种人的特性是多愁善感,悲天悯人,独能以慧眼洞观所谓世界历史的可怕的酷劫,默察大自然的残酷的暴力,而动不动渴望效法佛陀之绝欲弃志。艺术救济他们,生活也通过艺术救济他们而获得自救。”
叔本华说意志是求生存的意志,尼采则认为意志求的是强力。《哈泼斯》虚构的采访中的第二个问题是:“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称赞了你,说你是他的导师,但后来他又说你和基督教是他终生的敌人。是什么造成了你和尼采之间的争论?”叔本华回答说:“对此有两种解释。简单的解释是,满怀赞扬和敬佩之情的尼采是心智健康的尼采,后期的尼采处于梅毒造成的幻觉之中。头脑正常的人怎么会把我跟基督教相提并论呢?当然,我有时也无法避免自相矛盾。尼采认为我是一个绝望的一成不变的悲观主义者,但对我来说认识到人生的无聊只是寻求与意志的力量达成妥协的开始。尼采拒斥基督教,但他寻求一个比我的更强的肯定生命的视角。这导致他提出永恒轮回理论,他在论救赎中说,由于时间的限制,意志无法向后意欲,轮回就成了走出这一境地的方式。这个理论有其杰出之处,但也是很多可怕的漂浮在他大脑中的梅毒。他最终成了一位科幻作家。”
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2002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刍狗:关于人和其他动物的思考》,扉页上引用了老子的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英国哲学家西蒙·克里奇利说,格雷这本书把以悲观的人性论为基础的伯克式的保守主义和道家哲学结合在了一起。“伟大的道家哲学家庄子提出的悖论中,让格雷感兴趣的是,要接受这样一种事实:生命是一场梦,没有从中醒来的可能性和欲望。道家教导我们,自由系于把我们从个人叙事中解脱出来,认同于宇宙的生灭过程。因此,不要去寻求乌托邦思想家的陪伴,应该从神秘、诗意的词语中寻找慰藉。”格雷跟后期海德格尔一样,认为人类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相信行动能改变世界。行动只能使我们无意义的生活短暂地摆脱无意义的威胁。
叔本华是19世纪最受欢迎的哲学家。警句式的悲观主义最有市场了。它解释了读者遭受的不幸,用语言帮助他们承受绝望和无能为力的感觉。克里奇利把约翰·格雷称作当代的叔本华式的欧洲佛教徒,因为它的理论导致一种消极虚无主义的立场,以一个特别有教养的超脱的眼光看世界,发现它没有意义。“消极的虚无主义者不是努力去行动,因为行动没有意义,而是回撤到一个安全的沉思的距离,培养它的审美感受力,追求诗歌、瑜伽腾空、观鸟、园艺的乐趣,或者像晚年的卢梭一样,他在《漫步遐想录》中说,植物学适合一个无所事事而又疏懒成性的孤独的人去研究。在一个冲向自我毁灭的世界,消极虚无主义者撤退到一个岛屿,在那里神秘的存在如其所是地被看到,未曾被提炼出意义。在一个面临信仰冲突和环境灾难的时代,格雷提供了一个冷酷但安全的临时庇护所。”■ 逝世叔本华15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