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伦与哲学
作者:薛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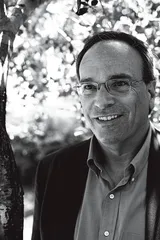
( 汤姆·莫里斯 )
伍迪·艾伦与存在主义和分析哲学
6月底,伍迪·艾伦在接受《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说,在他的46部电影作品中,他最喜欢的6部分别是《开罗紫玫瑰》、《赛末点》、《子弹横飞百老汇》、《变色龙》、《贤伉俪》和《午夜巴塞罗那》。《卫报》记者凯瑟琳怀疑,导演开口评判自己的作品,表明他的创作力在走下坡路。她认为伍迪·艾伦最好的作品是《安妮·霍尔》、《曼哈顿》、《汉娜姐妹》、《爱与罪》、《曼哈顿神秘谋杀》和《解构爱情狂》。
哲学家们最喜欢的应该是伍迪·艾伦那些以哲学家为主角的作品:《仲夏夜绮梦》中的列奥波德是伍迪·艾伦电影中出现的头一个职业哲学家,《爱与罪》中的一个主角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大学教授路易斯·李维,《另一个女人》的主人公玛丽昂·普斯特是一位女哲学教授。
莫里斯人性价值研究学会主席汤姆·莫里斯在《伍迪·艾伦与哲学》一书的前言中说:“伍迪·艾伦的电影里充满了最重要的哲学命题和观念,有的直接通过精彩的对白表达,有的成为电影情节的基础。他提出了很多让人对哲学好奇的问题:道德是什么?对错之间是否有客观区别?人生有什么意义?天地之间可有正义?神存在吗?如何看待死亡?对智力超群而又找不到伴侣的人来说,哲学是否就是性欲的最终升华?”
多数人认为伍迪·艾伦的哲学立场是无神论的存在主义。美国玛丽山曼哈顿学院哲学助理教授马克·科纳尔说,伍迪·艾伦片中反复出现的论调是,人生原本就是彻底无意义的。通过像人际关系、艺术创造之类途径去发现或制造真正的意义、价值,也是没指望的。人生无意义,这是可怕的宇宙本质,每个人最终都逃不过灭亡。在《安妮·霍尔》的开头,童年时代的艾尔维·辛格对医生说,他之所以不再做家庭作业,是因为宇宙在膨胀,要是这么膨胀下去,总有一天四分五裂,一切全都玩儿完,干什么都没用,包括写家庭作业。这里的意思很清楚,既然宇宙是短暂无常的,既然有朝一日一切都将烟消云散,什么都不能永存,那生命就没有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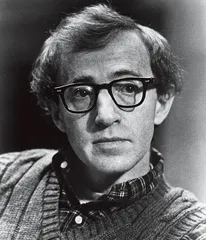 ( 伍迪·艾伦 )
( 伍迪·艾伦 )
苏格拉底在他的申辩的结尾说:“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康德说,能使我们配得上享有幸福的最高的善需要三个预设:人是自由的,神是存在的,灵魂是不朽的。伍迪·艾伦的观点跟存在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存在主义认为,如果神不存在、宇宙最终会消亡,只能说外界不再赋予我们人生的意义,现在人生的意义要通过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来实现。
美国普度大学哲学教授戴维·德特默指出,伍迪·艾伦另一部影片《变色龙》中的主人公泽里格体现了海德格尔所说的非本真存在:他随时都可以变成他身边的各种人,不加判断地采纳他人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不认真开辟自己的事业和立场。
 ( 作品《伍迪·艾伦与哲学》 )
( 作品《伍迪·艾伦与哲学》 )
加拿大约克大学哲学系教授伊恩·贾维认为,伍迪·艾伦是个实用乐观主义者。伍迪·艾伦仍在工作:写作、导演电影,就像他创造的人物,荷莉、哈里、克里夫。在这些影片里,“面对可怕的浮生,令人失望的人际关系,甚至连餐后甜点都没有,创作却是一种断然的积极表态。就算艾伦曾经绝望,他仍在不断拿出新作,这还是肯定了乐观主义”。
伍迪·艾伦的电影中也出现了分析哲学。金恩州立学院哲学教授桑德·李认为,伍迪·艾伦的《仲夏夜绮梦》表现了享乐主义的危险,而这种享乐主义源于分析哲学对经验的态度。在该片的开头,哲学家列奥波德在课堂上说:“除了能够经科学方式证实的经验之外,没有什么是真实的。形而上哲学家不过就是一些过于软弱而不敢承认真实世界的人。他们那些所谓人生神秘性的理论,无非是他们自我内心不安的表现。”
列奥波德的论述属于分析哲学,是极端经验主义的立场,听起来很像罗素,他认为我们对存在的一切了解都只来自感官体验,与形而上学对立的科学才是重要的认识之源。英国哲学家艾耶尔也是分析哲学运动的一员,他认为形而上学方面表述无法用经验证实,根本谈不上真假,是毫无意义的呓语,包括道德、艺术、宗教方面的表述。比如“杀人有错”,它无法接受任何形式的验证,只是表达了一种情绪。
桑德·李进而断定:“分析哲学家认为,因为感官体验是可靠的,因此追求快感是有意义、可以理解、值得一试的行为。如果不加选择地应用他们的这种标准,就会使人拒绝伦理道德而寻求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列奥波德的哲学观点与享乐主义完全相容,列奥波德说他写过一本关于实用主义的书,更是证明了这一点。”这一结论有违分析哲学家的真实立场,因为如果他们将逻辑实证主义贯彻到底的话,在伦理和政治问题上,原则上我们做出的决定是无法得到合理辩护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也无法令人信服地得到论证。
伍迪·艾伦与其他哲学家
《伍迪·艾伦与哲学》一书的副标题为“你说我的谬论一无是处”,出自电影《安妮·霍尔》,片中麦克卢汉说:“我的作品你根本没懂,你说我的谬论一无是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英语教授詹姆斯·华莱士说,要去分析这句话的含义,那就上了伍迪·艾伦的当了,艾伦在这儿想要的,就是给那些训练有素、自命不凡、一定要给言语弄出点意义来的脑瓜里制造混乱。“他告诉我们,在一个错乱的世界上认知的局限,告诉我们在一个相对论的、不可知的世界上,绝对主义有多荒谬。”
如华莱士所说,伍迪·艾伦的俏皮话多数遵循一个特定模式:读者先看到一段郑重其事的论述,然后惊愕地发现这么严肃的话题焚琴煮鹤地跌落到世俗的、更易懂的层次。他先搬出抽象的、纯哲学的或心理分析的论述和问题,然后又用古怪但具象的图景,或者现实与生计的提示——经常是对食、色、财的需求和欲望——来削弱这种抽象思辨。比如,“我想归根结底,问题就在于我憎恨现实,真的。可是你也知道,我们偏偏只有在现实里才能好好吃顿牛排。”“要是什么都不存在,一切只是幻影可怎么好?要是这样我那块地毯绝对买亏了。”“要是有上帝,怎么会有纳粹?我怎么知道为什么有纳粹,我连开罐头刀的原理都不知道。”华莱士说,这些俏皮话的深意是,告诉读者,宇宙不是一个有条理、好理解、成系统,从根本上能弄明白的地方,想在知识或哲学意义上理解宇宙是痴人说梦,而且说白了,还是生存需要占头一位。
美国克雷顿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谢洛德·艾布拉姆斯认为,伍迪·艾伦和福柯的观点一致:活着就等于让人盯住和盯住别人,“在摄影机、镜子和每日心理分析构成的无尽迷宫里,通过自我重新阐述实现被监视对象的重建是唯一的出路。以尼采式的方法,对自身进行身体和语言上的实验,夺回对自身主观阐述的控制权,创造自己的私人形象。换言之,走出迷宫的唯一途径,就是待在里边”。
美国马凯特大学哲学副教授詹姆斯·索斯说,伍迪·艾伦在影片《曼哈顿》里描绘情感变化,用电影的方式呼应了亚里士多德的情感理论。亚里士多德声称,理智与情感彼此冲突的看法并不正确,纯粹理性的智慧或完全非理性的情感都不存在,情感会影响人们的判断,情感总是带有某种对世界的认知倾向。他在《修辞学》中说:“当人们感到友善与宽慰,他们想到的是一回事;当他们感到愤怒或敌意,想到的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或者同一件事中人的不同状态下会有不同的强度:当他们感觉到前来接受判决的人是友好的,即使他有错,他们也觉得不过是小错;若他们感到敌意,看法就相反。”
情感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感知,理智却不足以动摇情感,索斯举例说:“如果我相信飞行是安全的,我就不该害怕坐飞机,但显然事情没那么简单。也许并不能拿一个论点来改变情感,因为情感本身有自己的论点。”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美德没有成为人的习惯,光靠理论并不能使人变得善良。
如果情感并非总能听从理性,我们怎样能改变情感?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关键是形成习惯,而童年是形成习惯的时期,再往后,能塑造我们的性格的,就是音乐。伍迪·艾伦展示了音乐如何能改变人的性格。《汉娜姐妹》中的荷莉最初听摇滚乐,不听歌剧和爵士乐,后来试镜的时候她选择演唱了一首《我很老派》,她与米奇在唱片店重逢时,她正在爵士乐区,手里拿的是两张歌剧音乐专辑。“她新养成的音乐趣味反映出她生活的稳定,证明她具备了爱情成功的道德品质。”■ 艾伦哲学研究伍迪哲学剧情片爱情电影喜剧片美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