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知论宣言
作者:薛巍(文 / 薛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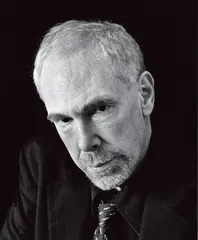 ( 罗恩·罗斯鲍姆 )
( 罗恩·罗斯鲍姆 )
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的东西
每年的里斯讲座一共有四讲。马丁·里斯第三次讲座的标题叫《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的东西》。演讲开始前他提醒说,这一次主要讲的是猜测性的边缘科学,他要讲的一些东西只是猜测性的,不是权威性的。
有听众说,今年的里斯讲座是历年最为有趣的一次。马丁刚开始就开了一个玩笑:“在努力准备今天要讲的东西时,我有一个幻想。假如我有一台时间机器,我能够快速地进入未来,打开收音机,收听这次讲座,做笔记,然后回到现在,写讲稿。可是,显然没有这样的应急之道。物理学家们可以自信地说,时间机器永远都只能是一种虚构。因为改变过去会导致悖论——如果你杀掉你的祖母,这既违反逻辑(你就不会出生),也违背道德。”
爱因斯坦断言,关于宇宙,最令人不解的是,它是可以理解的,他有理由感到惊奇。我们的心灵,进化到能够对付在非洲大草原上的生活,也能理解原子的微观世界,以及宇宙的广阔。那么,还有没有永远都会让我们感到困惑的科学问题,一些超越了人类理解能力的现象?
“不同的科学经常被比作一幢高层建筑相连的楼层——物理学在一楼,然后是化学、细胞生物学,一直到心理学,经济学们在阁楼。相应的,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也在增加——原子,分子,细胞,有机体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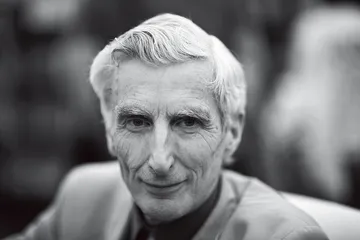 ( 马丁·里斯和他的新书《我们的最后时刻》 )
( 马丁·里斯和他的新书《我们的最后时刻》 )
“但是这一类比在一个关键方面并不成功。对一幢大楼来说,不稳固的地基会危及上面的所有楼层,但处理复杂系统的更高水平的科学不会受到不稳固的基础的危害。亚原子物理学的不确定性跟生物学家们无关。”
马丁举例说:一只信天翁在南方的大海游荡了1万英里之后回到它的巢穴,这是可以预见的,但不可能通过把信天翁看做原子的组合而计算这种行为。一切东西,不管有多么复杂,都是由原子组成的,遵守量子物理学的方程。但是即使可以列出这些方程,它们却并不能给出科学家们寻找的答案。每一门科学都有其独立的概念和定律,还原论在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但是它几乎没有用处。他说:“生物学、环境和人类科学方面的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因为很难阐明它们的复杂性。不是因为我们对亚原子物理学理解得不充分,你不能通过拆开一只手表来理解时间的本质。”
人类不只是一种灵长类动物:我们很特别,我们的自我意识和语言是一种质的飞跃,为文化进化、带来科学和技术的多种专门知识的积累创造了条件。“但我们理解不了现实的某些方面——统一的物理学或意识理论——可能就完全是因为它们超出了人脑的能力,就像爱因斯坦的理论会难倒一只黑猩猩。”
里斯在这一讲的最后说:“自达尔文以来,我们就知道了进化的过去惊人的时间跨度。很多人认为,我们人类是地球上的进化之树的顶点。但对天文学家来说,这并不可信,因为他们知道延伸到将来和过去的巨大的时间地平线。我们的太阳形成于45亿年前,但它还能燃烧60亿年。宇宙的膨胀还将继续,也许永远继续下去,变得更冷、更空。如伍迪·艾伦所说,永恒非常漫长,尤其是在走向结束的时候。因此,即使地球上只有一种生命,在地球或其他地方,仍然有后人类进化的余地。见证太阳毁灭的不会是人类:那将是跟我们不同的存在,就像我们与虫子的不同。我们无法想象他们会有怎样的力量,但仍然有他们做不了的事情,比如回到过去。因此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知道什么。”
无知的乐趣
里斯对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度的断言看上去令人很惊讶。但60多年前,罗素就在《西方哲学史》的绪论中写道:“思辨的心灵最感到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的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不再像它们在过去的世纪里那样令人信服了。”
罗素说,哲学本质上就是一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他说:“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和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典型的哲学问题包括:世界是分为心和物吗?心物之间是什么关系?宇宙有没有统一性或者目的?
罗素提出了正确面对不确定性的态度:“科学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能够知道的事物,但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很少的,而我们如果竟忘记了我们所不能知道的是何等之多,那么我们就会对许多极重要的事物变得麻木不仁了。在鲜明的希望与恐惧之前而不能确定,是会使人痛苦的,可是如果在没有令人慰藉的神话故事的支持下,我们仍希望活下去的话,我们就必须忍受这种不确定。教导人们在不能确定时怎样生活下去而又不致为犹疑所困扰,也许这就是哲学所做出的主要事情了。”
爱尔兰散文家罗伯特·林德曾经写过一篇《无知的乐趣》:“对不论是什么事进行思索,都会使我们心醉神驰。我们思考的可能是死后的归宿,也可能是一个据说曾经叫亚里士多德为难的问题:为什么从中午到午夜打喷嚏是件好事,而从午夜到正午打喷嚏却预兆不幸?我们所知道的人生最大乐趣之一,就是逃遁到无知中去寻找知识。无知的乐趣,就在于探索问题的答案。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这种乐趣,或者以武断的乐趣取代它,也就是说,以能解答问题而沾沾自喜,他也就开始僵化了。”
有时,我们宁愿处于无知状态。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帕谢在《哲学家的休息》一文中说,对于足球比赛,任何人都不会先知道结果,甚至上帝也不会先知道结果。即使存在着一个骗局,也可以不无道理地认为,骗子未必能让比赛先成定局,他也必然要在幕后等待着,看看一切是否按照预谋进行。在1937〜1938年莫斯科审判中,斯大林专门准备了一间特殊房间,他可以从那里观望法庭开庭审判的进程。他想让敌人当场出庭,带着其自己的感受和潜在的性格力量出庭。“有可能的是,他就像某些关于自由意识论解释中的上帝一样,不得不让一小部分认识能力逃离他自己的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知道事情的结果这一事实有助于加强在场者(现在)的重要性,因为这种不知可以保持集中的注意力并处于一种悬念状态。”
近来西方兴起了一批新无神论者:理查德·道金斯出版了畅销书《上帝的迷思》,丹尼尔·丹内特出版了《破解魔咒:作为自然现象的宗教》,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出版了《上帝并不伟大》。
美国学者罗恩·罗斯鲍姆在《不可知论宣言》一文中说,新无神论是一种有神论——它跟正统宗教一样以信仰为基础。无神论者展示了一种轻信的、幼稚的信仰,信仰还没有证据支持的确定性,确定他们能够或以后能够解释宇宙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存在。面对为什么有某物存在而非空无一物这一问题,无神论者相信科学最终将告诉我们答案。这一问题是一个根本的谜,使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的哲学家们和神学家们为之着迷。罗恩说:“近来科学家们试图用多元宇宙和充满量子可能性的真空来回答这一问题,在我看来都没有说服力。我接受新无神论者对宗教和神学的大部分批评。我只是不能接受把科学变成一种新的宗教,认为它能回答一切问题,目前并非如此,也许永远也做不到。无神论者没有证据证明,科学能够解决为何有某物而非空无这一问题。仅仅因为其他困难的问题被解决了,并不意味着所有困难的问题都能解决。无神论者跟托马斯·阿奎那一样迷信,他试图用逻辑证明从空无中创造的可能性。他最终的解释需要一个处于时间和空间之外的超级存在,但没有解释这个没有原因的原因是从哪儿来的。”
罗恩希望复兴不可知论。他认为,不可知论之所以失宠,是因为新无神论有一种富有魅力的、欺骗性的反叛姿态,而不可知论只有不那么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的谦卑。他说:“不可知论是一种激进的怀疑论,怀疑确定性的可能性,反对无神论和有神论没有根据的确定性。”“不可知论”这个词是达尔文的追随者赫胥黎创造出来的,他这样定义:“这一原则也许有多种表述,但它们都可以归结为一点:一个人除非他能够提出证明,符合逻辑地证实其确定性,不然说他能确定某一命题的客观真实性就是错误的。”赫胥黎最初提出不可知论是为了反对宗教的主张,罗恩认为,它也适用于科学无所不知这一主张。■ 科学宣言不可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