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错误正名
作者:薛巍(文 / 薛巍)
 (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错误可以用我们生活于时间和空间中来解释:因为我们受到一套特定的坐标的约束,我们不能超越它们,以鸟或者上帝的眼睛把现实看做一个整体 )
(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错误可以用我们生活于时间和空间中来解释:因为我们受到一套特定的坐标的约束,我们不能超越它们,以鸟或者上帝的眼睛把现实看做一个整体 )
误判是比赛的一部分
凯瑟琳·舒尔茨是《民族》、《滚石》和《石板书》杂志的撰稿人。《纽约时报》书评人德怀特·加纳说:“凯瑟琳·舒尔茨和大卫·弗里德曼的书虽然叫《犯错》和《错误》,但它们不是格林斯潘的传记,也不是对搜寻萨达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记录。舒尔茨的书是非常有趣的哲理性思考,思考为什么犯错是一种人道的、勇敢的、令人向往的人性特点。”
舒尔茨在书中说:“我们犯下的所有的错误中,关于错误的看法也许是我们的元错误:我们搞错了犯错的内涵。犯错不仅不是智力低下的表现,而且对人类的认知能力来说非常关键。犯错不仅不是道德上的缺陷,而且它跟我们最人道、最光荣的特点密不可分:同情、乐观、想象、确信和勇气。它不仅不是漠不关心和不宽容的标志,而且是我们学习和变革的重要部分。如富兰克林所说,错误是观察正常人性的一扇窗口,观察我们能够想象的心灵、我们无限的能力和我们丰富的灵魂。最终是错误而非正确能告诉我们,我们是怎样的人。”她感兴趣的是错误这一概念和犯错的经历:我们如何看待犯错、犯错后我们心理上的反应。
舒尔茨指出,认为错误可以被清除会导致可怕的、反动的冲动,如大清洗。她注意到,我们特别热爱正确,高兴地以为我们近乎总是正确。“正确怎么会那么有趣?毕竟,在快感中它最多只能排在第二位。不像生命中的其他乐趣——巧克力、冲浪、接吻,正确没有生理基础,跟我们的欲望、肾上腺、大脑的边缘系统和我们神魂颠倒的心都没关系。然而,正确的快感是无可置疑的、普遍的、几乎是没有差别的。我们不会乐于跟任何人接吻,但我们在任何方面弄对了都会很享受。不管是猜对了一只鸟的种类,还是猜对了同事的性取向。
“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过得很顺利,这表明我们弄对了很多事。有时我们对得非常了不起:原子确实存在(在现代化学出现的几千年之前古代的思想家们就提出了这一假想);弄对了阿司匹林的疗效。它们证明了我们是聪明的、有能力的、值得信任的、跟环境是协调的。更重要的是,它们使我们活着。我们的生存依赖于我们对周围的世界做出正确结论的能力。搞对了的体验对我们的生存来说是必需的,使我们的自我得到满足,是生命中最低廉的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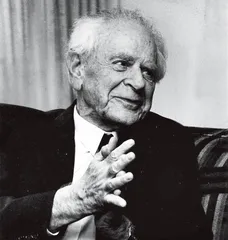 (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
(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
体育迷都会预测比赛结果,一旦猜对了比分便很满足。美国《体育画报》记者乔·波斯南斯基说:“超级碗的乐趣在比赛前的一周,一旦真的开赛了,故事飞快地变得越来越平淡。但在比赛即将到来的时候,所有的故事,所有的角度,所有关于会发生什么的不同版本,这些95%都是错的,但它们却构成了95%的狂喜。在体育比赛中、人生也是如此,大部分时间,事情的结果不会是你以为的那样。如果真是那样就很枯燥了。”
在预测比赛结果时,职业体育记者会比一般人预测得更准吗?波斯南斯基说:“也许体育记者通过跟运动员和教练等局内人交谈能获得更多洞见,但事实上,记者并不比一般人错得更少。”
 ( 凯瑟琳·舒尔茨 )
( 凯瑟琳·舒尔茨 )
如何更准确地预测比赛结果呢?“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能说的一点就是,要努力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1995年去看超级碗时,是圣地亚哥电光队对旧金山49人队,从一开始就很清楚49人队会打败电光队,他们要强出许多许多。但开赛前一周里,所有人都说,这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你看到电光队的队员显得都很自信,听到他们在房间里说他们会使用某种秘密武器,慢慢地你认为比赛的结果会有惊喜发生。但结果49人队完胜。你大部分时间都是正确的,但你接受了那些信息,开始忽视那些重要的东西。我认为你越是坚持从宏观的角度判断,做出正确预测的概率就越高。”
体育比赛中另一个跟错误研究有关的是裁判的误判。令这个问题变得复杂的是现在可以通过录像回放来审核裁判的误判。这种做法是否应该推广?波斯南斯基表示质疑:“体育迷搞不清楚立即回放比赛画面是不是太过了,这是一个大问题:人犯下的错误是不是应该继续作为体育的一部分而存在下去。有时它让比赛更完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把一些人性化成分拿走了。我反对在橄榄球比赛中回放,因为我认为那会改变比赛的性质。但当你知道正确的判罚时,又没有理由说坚持错误的判罚。体育跟合理性有关,只要有人看着电视说裁判该吹哨的时候没吹,就不应该置之不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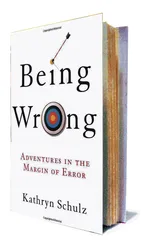 ( 作品《犯错》 )
( 作品《犯错》 )
不完全归纳
凯瑟琳提出,我们会犯错,是因为我们大量使用归纳推理。“当你凌晨3点在家里听到奇怪的声音时,你会报警;当你的左臂抽搐时你会去看急诊;当年看到桌子上爱人的偏头痛药时你会立刻开启咖啡机,关掉电视。在这些情况下,你都运用了归纳推理。在这些情形下,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去找证据。由于归纳推理,我们能够立刻形成想法,相应地采取行动。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们越来越认为,归纳推理是人类所有认知的基石。学习语言、把世界上的东西分类、把握因果关系,都要使用归纳推理。但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整个认知体系不可避免地要出错。归纳推理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会产生错误的结论,它们可能是对的,因此也可能是错的。”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个别,结论没有超出前提中的内涵。归纳推理是从个别现象中得出一般的结论,其间发生了跳跃,得出了新的东西,所以有犯错的可能。不管我们已经看到多少只白天鹅,也不能证明这样的结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卡尔·波普尔由此认为,科学不像培根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仅仅从特殊事件中就可以归纳出来,并且绝对可靠。他说归纳法只是神话,归纳方法认为科学假说来自观察。但波普尔说,是观察来自假说,先有了假说,有了一定的目的,才知道观察什么。我们的科学知识是通过未经证明的预言,通过猜测,通过对我们问题的尝试性解决而进步的。科学包含错误,要经受经验的检验,这不是科学的缺点,而恰恰是它的优点,对一个理论的反驳或证伪都是使我们接近真理的前进一步。托马斯·库恩进一步提出,在一种科学范式崩溃、新的范式降临时,总会出现众多相互竞争的假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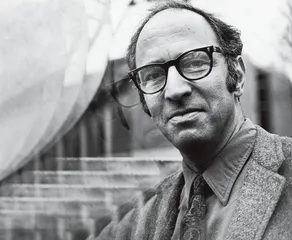 ( 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说,在科学范式新旧转换的时候,会出现多种相互竞争的假说 )
( 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说,在科学范式新旧转换的时候,会出现多种相互竞争的假说 )
搞清楚我们会犯错的原因对我们来说很有帮助。首先,这意味着要认识到我们不能彻底消除错误。其次,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认为那些犯错误的人是懒虫、傻瓜或坏蛋。“如果错误是理性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你就不能通过妖魔化和羞辱来培养更可靠的飞行员、更优秀的医生、更安全的核电站操作员。”
凯瑟琳对很多传统观点都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辩驳,如幽默理论。犯错会很有趣。这是一个残忍但又无可辩驳的关联:别人的错误会非常、非常有趣。错误和喜剧在骨子里是相互交织的。2000多年来,作家、哲学家和评论家一直在努力理解幽默和错误的关系的本质。一个存在了很久的主张是,我们嘲笑那些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可以俯视的人。这就是关于喜剧的优越性理论,其最著名的提出者是霍布斯。根据霍布斯的观点,幽默源自“较之于别人或者我们自己先前的虚弱,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卓越”。按照这种优越性理论的逻辑,错误使我们发笑是因为他们使得其始作俑者显得愚蠢,因为使我们显得更聪明。在这种模式中,喜剧确认了我们的正确、别人的不正确。
凯瑟琳说:“优越性理论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在看到有人撞到特别干净的玻璃门时会发笑。但好像对喜剧来说,这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在关于大象的笑话中就没有优越性可言,年迈的父母的虚荣也不会让我们感到好笑。这种理论剥夺了幽默的两个核心元素,欢乐和轻松,代之以个人的恶意。”
她提出了关于喜剧和错误之间关系的一个更加宽厚的观点:我们笑话别人的错误不是出于得意,而是出于自我确认。有些思想家甚至提出,正规喜剧的意义就在于向我们展示我们犯错的方式。可以称这种观点为关于幽默的自我改善理论。伊丽莎白时期的评论家菲利普·西德尼说,喜剧应该“模仿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错误”,差不多100年之后,喜剧作家莫里哀说:“喜剧的责任是通过逗乐人们来纠正他们。”■ 错误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