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在怎样改变我们的大脑
作者:薛巍
卡尔
卡尔现在51岁,曾经是《哈佛商业评论》的编辑,他以前对技术革命的态度相对中立,但现在他作为哈佛大学英美语言文学硕士所推崇的价值占了上风。在书中他明显推崇文学和哲学。我们把在线百科全书和谷歌当做具有无限存储能力和处理能力的公用大脑,但卡尔指出,搜索引擎还无法完全复制人脑的可塑性和工作机制。
他在书中回顾了各项技术引起人们的担忧的历史。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宣布要驱逐诗人。乍看上去这种提议显得专横粗暴,其背后的原因是,柏拉图把诗歌当成古希腊口述传统的代表。荷马史诗是古希腊人保存和传承知识的方式。但柏拉图认为新的写字技术更加优越,因为它能够让知识的传承变得更有序,更有逻辑性。如文化学者瓦尔特·翁所说:“最终文字胜出了,但是高度艺术性的口头表演永远地遗失了。”
卡尔提出,网络造成的结果是,我们从网络得到的是知识的宽度,失去的是深度。他引用一位剧作家的话说,我们正在成为煎饼人,跟无限的信息网络连接后我们的知识变得又大又薄。我们正在失去阅读严肃作品所需的持续、深入思考的能力。美国人现在每天有8.5小时在使用电脑、电视和智能手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重新变成了数据处理器。“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回到文明演进的早期:我们在从个人知识的耕种者变成数字数据丛林里的打猎者和采集者。”
卡尔指出,过去20年来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人脑是有弹性的,像我们的肌肉一样,可以通过锻炼加以改变。但认知能力的发展是一种零和游戏,大脑越是被用于浏览、网上冲浪和持续的低级的选择,用于深入思考的部分就会变得越弱。进而,我们得自遗传的特性使得我们特别容易注意力涣散,这是一种有利于在荒野中生存的优点,我们很难集中注意力,它跟我们大脑的天性相反。“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深入思考是有可能的,但那不是这种技术所鼓励或者会奖励的思维方式。”相反,它倾向于把我们变成实验室里的小白鼠,经常按一下拉杆,得到一点社交或理智上的回报。
卡尔引证了很多神经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但有些专业人士不同意他的结论。神经科学家、博客作者约拿·莱尔评论说:“卡尔忽略未提的是,大部分科学证据表明,网络及相关技术对大脑有好处。比如,关于视频游戏对认知的影响,结论是游戏能显著提高各种认知能力,从视觉感知到持续的注意力。这一惊人的结果使科学家提出,哪怕是最简单的电脑游戏也能显著提高处理信息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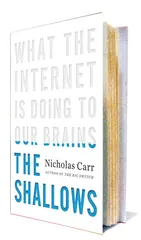 作品《浅薄:网络在怎样改变我们的大脑》
作品《浅薄:网络在怎样改变我们的大脑》
6月10日,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夫·平克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网络技术不但没有让我变傻,而且是唯一使我们保持聪明的东西。”他论证道,从经验层面说,如今科学家们经常使用电子邮件,很少接触纸张,不用PPT就不能演讲。如果数字媒体对智力有害,科学水平就应该在降低。但新发现层出不穷,科学的进步眼花缭乱。哲学、历史和文化批评等精神生活也是蒸蒸日上。
从理论层面说,神经元具有可塑性,并不意味着大脑是一团会被经验塑造的黏土。经验改变不了大脑基本的信息处理能力。“速度课程一直声称能够做到这一点,但如伍迪·艾伦所说,他在速度课上读《战争与和平》之后只知道它写的是俄国。媒体批评家好像认为大脑会染上它吸收的东西的特性,信息就如吃到的东西。就像原始人相信吃凶猛的动物会让他们变得凶猛,他们认为观看快切出来的摇滚视频会让大脑变得快切,读微博会把思想变成微博的条目。纷至沓来的信息会干扰我们的注意力或令人上瘾,但解决方法不是悲叹技术而是加强自我控制。”平克说。
6月12日,卡尔在博客上对平克的批评做出了回应:“平克承认我们的大脑会适应环境的变化,但他认为我们不需要予以关注。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会影响大脑,我们就不需要关注某个东西如何影响大脑。平克这么说另有原因。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人脑的适应能力,这对平克的进化心理学和行为遗传学是一种挑战。大脑适应性越强,我们越不受制于得自遗传的行为模式。”■ 怎样改变大脑我们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