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论邪恶
作者:薛巍(文 / 薛巍)
 ( 朱利安·巴吉尼 )
( 朱利安·巴吉尼 )
不要误以为邪恶很有魅力
英国《哲学家杂志》主编朱利安·巴吉尼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说:“英国文学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出版了《论邪恶》,哲学家茨维坦·托多罗夫出版了《用记忆治疗邪恶》,不到一周后,挪威哲学家拉斯·史文德森又出版了《邪恶的哲学》一书。也许这种对邪恶的兴趣的复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虽然邪恶作为一种观念也许已经不再流行,但在现实中它从未曾远去。面对屠杀、虐待和对生命公然的漠视而不用到这个词会显得非常荒谬。”
英国哲学家格雷林评论说:“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字风格有些含糊,但很风趣,为了考察邪恶,他踏上了一条复杂的旅程,就像一个弹球的路线,在西方文化的电话簿的条目中前前后后跳来跳去,从戈尔丁到圣奥古斯丁,从《麦克白》到伪狄奥尼修斯,从原罪到大屠杀,从莎士比亚到弗洛伊德,从撒旦到托马斯·曼,从阿伦特到亚里士多德,等等。”
伊格尔顿把邪恶定义为一种生存状态。怎样的一种状态?不如看他认为哪些算邪恶。纳粹邪恶吗?伊格尔顿说,只有希特勒本人是真正的邪恶。“9·11”恐怖袭击是邪恶吗?显然不是,它是缺德的,但是可以解释的,而且不管怎样,美国人为了把自己的方式强加给世界,杀害了更多人。因此邪恶是非理性的存在状态。但进一步的考察表明,邪恶还是一种非存在,它跟虚无、灭绝和死亡有关。
伊格尔顿写道:“邪恶的人讨厌人类存在的混乱,他们宁要完美的死亡而不要鲜活的生命。邪恶的人是如何努力说服自己他们是活着的呢?答案既简单又令人胆寒:通过撕裂他人。他们唯一不像死人的是,他们从破坏中获取快感。纳粹是纯粹的虚无主义者,热爱死亡和灭绝。如果说他们是疯狂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也是纯粹的犬儒主义者,乐于打碎一切人性的意义和价值。纯粹的邪恶憎恨人类的存在这一事实,想把它从地球表面抹掉。它在人性中只看到可怜的假象,它想证明,人类的生命像它们一样空洞。邪恶是完全无意义的,疯子有时候会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但当正常人为破坏而破坏时,我们面对的就不只是不道德了。”
 ( 特里·伊格尔顿的作品《论邪恶》 )
( 特里·伊格尔顿的作品《论邪恶》 )
魔鬼最有腔调。为什么邪恶有着无法抵挡的魅力?美德令人敬佩,但是让我们觉得性感的是罪恶。如果能跟费金一起喝咖啡,没人愿意跟奥利弗·退斯特一起喝橙汁。如王尔德所说,不觉得狄更斯笔下圣洁的小内尔之死滑稽有趣的人一定是铁石心肠。我们都喜欢向一个恶棍发出嘘声,如(毒舌评委)西蒙·考威尔。流行文化痴迷于食尸鬼、吸血鬼、僵尸和恶魔。没有什么比被吓得半死更快活的了。
罪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显得如此吸引人的?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当美德开始显得枯燥的时候。可以把这归罪于清教徒式的中产阶级,是他们重新把美德定义为节俭、慎重、谦恭、节制、纯朴和勤劳。不难看出为什么有人更喜欢僵尸和吸血鬼,美德变得消极和约束。如诗人奥登所说,十诫就是观察人类的行为,然后加上一个不许。但美德并非一直如此枯燥。对一些古代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关于知道如何享受的问题。它意味着学习怎样去培育自己,学习如何充分发展自己的人性。照他看来,你必须变得擅长做人,如演奏低音号或者忍受派对上的无聊。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美德跟幸福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做一个有美德的人是获得幸福最快的路线,善良的人就是优秀的人。那些杰出人士——圣人——是在生活上技艺超群的人,是美德方面的帕瓦罗蒂和鲁尼。美德是一种生活乐趣,是力量和兴致的来源。至于十诫,它跟享受丰裕的生活有关,而不是跟缴税和准时去上班有关。
 ( 特里·伊格尔顿 )
( 特里·伊格尔顿 )
在这种哲学看来,邪恶的人是那些没有掌握生存技巧的人,就像一个永远学不会打扑克的人。他们处于缺乏、不足的状态,没有真正地活着的能力。邪恶的人并不真的存在,他们是真正的人未完成的草图。就像食尸鬼,他们漂浮在生和死之间,陷入了一种使他们与人的世界隔绝的过渡场所。他们也许看上去像人,但跟恐怖片里的外星人一样,这只是一种假象。
邪恶也许看上去很炫,很吸引人,但如果你戳它一下,它就会化为乌有,它是虚假的。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观看艾希曼的审判时意识到,邪恶最惊人的一点是它的平庸。艾希曼看上去就像一个疲惫的银行职员,而非一个恃强凌弱的恶棍。他是一个官僚,官僚不喜欢凌乱,邪恶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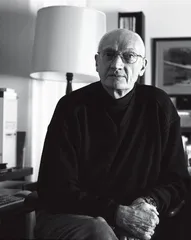 ( 理查德·霍洛维 )
( 理查德·霍洛维 )
踩扁某个东西会显得很有创造性,像小孩感到的那样。对一些人来说,用一块砖头砸烂玻璃窗比设计玻璃窗有创意得多。我们都能从破坏行为中得到快感,这是我们爱看暴力影片的原因之一。只有真正这么干、为破坏而破坏的人才邪恶。令人感到释然的是,这种事情很少发生,之所以很少发生,一个原因是为了拒斥美德。邪恶的人必须首先体验过美德,不然他们就不是坏人,只是无知。但任何知道人性爱的滋味的人都不会认为它毫无意义。严重伤害和剥削他人的人不是一般的邪恶,很可能是,他们从来就没体验过爱。
如巴吉尼所说,伊格尔顿把邪恶定义为“最没有意义的行为”,即单纯为作恶而作恶的行为。但由于他认为这种行为非常罕见,不应该让我们为它而辗转反侧,结果他不得不去讨论很多只是算缺德的事情。为了至少有一些合适的邪恶可以讨论,伊格尔顿被迫使事实变得适合他的定义。比如为了使大屠杀算作邪恶,他不得不说那是一项没有实际意义的行动,如果只是把大屠杀视为一种独特的、恶魔般的越轨行为,我们就不能从对它的记忆中学到什么。
为何人们不再虐待动物?
理查德·霍洛维分析了伊格尔顿指出的邪恶的另一个来源。伊格尔顿是一位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大部分暴力和不公是物质力量的结果,而不是个人邪恶的天性造成的。跟这种唯物主义相反的是道德主义,认为善行和恶行独立于它们的物质背景。
伊格尔顿认为,大部分不道德行为都跟结构和机构密切相关,因此完全不是与此有牵连的个人的过错。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人们不再虐待动物,这种现象跟为获取廉价食物而产生的庞大的、工业化残杀动物的体系勾连在一起。
伊格尔顿呼吁我们看清人性的状况。我们是有双重性的生物,又能行善又能作恶,而且往往掩盖我们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尤其是在机构或者体系领域。我们在集体或机构中,伊格尔顿所说的物质中最坏。我们独自一人时做梦也做不出来的行为,我们会以存在距离的名义做得出来。艾希曼没有亲手杀害一个犹太人,但他会确保开往集中营的列车准点开出。
伊格尔顿的政治哲学是跟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对立的现实主义。这种立场认为,我们的命运并非彻底被决定了的,无法改善我们的处境。我们并非无力改变我们的现状,但我们这么做的时候要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令人沮丧的历史。
保守主义者本质上是悲观的。他们认为,人类并非真正道德的物种,容易受到邪恶的诱惑,但也能够做到善良。他们大部分是堕落、懒散的人,需要不停地惩罚和权威地存在。由此保守主义者强调机构管制有罪的人任性的意志和情感。保守主义忠实于传统的缺点是,他们没有把关于堕落的理论用在他们树立起来阻拦混乱的机构之上,拒绝承认他们建立起来阻止混乱的机构会变成搞破坏的工具。
霍洛维说:“如果说保守主义者相信原罪但不相信救赎,自由主义者就是相信救赎但不相信原罪。”他们缺少对生命的悲剧感,因为他们往往认定困扰我们的邪恶不是来自我们自身,而是外界对人类幸福的妨碍,除掉这些外界的障碍,天堂就将降临。伊格尔顿要对自由主义者说,邪恶确实存在。他认为,自由主义对邪恶加以降格,会导致不能对邪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他同样也抨击了理查德·道金斯等新无神论者没有头脑的进步主义,自满地认为我们都已经变得更加和善、更加文明了。
激进主义者努力维持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平衡。一方面要求非常现实地看待人类堕落的深度和韧性,另一方面,相信这种堕落还没有达到无法改变的地步。激进主义没有陷入绝望是因为他们的唯物主义。■ 伊格尔顿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