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福利国家
作者:薛巍 ( 《战后欧洲史》凯恩斯
)
( 《战后欧洲史》凯恩斯
)
为什么自由主义战胜了福利国家理论?
身患绝症的托尼·朱特批评说,现在的欧美政治家缺乏勇气。社会民主党人不敢提出成本更高的社会目标,跟他一样出生于1948年前后的小布什、克林顿、布莱尔、布朗生活的时代实在太平,以致不敢做出不受欢迎的选择。
《战后欧洲史》的主题之一是,最初,凯恩斯的理论战胜了哈耶克的理论,战后西欧国家选择通过建立福利国家来消除政治极端主义,但是后来是自由主义占了上风。
对当今英美经济思想最有影响的是5个奥地利人:米塞斯,哈耶克,熊彼特,卡尔·波普和彼得·德鲁克。他们都为他们的祖国奥地利在两次大战期间的灾难苦苦思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浩劫和维也纳短暂的社会主义实验之后,1934年奥地利发生了一场反动政变,4年之后又遭纳粹入侵并被占领。此后,他们都被迫流亡,毕生都在考虑这一问题:为什么自由主义的社会崩溃了,让位给了法西斯主义?他们的回答是:左派试图向奥地利引进国家指导的计划、政府提供的服务和集体经济活动未能取得成功,这不仅证明这一模式是一种幻觉,而且直接导致了对它的反动。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保卫自由主义的最佳方法是把政府拒于经济生活之外。如果政府被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之外,政治家被禁止计划、控制和指导公民的生活,那么极端主义者就无法迫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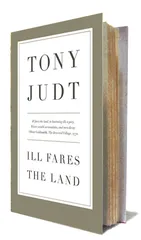 ( 《遭受苦难的土地》
)
( 《遭受苦难的土地》
)
凯恩斯也面对着同样的挑战——如何理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的事情,并阻止其重演。这位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成长于一个稳定、自信、繁荣、强大的国家。当时,他处在英国财政大臣这样一个有利位置,并参与了凡尔赛和谈,得以目睹他的世界的崩溃,他的文化的确定性也随之消失。凯恩斯也在考虑哈耶克等人提出的问题,但他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凯恩斯认为,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中应该得出的教训是,不确定性是一种腐蚀性的力量,会威胁到自由世界。因此应该增强政府对社会稳定的作用,不仅限于干预经济。
 ( 托尼·朱特 )
( 托尼·朱特 )
福利国家并不“淹死富人”,相反,虽然穷人感受到最大的直接利益,但真正长期的得益者是专业人士和商业中产阶级。到60年代,中产阶级有很多可支配收入。但到了70年代,自由市场理论再次出现,抨击大政府带来的不幸。
福利国家有一个悖论:它们的成功将逐渐减低它们的吸引力。老一辈知道30年代的苦难,所以热心于保存税收、社会服务和公共供应,将这些视为防止回到可怕的过去的保障。但他们的后代忘记了最初为什么要寻求这种安全。再者,在半个世纪前自由主义理论占统治地位时他们还未出生,未能亲身体验到自由主义带来的不利后果,所以很容易被自由市场理论迷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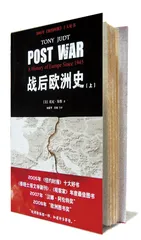
西欧经历了福利国家理论的反复,美国则是从头到尾都对福利国家不感冒。一个世纪前,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曾经写过一本《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书。朱特说:“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有些跟美国的面积有关:在这么大的帝国,共同目标很难去组织和维持。还有文化因素,包括美国人对中央政府的怀疑。”
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在小的、同质的国家有效并非偶然,在这样的国家,不信任和相互怀疑不那么严重。愿意为别人得到的服务和好处付钱,这需要相信别人也会为你和你的孩子那么做。反之,移民和少数族群的出现改变了国家的人口构成,对他人的怀疑日益加深,对福利国家的热情降低了。福利国家遇到了严重的挑战,不再像以前那样自信了。
但即使如此,受到机能失调和不平等的困扰的美国也应该想象一个与此不同的社会,而“美国人好像失去了质疑当下和提供别的选择的能力”。英美等国在讨论公共事务时总是求助于经济学,过去30年间,在英语世界,当考虑是否支持某种提议时,他们问的不是它是好是坏,而是问它是否有效率。“这种回避道德考量、将自己局限于利润和损失问题的倾向并非人类的本能,而是后天获得的一种趣味。”
早就有人担心人们会把公共政策的考量只看做经济得失的计算。对商业资本主义最有洞见的孔多塞就预料到,在最贪婪的国家,自由将只是安全的金融运作的必要条件,人们会把挣钱的自由跟自由本身搞混。亚当·斯密说过:“钦佩或近于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或至少是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倾向,是我们道德情操败坏的一个重要而又最普遍的原因。”
为什么铁路不能私有化?
把公共政策的考量只看做经济得失的计算,就会认为私有化就是可行的。朱特说,因此过去30年间,西方政府沉迷于私有化。实现私有化的原因是,在预算紧张的情况下,私有化能省钱。如果政府拥有一个效率低下的公共项目或昂贵的公共服务——供水、汽车厂或铁路,它会努力将它们卖给私人买家,卖掉之后能马上给政府带来收入。转到私人手中之后,由于追求利润的动机,这些服务会变得更有效率。这样每个人都将得到好处:服务得到提高,政府卸掉了它管理不善的责任,投资者得到利润。
朱特说,理论上是这样,实践起来就不同了。过去几十年来,将公共责任转移给私人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好处。首先,私有化效率不高,大部分政府认为适合转给私人的东西都是亏本经营,不管是铁路公司、煤矿、邮政还是电力。因此要不打折出售,公共产品对私人买家是没有吸引力的。但如果政府贱卖的话,公众就会受到损失。
其次,这样做还有道德上的危害,私人投资商愿意购买低效公共产品的唯一原因是政府会消除或降低他们所遇到的风险。以英国地铁为例,政府向买家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不会蒙受巨大损失,因而削弱了能够提高效率的追求利润的动机。在这种有利条件下,私人至少跟政府一样没有效率。
第三个也是最显著的反对私有化的原因是,邮政、铁路、监狱等公共服务即使在私有化之后,仍然不能全部任市场左右,它们天然需要有人来监管。
今天在美国,如果你的缴税情况有问题,虽然是政府决定调查你,但调查是由私人公司来执行。政府把它们的责任外包给私人公司,在18世纪这被叫做税收外包。早期的现代政府经常缺少收税的手段,因而邀请私人投标,承担这一任务。政府拿到的钱会被打上折扣。
在法国的君主制被推翻后,人们普遍认为,税收外包效率很低。首先,政府找一个贪婪的谋求利润的私人来代表它,会破坏政府的可信度。其次,这样收上来的钱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收到的多,因为私人收税者会拿走部分利润。更严重的后果是,将政府的责任剥离,会降低政府在公众生活中的存在。“如果人们只跟私人机构打交道,渐渐的人们跟公共领域的关系就会变浅,对政府的效忠就会降低,从而失去一种跟其他公民共有的东西。”
朱特以铁路为例来说明,政府不能只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而决定将公共服务私有化。对人潮汹涌的火车站来说,私有公司能做得很好,没理由让国家在那里经营报摊或咖啡馆。但在铁路方面不能放开竞争,铁路跟农业和邮政一样,既是经济活动,也是公共产品。而且,你不能通过把两列火车放在铁轨上,看哪一列表现得更好来让铁路系统变得更有效率,铁路是一种自然垄断。难以置信的是,英国已经在公交方面确立了这种竞争,但公共交通的悖论是,它越优质,越没有效率。
向付得起钱的人提供服务、避开偏僻地区的公交系统能给它的拥有者挣到更多的钱,但国家或地方政府一定要提供无利可图的地方交通服务。不然,取消这种服务,短期的经济所得将被对公众长期的损害抵消。因此,竞争性的公交会提高公共领域的成本。
火车首先也是一种社会服务,如果只需要开通伦敦到爱丁堡、巴黎到马赛、波士顿到华盛顿之间的铁路,谁都能盈利。没有人愿意出钱兴建那些人们只偶尔乘火车去的地区之间的铁路,只有国家和地方政府来做。政府的补贴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总是低效的——让每个人自己开车比运行火车更便宜。但开通通往边远地区的铁路使群体感得以维持,不管花费有多高,它是整个社会拥有共同的渴望的象征。■
(文 / 薛巍) 国家福利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