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的艺术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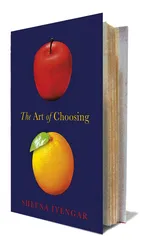 ( 《选择的艺术》 )
( 《选择的艺术》 )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要做出选择。不管是做什么工作,还是吃什么饭,我们都希望有所选择。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社会心理学博士希纳·杨格尔说,实施控制会让我们感到舒服。选择的欲望和需求是非常先天的、普遍的,在我们还不能表达自己想选择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做选择。研究发现,婴儿不仅表示他们想听音乐,而且渴望选择听什么样的音乐。
“世界领导人的选择应该是以10%的直觉确定目标,以90%的理性去实现目标。”普通人做选择时非理性的成分更大。书中说,在投票的时候,我们往往把候选人的外貌跟他们的能力画等号。位置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货架两端展示的商品比货架中间的商品卖得更多。在招聘面试中,第一位和最后一位候选人会给面试官留下更深刻的印象。雨的大小会影响人们是否叫外卖,如果开始下毛毛雨,许多人就会明显地想吃快餐,但是当雨下得更大时,人们就宁愿待在家里从冰箱里找吃的。
杨格尔在斯坦福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开始研究人们如何做选择。她研究选择对一群3岁孩子的影响,一半的孩子被允许玩房间里所有的玩具,另一半孩子被指定了几种玩具。刚开始她想当然地以为,能够自由选择的孩子会玩得更开心。结果表明,恰恰相反,被指定了玩具的孩子玩得很开心,能够自由选择玩具的孩子则不知所措、无精打采。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乔治·米勒在这一领域做了很多研究,他发现我们大部分人在做选择时,只能处理5到9件东西。当面临的选项太多的时候,做决定变得过于复杂,决定的过程就会延迟。
人们如何做决定跟他们的文化传统有关。美国人特别注重自由选择,日本孩子在做选择时则更喜欢听从父母的指导。两国养育孩子的方式就不一样。在美国,当孩子学习说话时,家长训练他们回答“你想吃哪种麦片粥?”到他们5岁的时候,问他们长大了想干什么。家长告诉孩子,他们需要学习做选择。大部分美国孩子最先学会说的词不是“妈妈”或者“爸爸”,而是“不是”。她自己的儿子两岁时学会说第一个词“还要”。日本家长不会问小孩长大了想干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小孩子还回答不了这一问题。
刚从加拿大移居到美国时,让她感到惊讶的一件事是,美国的医生会给病人提供很多治疗方案,让他们自己做选择。杨格尔认为,这样做并不是好事:“在治疗过程中,医生需要让病人有一种操控感。他们至少要感到自己受到关注,他们的利益得到了考虑。但应该由医生给出建议,因为在生病时病人很难想清楚最佳治疗方案。让一个对癌症一无所知的人选择如何治疗会带来很多问题。”

杨格尔去买指甲油的时候,两位营业员分别推荐芭蕾舞鞋色和淡粉色,她们说,前者更优雅,后者更有魅力。她对这种主观的区分不满意,便在学生中间做实验。20名学生,一半的人可以选择芭蕾舞鞋色或者淡粉色,另一半只能在瓶子上看到A和B。结果第一组有7人选择了芭蕾舞鞋色,认为它颜色更深、更丰富,第二组有6人选了淡粉色,还有人认为A和B颜色上没有区别。结论是,瓶子上的品名使指甲油的颜色更好看,或至少制造了有差别的感觉。对失明的人来说,她只想有一个对颜色的客观描述。盲人关心颜色的视觉属性,而有视力的人却根据外包装来评价颜色。盲人不关心品名,而视力正常的人是在视觉文化的背景之下做选择,别人给产品取了名字,使它们尽可能有吸引力。
杨格尔说,选择的艺术跟做出限定有关。方法之一是使做选择成为一种人际互动,借助别人的支持和智慧,让他们提供直觉和知识。另一个方法是给选项加以分类,比如,在刷墙的时候,不是考虑无数种颜色,而是从蓝色、红色和淡素色中选。“就像爵士乐,爵士乐手温顿·马沙利斯说,任何人都可以毫无限制地即兴演奏,但那不是爵士乐。也许我们要学习基本的作曲方法才能知道如何选择,这样才能创造出音乐,而不是噪音。”■(文 / 小贝) 选择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