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滨和他弟子们鲜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李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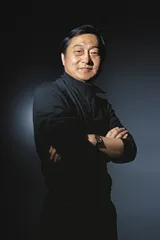 ( 姚滨 )
( 姚滨 )
赢在相爱
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短节目比赛,重新站在花样滑冰舞台上的申雪32岁,赵宏博37岁,已不再年轻。但是,当音乐响起,第一对出场的申雪、赵宏博依然给人们带来了惊喜。
“申雪、赵宏博与其他组合比最与众不同处,就是他们在冰上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化学作用,在场边看感觉就像他们二合为一。”由2005年开始为他们编舞的加拿大安省人劳瑞·尼科尔(Lori Nichol),向本刊记者坦言每次见到他们在冰上表演,都令她十分感动,“在短节目中,我为他们编了一首较为摇滚的小提琴弦乐曲《谁望永生》,就是想让评判和观众有新鲜感,更重要的是让申雪和赵宏博两人也有新鲜感。因为他们共舞了那么多年,很多曲目都试过,这乐曲会给他们一点惊喜。”结果,两人在短节目获得破纪录的76.66分,并且同以破纪录的216.57分勇夺金牌。
46岁的劳瑞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是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运动员,职业生涯最好成绩是获得世界职业滑冰锦标赛银牌,但现在她是花样滑冰界首屈一指的编舞师,是2010年加拿大冬奥会男子单人滑金牌得主莱萨切克(Evan Lysacek)、我国选手陈伟群,女子单人滑铜牌得主罗切特(Joannie Rochette)、世锦赛冠军卡罗琳娜(Carolina Kostner)以及浅田真央,甚至是已退役的关颖珊的编舞。在业内,她被认为是最善于在新的计分制度下,能够为选手尽量争取最佳分数之余,又能保留整个项目的美感。想请她编舞的花样滑冰运动员很多,但她只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员。
“虽然第一对出场承受很大压力,但是我们的心态很好,因为不占什么优势,我们的想法就是享受比赛。”赵宏博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参加职业比赛了,这个音乐说的就是我们自己。劳瑞在舞蹈中综合了我们以往多年的精华动作,我自我感觉很好,这也算是我和小雪互送出的最好的情人节礼物吧。”
 ( 编舞师劳瑞·尼科尔 )
( 编舞师劳瑞·尼科尔 )
自由滑比赛申雪、赵宏博是最后一对出场,他们之前,中国队“老二”庞清、佟健以完美的表演拿到了场上最高分,排名暂列第一。但是,出乎本刊记者想象,“老二”并不是当时赵宏博认为的争夺金牌的竞争对手。赵宏博说:“‘老二’能发挥成这样,我们已经预料到了。但是我们觉得,要拿金牌就是和自己竞争。自由滑之前,我问自己,怎么会出现失误呢?只要正常发挥我们的水平,冠军就是我们的。”
劳瑞说,申赵两人能胜过各国好手,除了高超的技巧外,全凭两人真心相爱,在冰面上让感情自然流露。“他们在冰上完全是忘我的真情表达。很多小动作如开场时喁喁细语,在一个周跳后轻抚对方,用一个眼神表达默契,完结后相互击掌鼓励,旁人看来都很贴心。很多组合是在冰上演出爱的动作,靠努力去培养默契,他们已经合作了那么久,一切都变得很自然。最重要的是,他们根本就是相爱,那种热情与爱的表达不用装不用演,就自然从细微的动作中流露出来,令评判及观众有深刻印象,我相信是这些令他们的项目分数如此之高。”加拿大滑冰协会顶尖运动员主管麦克·斯利普查克(Mike Slipchuk)亦认为,国家级选手比试中,技术层面其实大家都差不多,评分高低就是呈现在项目的艺术表达中。
 ( 张丹、张昊在2008年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答谢表演赛上 )
( 张丹、张昊在2008年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答谢表演赛上 )
事实上,在2009年5月申赵宣布复出时,他们并不被人看好。即使是教练姚滨,对他们的复出前景也没有明确的想法。“回来能怎么样?先试试看看。”反倒是老二老三,对老大的复出并不意外。“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在国外巡演的时候,我们经常联系,也知道他们一直在练习捻转,抛跳。毕竟,他们就缺一块冬奥会金牌。”张昊向本刊记者坦言。
复出前,赵宏博对申雪的父亲谈了自己的想法。“他针对自己的能力,分析了目前所有竞争对手的竞技状态,认为可以再打一下。”申雪的父亲申杰在首体宾馆的咖啡厅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他说,“我们起初是不同意的,宏博年龄偏大,身体有伤病。虽然这两年参加巡回表演没有放弃过训练,但毕竟不等同于系统训练。按他们的一贯表现,回去就得付出更多。年轻队员恢复期短,他们不一样,大体力消耗之后恢复慢,这么一天天积累下来是否能消化?而这个时期最容易受伤。”申杰的顾虑也是当时冬运中心很多人的顾虑,“中心领导考虑更全面,他们的技术难度在新规则下是否能承认?裁判是否认可?会不会觉得‘老了,怎么又出来了?’”
 ( 2009年,第十一届全运会冰上项目在青岛开战,庞清、佟健考察场地,进行适应性训练 )
( 2009年,第十一届全运会冰上项目在青岛开战,庞清、佟健考察场地,进行适应性训练 )
离开国家队两年,申雪和赵宏博的身体素质和有些动作比如抛跳和捻转质量并没有降低,只是在跳跃和体能上有点问题,成套也有些费力。第一次队里测试他们扔了(失误)三个动作,第二次两个。或许是对“老大”的自控能力比较放心,姚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老二和老三身上。
“第一个月我们自己恢复训练,第二个月姚教练带着老二、老三去美国编排了。第三个月因为训练强度大,我膝盖受伤了。第四个月,身上能疼的地方都疼了一遍,刚开始靠按摩恢复,后来必须靠针灸来减轻疼痛。”赵宏博告诉本刊记者,当时队内的格局是老三连续两届世锦赛第二,状态最好;老二虽然两届世锦赛不是最好的,但是在总决赛上获胜了,也有机会。“我们是最没优势的,两年没比赛了,是不是在吃老本?大伙都不看好我们。”赵宏博也很“自觉”,虽然老二、老三一如既往地尊重老大,但是他们很低调。“我们找了韩冰教练带我们训练,他是姚教练的助教,上冰的时候,我们和老二、老三是分开练的,我们和二线的小孩们一起训练。”之所以这么做,赵宏博说,是为了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最有希望的老二、老三。
反而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管理中心副主任任洪国,一直对申雪、赵宏博很有信心。任洪国和姚滨是同时代的花样滑冰运动员,他14岁进专业队,那时姚滨17岁。1995年,任洪国是花样滑冰队领队,姚滨的三对弟子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他对当时格局的分析与赵宏博想得不一样。“张丹、张昊和庞清、佟健也都是非常有名的双人滑运动员,但申雪、赵宏博退役后的两届世锦赛,金牌都是德国组合(萨维申科、斯佐尔科维)的,张丹、张昊拿了两个第二,庞清、佟健那时一直摇摆不定,因为他们的三周跳一直得不到裁判的认可。长短节目一共3个三周跳,不被承认十几分就没了,差10分怎么去竞争?!他们自己也挺苦恼的。张丹、张昊从名次上看还不错,表演方面与德国组合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只要德国人动作全成功,张丹、张昊拿金牌是很难的。当时我们就考虑让申雪、赵宏博回来,我们也相信他们肯定会回来,包括他们的宿舍,我们也一直在给他们留着,毕竟他们还有一个未圆的梦。我们也衡量了德国组合的水平,如果申雪、赵宏博回来,很有可能赢他们。”任洪国告诉本刊记者。
申雪、赵宏博复出后参加的第一站比赛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中国杯的比赛,他们以200.97分征服了裁判和对手,夺得冠军。这给了他们信心,也打消了很多人的疑虑。两周后,在美国站的比赛中,他们以201.40分再次夺冠。这一次,再也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了。“到了总决赛,我们已经是胜利者的姿态了。”说到这一句,赵宏博有些激动,“技术动作,音乐把握,什么都很好,我们没有表现出老态,裁判只会觉得这两人比以前更好,那为什么不给他们打高分呢?”
2010年冬奥会双人滑比赛,申杰自始至终一直在电视机前观战。短节目申雪、赵宏博拿了第一后,申杰就有感觉他们能最后夺金:“自由滑他们只要正常滑,德国那对组合就会出现闪失。比赛前德国组合的教练就宣扬,去就是要拿金牌。心态不好。”任洪国的分析也是如此,“去年总决赛输给申雪、赵宏博之后,他们就已经崩溃了。以前他们一瞪眼就能赢我们的张丹、张昊,申雪、赵宏博复出后两个分站赛都拿了冠军,总决赛是他们第一次跟德国组合对决,申雪、赵宏博又发挥得非常完美,这也给了对手很大的压力。冬奥会短节目,德国组合在自认为发挥很完美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赢,而且申雪、赵宏博又是在第一次出场的情况下拿到了这么好的成绩,他们几乎失去了斗志。所以导致了自由滑出现这么大的失误,这完全不是他们的真实水平。庞清、佟健之所以能发挥得这么好,也跟有老大在前面扛大旗有关。”
回首来时路
1992年6月23日,申雪和赵宏博第一次“拉手”。申杰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
拉手的时候,赵宏博已经和谢毛毛搭档拿到双人滑全国冠军和亚洲冠军,因为谢毛毛身体发育体重增加,赵宏博不得不更换女伴。在众多滑单人滑的女孩中,申雪并不是条件最好的。“没有参加过全国性的比赛,最好的成绩也就是黑龙江省少儿比赛第四名。长得不够好看,也不会化妆,经常把自己化得跟小熊猫似的。”申杰向本刊记者如此描述当年的女儿。能从市体校滑到市体工队就是申杰对女儿成功的定义。
观察到申雪和赵宏博的差距实在太大,姚滨连续两个多月住在体工队,白天给申雪和赵宏博上完两场冰上训练课后,晚上单独给申雪开了一堂课,专练单人滑。此时,姚滨是国家队教练。1988年,姚滨第一次以教练身份带队员参加冬奥会,他的弟子,21岁的李为和16岁的梅志彬依然排在双人滑“老末”。首次率队征战冬奥会铩羽而归,没有让姚滨打退堂鼓。“同样是人,人家老外能干出一番事业,我们为啥干不出来?”
姚滨埋头研究业务,自学英语翻译加拿大关于跳跃的理论教材。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先把中国双人滑的技术难度提上来。在摸索中,姚滨发现自己当运动员时其实全练拧了,于是大胆地推翻了以前的训练方式,开始针对冰上需要的肌肉在陆地上训练。“至今我手上也没有任何成型的外国双人滑教学版本,现在全是我自己总结出的一套。”姚滨告诉本刊记者。
申雪和赵宏博实际上是姚滨带的第六对弟子。
8月份,为了两个月后在齐齐哈尔召开的全国锦标赛队内进行了一次测验。“一个小小的测验,去了近200人看。其中很多人都是当初不赞成他俩搭伴的。”申杰告诉本刊记者。这次测验,一套节目,申雪摔了4跤。测验结束后,申杰说,他当时很不好意思地对姚滨说:“真对不起,孩子今天表现很差。”姚滨声音沙哑地回答:“没关系,这刚开始呢。”
对于这次全国锦标赛,申杰没有更高的奢望,只希望能比测验赛好一点。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申雪和赵宏博拿了冠军。回来的时候,姚滨很高兴,对申杰说:“我培养的学生4个月就拿全国冠军,这是头一对。”
赵宏博起初对申雪并不看好,是申雪的刻苦打动了他。他说:“最初就是兄妹,在冰场上一般都是我占主导地位。她很吃力地跟着我。”在带申雪、赵宏博一年后,姚滨门下又多了一对弟子,庞清和佟健。
作为我国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ISU(国际花样滑冰协会)裁判长,现年70多岁的杨家声见证了中国花样滑冰的整个发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他连续4年是男子单人滑全国冠军。“文革”前,杨家声考入哈尔滨医科大学,学医的时候一直没有放弃对花样滑冰的热爱,70年代成为花滑国家裁判,80年代成为国际裁判。按照国际滑联规定,担任国际裁判工作4年以上,有过3次工作经历,令国际滑联技术委员会满意者可以由所在国协会推荐考ISU裁判员。1985年,杨家声被推荐去英国伦敦考ISU裁判员。
杨家声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ISU裁判员考试分两部分,理论和实践。理论有50道题。总则、单人滑短节目、自由滑、双人滑短节目、自由滑5部分内容各占10分。总成绩达到84%,每部分准确率在60%以上算及格。然后是3天的实践考试,那边有比赛,6个人打分,之后大家讨论。为什么这么打,解释你评分的理由和根据。只有理论和实践都通过了,才能成为ISU裁判员。这次总共6人参加的考试,有1名英国裁判没有通过。
“裁判长分两级,国际裁判长和ISU裁判长,ISU裁判员同时可以做国际裁判长,工作6年获得国际滑联满意的才能申请晋升ISU裁判长。国际裁判长和ISU裁判长的权利是有区别的,前者只能主持参与一般的国际比赛裁判工作,后者可以在ISU系列的重大国际赛事(如世界青少年锦标赛、世界锦标赛、欧锦赛、四大洲锦标赛、国际滑联大奖赛总决赛、冬奥会)中担任裁判长。具体主持哪场比赛,由国际滑联邀请,而非国家任命。”1996年,在杨家声担任ISU裁判10年后,他成为我国第一个ISU裁判长。
“1980年中国第一次去美国的普莱西德河参加冬奥会,花样滑冰只参加了单人滑项目。赛前在日本训练了两个月,才明白了比什么内容,该怎么滑。也是同年,中国花样滑冰队又参加了在德国举行的世锦赛,那一次去了男单、女单和双人滑,双人滑去的是姚滨和栾波。我去观摩比赛,那时就发现,中国花样滑冰根本没入门,和国外选手比,完全是业余和专业的差距。滑完短节目,自由滑姚滨都不想上场了。那时,他就非常有想法,憋了一口气。”
杨家声说,按照竞技体育的规律,应该先参加一些小比赛,趟出一条路子来,再逐步参加更高级别的比赛,但是因为那时候,中国要争取重新加入国际奥委会组织,先从冬季项目开始努力,所以出国比赛政治意义远超出体育层面。
在那之后,相当长时间里中国花样滑冰没有再参加过世界比赛。1994年,申雪和赵宏博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这还是傲气的姚滨低头向领导勉强争取到的机会。“1986年第一届亚冬会上,中国在冰舞项目拿了冠军,所以领导曾误认为冰舞水平高,实际情况是日本一流的选手没有参加亚冬会。”杨家声说,在定下冰舞作为突破项目后,其他项目都被解散,姚滨带着队员回了哈尔滨。也就是那时候,陈露出现了。1991年,年仅12岁的她在世界青少年锦标赛上拿了女单第三。当时,国家给了陈露特殊政策,可以出国编排节目、比赛,但是因为经费有限,出国比赛教练都不能去。
在杨家声看来,当时的领导完全不了解花样滑冰的国际影响力。“花样滑冰在西方是一个关注度非常高的项目,国际滑联每年能获得很多赞助。在90年代参加国际滑联的比赛,运动员食宿由国际滑联支付,裁判员的所有经费国际滑联出,国家只需要支付运动员的路费。如果拿了前四名是有奖金的。此外,国际滑联每年结算后剩余的经费会发给参加世锦赛的所有运动员作为旅途补助,所以出国比赛不仅花不了什么钱,还可能赚钱。”杨家声说,像这次温哥华冬奥会,花样滑冰一票难求。400美元一张的票能涨到2000美元。
直到1996年第三届亚冬会,申雪、赵宏博拿了双人滑冠军,双人滑才开始受重视。还是1996年,在加拿大埃德蒙顿的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上申雪、赵宏博拿了第15名,当时中国代表队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法国花样滑冰协会主席伽吉亚却走过来跟杨家声握手表示祝贺,杨家声很奇怪,“拿第15有什么可祝贺的?”杨家声至今记得,伽吉亚当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过几年就是世界冠军了。”
类似的预言杨家声也听到过。“1991年,陈露参加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赛前训练时,当时的国际滑联技术委员会主席意大利人索尼娅·比安切蒂特意滑到我面前说,这小孩滑得太好了,将来肯定是世界冠军。她的话后来果然得到了验证。”杨家声说,由此可见,绝大部分专家和裁判都是公正的,只有当两个人特别接近时,裁判的印象才会至关重要。
姚滨和李明珠,都是杨家声心目中国内最优秀的花样滑冰教练。“一个优秀的教练员要有敏感思维和创新思维,出去比赛对于新的东西要有感觉,容易被小事触动,激发出创新思维,而不只是看看热闹,回来做流水账一样的汇报。”
杨家声说,他做ISU裁判的时候,李明珠有个习惯,每次打分讨论结束后都要和他聊天。“作为裁判,我们打分后的讨论会评价前三名的选手,好在哪,差在哪。尤其是当冠亚军实力接近需要投票决定归属时,大家都会说出自己的理由,争得面红耳赤。当时有个美国裁判很喜欢陈露,但是他指出,陈露的技术动作好,尤其是跳跃能力很强,裁判们都爱叫她‘跳跃的豆子’,可是她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不像美国的优秀选手成熟,对音乐理解透彻,表演有内涵。我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李明珠后,她当时就跟国家提要求,技术的问题我能解决,但是编排和表演不是我擅长的,所以后来陈露被送去国外编排,学表演。”同样的,杨家声认为,姚滨的技术动作指导科学,这是建立在多年积淀基础之上的。
“姚滨在运动员时期没有见识过世界,当他看到世界是什么样时,他退役了。1980年在德国多特蒙德,他怯场,双人滑倒数第一。2004年3月,还是德国多特蒙德,中国双人滑获得第二和第三。现在的很多高难度动作,在姚滨刚执教的时候根本不会做。”杨家声告诉本刊记者,“申雪和赵宏博拉手的时候,没有机会送出国。舞蹈编排、音乐选曲、服装设计都是姚滨一手包办。因此大家评价他多才多艺,但我认为这不足以反映他的能力。他的聪明才智表现在,在某一个动作,某一个技术上他能一步步拉到世界顶峰。中国双人滑在捻转、抛跳、托举姿态这些环节创造了新的东西,引领了某些动作上的世界发展趋势。比如捻转,以前女伴的姿态是与冰面垂直的,中国队女伴则是倾斜的,与冰面有一定的角度。这曾被一些国家的裁判否定,但是后来被国际公认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因为技术上是合理的,更有利于女伴落冰。再比如托举,传统做法是男伴扶着女伴身体侧面,女伴脸朝下,而中国队是扶胯托举,女伴脸朝上。一个小小的改动,却能让裁判眼前一亮。要知道,裁判喜欢看新面孔,新动作。”
屡败屡战
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这是申雪、赵宏博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短节目《流浪者之歌》有些紧张,排在第八。自由滑完成却比前一年的世锦赛上更为成熟,最终获得第五名,创造了中国双人滑选手在奥运会的最好名次。回忆起这届奥运会,赵宏博的感觉就是三个字:“很快乐。”他告诉本刊记者:“没有夺牌压力,只是想在与世锦赛气氛截然不同的奥运会上尽可能展示自我。”
这个时候的申、赵,实力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在冬奥会之前的大奖赛上拿到过第四。分析与对手的差距,赵宏博说:“动作质量与前三名没什么差别,有的甚至做得更好。输就输在艺术表现力和印象分上。”
陈露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就曾比较过国内花样滑冰训练和国外的差别:“国内的教育都是强制性的,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在国外是启发式的,国外的教练会给你很大的空间,启发你的想象力。我后来一直在国外做编排,每年都会去加拿大跟我的加拿大教练编排,他不会说我们选好了音乐,他教你怎么滑,他说,好吧,你滑,你自己想怎么滑怎么滑,你想做什么你做什么,你想怎么舞蹈怎么舞蹈。他会用你自己的东西,‘我喜欢这个,那个东西很有感觉’,最后完全用的是你自己的东西,发挥你自己的想象力,然后再精雕细琢一下,这样既锻炼了自己的能力,也发挥了自己本身特有的气质,不会是感觉别人教给你的东西,而是你在表演你自己的故事。我们小的时候,都是一个教练,一直倡导先练难度技术,回头再突出表现力,那也顶多是舞蹈老师帮着弄一弄。可是花样滑冰的要求太多了,有跳跃、有旋转、有步伐,要求的东西特别多,一个教练不可能面面俱到。”
曾被誉为领导世界双人滑潮流先锋的俄罗斯著名双人滑教练塔玛拉(Tamara Moskvina)也是在这个时候注意到申雪和赵宏博的。对于这个时期的申、赵,塔玛拉对本刊记者直言,“缺乏一些艺术表现力”。
2001年,申、赵参加了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世界锦标赛,赵宏博告诉本刊记者:“那次滑得特别好,难度比其他男的都高,最后还是输在艺术表现力上。”赵宏博说,比赛结束后,姚滨带着他和申雪找到其中一位俄罗斯老裁判长,他也是国际有名的教练员,赵宏博问他:“中国运动员怎么样才能再提高?”这位裁判长回答:“你们难度很好,艺术表现力不够。”他给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是继续提高难度,至少要比别人高出明显一截来;二是在现有难度基础上突出表演”。
世锦赛回来,申、赵就开始练习“抛后内接环四周”。这段时期的魔鬼训练让赵宏博至今回忆起来都认为“惨不忍睹”。“摔得申雪感觉五脏六腑都移了位,宏博都不忍心再抛。”申杰说,也是从那时开始,赵宏博对申雪有了敬重感,因为她为了事业舍得付出。为了在艺术表现力上有所突破,姚滨请来了美国的米勒(Miller)和两个副编导为申雪、赵宏博共同编排《图兰朵》。
赵宏博说,无论是情感表达和动作设计,编排都很有主题。但是姚滨还是不满意。最后还是陈维亚为这套节目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他告诉我们,每一段音乐在表达什么。这其实是在讲一个落魄的王子如何用爱情征服图兰朵公主的,把这个故事贯穿在舞剧中来编排。有了故事内涵,我们感觉能更好地去表现。”
2001年的世锦赛中国花滑队还得到了很多其他的反馈意见:“这是个打分项目,以前我们只觉得是竞技体育项目,经过分析才知道整体实力很重要。包括服装设计、编排、化妆,必须提升品牌。另外国家实力也很重要,裁判员、技术官员中更多的是西方人,俄罗斯人,中国只有一个ISU裁判长,完全比不了。所以如果只是技术好,金牌还是不会给你。”
先后参加过5次冬奥会裁判工作的杨家声对此有亲身感受。国际滑联是这样选择裁判的,有运动员参加比赛的国家都可以出一个裁判员,如果人数过多,则再抽签决定。1992年在法国阿尔贝维尔举行的冬奥会,杨家声作为女子单人滑裁判员第一次执法奥运会。那次裁判长是美国白人,对拿过欧锦赛冠军的法国黑人姑娘鲍娜丽很是看不上,一开始就提出:“她做的那是什么舞蹈动作?”认为分打高了。招致法国裁判不满,两人都快打起来。最后法国裁判向国际滑联控告这位美国白人裁判种族歧视,后者受到严重警告。
1998年长野冬奥会,杨家声是10个双人滑裁判员中的一个。在当时,俄罗斯、美国和加拿大还是第一梯队。裁判们对初次亮相冬奥会的申雪、赵宏博没有太多评论,只是说,“不错”。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赵宏博拼得很累。“冬运中心想从双人滑项目获得花样滑冰的突破,而我们也具备了争夺奖牌的实力。当时为了做不做抛四周领导特意开会讨论,做了,成了,有争冠军的希望,不成那就是第三,如果再有失误,可能第三都拿不到。”
没有退路的他们在上场前最后一刻决定使用抛四周。申雪落冰重心虽然有点低,可所有人都以为她成功了,申雪也以为自己成功了,急于做下一个动作的她紧接着却摔倒了。最终两人仅收获一枚铜牌,
这次冬奥会杨家声继续担任双人滑裁判员。杨家声说:“裁判讨论的重点在俄罗斯和加拿大的冠亚军之争。当时投票是5比4,加拿大不满意,打架打到国际法庭上去了,最后那届奥运会没有亚军,给俄罗斯和加拿大都发了金牌。申雪、赵宏博是没有疑义的第三,他们当时实力确实差一些,即使滑得很好,赢的可能性也不大。出发前代表团就讨论过,定的指标就是保三争二或一。”
《图兰朵》带给申雪和赵宏博的是远比铜牌更重要的艺术表现力的提升。“为什么有的人滑行像在跑,有的人就滑得很优美流畅?因为膝盖柔软度的使用不同。一个节目如果有了主题,有了灵魂,就不苍白。当我们了解了故事的背景,在表演时加入情感细腻的东西,就能更好地表现音乐。”赵宏博说。
2006年都灵冬奥会,是申、赵离金牌最近的一次。“在那之前整个赛季,我们就没输给过俄罗斯的托米安尼娜和马列宁组合。《胡桃夹子》、《宋氏王朝》、《沉思》,我们一次比一次滑得出色。但是也就是在状态最好的时候,我的跟腱断了。”赵宏博说,“离金牌很近,却一点机会也没有,这是最悲惨的一届奥运会。”
申杰记得,那天15点在昆明出了问题,20点,他就接到了申雪的电话。他告诉本刊记者,赵宏博跟腱做手术的时候,申雪也发烧了,但是她坚持每天去医院陪赵宏博,3张椅子一拼,她就躺在上面跟赵宏博聊天,给他讲笑话。这让申杰想起2003年华盛顿世锦赛时两人的经历:“赛前训练,小雪把脚给崴了。当时赵宏博一直在鼓励安慰她,她打了5针麻药参加短节目比赛。结果短节目结束后,她韧带拉伤了。在自由滑赛前又打了3针麻药。回来后她跟我们说,当时膝盖以下都没感觉。完全是凭着习惯在滑,在落冰。”
赵宏博说,和申雪的感情从那段时间之后更牢固,“最开始是兄妹、朋友,到了2005年,我就决定选择她作为我相伴一生的人。所有的比赛,成功也好,痛苦也罢,都必须是我们两个人去面对”。凭着“一定要站到奥运赛场上”的精神,赵宏博挺了过来,“但是拿金牌已经不现实,只能尽量去发挥了”。
塔玛拉对申、赵评价很高:“从他们排练的节目看,我发现他们的教练仔细研究了俄罗斯最优秀教练的节目编排,并很好地消化吸收。我们一直很喜欢这对组合,而且认为他们有很强的实力。”
强势回归
在很多人看来,都灵冬奥会将是申雪、赵宏博的谢幕演出。当他们回国后,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是否退役?”
赵宏博说,确实觉得很累,很辛苦,对铜牌的成绩也不满意。所以,选择了在2007年再滑了一个赛季。“都灵冬奥会不是我们真实能力和状态的反映,2007年的比赛,我们不为国家,不为其他人,就是为了证明自己。”
这是一个大满贯的赛季,从第一站开始申雪、赵宏博连续拿了6个世界冠军。赵宏博选择在最后一站比赛结束后公开他和申雪的关系:在冰场上向申雪求婚。这之前,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她妈妈当时看了还奇怪,怎么有这么个结束动作呢?后来朋友给我挂电话,问我是不是有特殊情况?我说,没什么,很正常,要退役了,就是情感的自然释放。转头姚滨给我打电话了,听到我也不了解情况,姚滨乐了,说他也不知道。”
这之后,申雪和赵宏博选择了暂时的离开。“我觉得需要调整心态。这时候,年龄是最大的对手。能否像20岁左右的小伙子那样再坚持4年?我觉得不太可能。和申雪商量之后,我们决定调整两年,好好享受一下生活。”赵宏博告诉本刊记者,在国内,他们和深圳世界之窗签订了3年合约,经营一家面向社会的商业性的滑冰俱乐部,对方出资,他们出教练,两人只是偶尔会去做些指导。更多的时间,他们则是在履行一单“国际生意”。他们参加了代表世界最高水准的世界星演出团,每年在全世界巡回表演60~70场,不仅收入不菲,还让二人补过了一段漫长甜蜜的蜜月旅游。
事实上,对于2009年的回归,申雪、赵宏博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复出前,他们特意寻访到了劳瑞。“我接到来自中国的电邮,问我对他们参加今年冬奥会的看法,我欣然说,去吧!他们便托我编舞。我只身飞往北京,为申、赵微调舞步,回到加国后也保持电邮联系,鼓励两人。”劳瑞告诉本刊记者,“我为选手编舞,先别管跳跃或旋转。从音乐开始,在溜冰场一角划一块小的地方,先要他们任意随音乐起舞,我要看他们怎样与音乐配合,留意身体的动作及节奏感,特别是脚部如何接触冰面,整体的感觉如何等等。因为一个项目仅有数分钟,每一个细节都要很着重,手怎样摆放,眼神是凌厉还是迷人,这些都要考虑周到。至于音乐的选择,我反而很少自滑冰获取灵感,多看现代舞及芭蕾保持新鲜感,再配合选手的节奏感及喜好决定。”
劳瑞笑言,申、赵两人的训练过程充满温情和可爱:“赵宏博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子,但对着申雪,他简直是一个充满爱的大熊。每次凝望她的眼神都让我融掉了,两人练习时很认真,但又很爱笑,经常互相取笑对方,场面很温馨。”劳瑞认为,申、赵与关颖珊及陈伟群等一样,有着中国滑冰选手的特质,训练刻苦勤奋,而且很尊重教练的意见。
劳瑞告诉本刊记者:“赵宏博有很多主意,会在冰上不停尝试(新动作),申雪就会站着观察,研究赵宏博的动作是否可行,又会问我意见,听我指示等。她某种程度上有点固执,感到某个舞步能投入的话,就很想跳出来,但我需要顾及舞步与整个曲目的配合,有时也要多番劝说她修改或直接弃用。不过她的固执是好事,即使当下做不到,她都会坚持练习直到做好为止。”
2010年冬奥会使用的是新的裁判打分系统。“以前是6.0分制,整个技术动作打一个分,艺术表现力一个分,两分相加排名次,最高有12个裁判打分。现在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打分,比赛完后,裁判组会对两个比赛分讨论,对于打分异常的情况进行分析。如果裁判员不能给出合理解释,就要受到严格的处罚。最严重的错误是国家偏见,六级惩罚系统里最严厉的处罚是除名。”杨家声告诉本刊记者,本届冬奥会双人滑有13个国家的运动员参加,从中抽取9个国家的裁判员担任裁判;自由滑阶段,从第一组的9个裁判中抽取5人,再加上另外4个裁判形成新的裁判组。我们男单没有获得参赛资格,女单和冰舞都没抽上,只在双人滑短节目抽中一个中国裁判。对于节目内容,裁判主要从5个方面进行评判:滑行技术、动作联结、表演与动作的完成、艺术编排(各种动作的比例)、音乐风格特点的表达。“新裁判系统对技术动作量化,质化,评分更准确合理,很少出现偏见。而且现在重大比赛时,不会显示每一个裁判的打分,只有总的分数,这在保护裁判员的同时,也解除了他们的思想负担,这让他们心理平衡,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裁判。”
劳瑞也比较赞同新的评分系统:“在现有计分制度下,每一个动作都能详细解构,怎样出脚,旋转次数是否足够,落地质量如何,都有很详细的计分,逐项评分较以往只有一个项目总分公平得多。”
“现在编舞要编得精明,要针对重点去编。某种程度上是限制了创作自由,但好处是就算一个动作做得不完美,又或在落地时跌了一跤,都不会代表世界完结。以前选手跌了可能没有心情继续下去,现在的制度是鼓励他们坚持到底。”不过,劳瑞坦言,现在的制度太侧重旋转,对选手其实不太健康,她表示俄国冬奥银牌得主普鲁申科(Plushenko)认为美国金牌选手莱萨切克没有在项目中做到转体四周,因而不配夺金正是这种偏执。她觉得评分除了技术难度外,亦应照顾整体美感、完整性及流畅度,更要着重选手的健康安全,并非单以一个周转组合定胜。
“我经常问为何一个环节中有3组周转动作仍然不够,近45秒的时间已足够裁判去定夺该选手的能力。像申、赵两人曾经受伤,要求他们在整个环节中不断做旋转是一个挑战。老实说,在冰面或空中旋转动作中,女子的背部及男子、女子的臀部均很容易受伤,如何保障他们出赛时健康亦是很重要的因素。”劳瑞告诉本刊记者。
当劳瑞为申、赵两人编舞时,就特别着重跳跃及旋转之间的“休息时间”。“让他们休息并不代表什么都不做,而是透过步法的配搭,让他们在一个高难度的三周跳后可以稍微回一回气,想清楚下一个高难度的得分动作怎样处理。两人年纪较大,这样的设计对他们亦有利。”
现在再谈到艺术表现力,赵宏博的理解又有不同:“以前就是在模仿,在演。在做表现爱情故事的训练时,两人一对眼神,总是要笑场。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是在用心去领悟,是希望真正滑到对方的灵魂中去。”就连申杰也很有感触:“他们在首体训练时我去看过一次,即使是训练,他们也都是融入感情地去滑,真的是在享受这项运动。”
“我编舞最重要是跳的人开心,看的人也开心。一个自由环节虽然只有4分40秒,但我就想用那短短的时间打动观众,像申雪及赵宏博的表现,他们在冰上的爱意、姿势及技术打动了我,令我为他们的演绎感动落泪。但这样怎么做出来呢?当然要不断地练习,他们如果不是放松,能够完全操控及信任自己和搭档的身体,那些动作根本做不出来。要他们完全掌握,并在奥运会这种很高压的环境表现出来,是很困难的事——我为他们的表现感到自豪。”劳瑞说。■(文 / 李翊 吴丽玮) 故事花样滑冰鲜为人知中国金牌弟子世锦赛姚滨赵宏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