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我不是机会主义者
作者:马戎戎(文 / 马戎戎)
 ( 电影《三枪拍案惊奇》海报 )
( 电影《三枪拍案惊奇》海报 )
三联生活周刊:回头再看《活着》,你怎么看待这部作品?
张艺谋:我认为《活着》实际上是拍得很好的。“文革”是我的成长期,它当然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阶段。以后有机会的话,如果制度宽松了,还想尝试这个题材。大时代和动荡的时代是容易出故事,出人物的。《活着》的方式没问题。而且现在看来还可以更凝重一些。我至今认为方法是对的,但也可以说能够拍得更好。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这个年纪,再来看悲剧,你会觉得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是外部的时代环境还是人的性格?人能逃脱悲剧的命运么?
张艺谋:这已经成了哲学的大问题了。实际上,有人说,人生一世就是来受罪的,所有的宗教都相信人是来赎罪的。人类大概在地球上就是个悲剧。我们人类的贪欲让我们短短地造了一两万年,这星球如今已然就成这样子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宗教感兴趣么?
 ( 电影《三枪拍案惊奇》剧照
)
( 电影《三枪拍案惊奇》剧照
)
张艺谋:我不懂,我不迷信。我们这一代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一代,我们这一代基本上不信佛不信教,我们是俗称的“唯物主义”的信仰,所以我至今是啥都不信,也不迷信。但是我尊重。
三联生活周刊:你承认人有时候是无力的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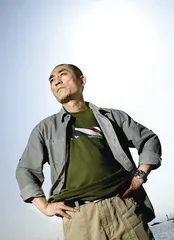 ( 张艺谋 )
( 张艺谋 )
张艺谋:个人当然是无力的。《三枪拍案惊奇》(以下简称《三枪》)恰好回答了这个问题:人是命运带来的,所有人都在犯错误,最缜密的如孙红雷这样的杀手其实也在犯着最简单的错误,可是在他的位置来看这个错误是非犯不可的,因为只有这么一条思考道路。
这是个人命运的无力和荒诞,人可能就是这样子。你知道你只能做一个记者?不知道吧?我知道我只能做一个导演?也不知道。不知道,那么很多东西我们就不能选择,我们不能选择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最终做了什么没做什么,从世俗的角度来考虑,成功或不成功也都不知道,不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三枪》的结尾,不是一个救赎的结尾,而是一个消解的结尾。那么在你看来:面对这种无力和命运的捉弄,最终能够让人解脱的是什么?
张艺谋:解脱不了。所以《三枪》最后没有给答案。喜闹剧只是一个包装,但实际上我自己认为还是在讨论一个挺严肃的命题。科恩兄弟的原作,我很喜欢。他们一贯的命题都是给人一种冷峻和疏离的关系,我自己在这里只是做了一个中国式的包装,我用了京剧“三岔口”的方式,强化了你上我下、你进我出走马灯似的戏剧结构,强化了误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误会,我强化这个的目的,可能就是我想说的,所谓有文化的一句话,“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和荒诞”。人,不能做你自己。
三联生活周刊:在很多人看来,你已经是为数不多能够主宰自己命运,而且比一般人有更多选择和自由的人了,你也这样认为么?
张艺谋:我要说我不是这样子,别人都不信,连我都不信。不能这么比,我们说的是一个抽象的问题,而还原到我身上就变成了世俗的具象判断。这是两个问题。宽泛地来讲,不同位置的人要面临的困惑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生命的困惑。
三联生活周刊:你眼前最具象的困惑是什么?
张艺谋:很简单,最功利的——我至今就没碰上一个让我舒服的剧本。每一个电影我都要把2/3的精力用在编剧上,我又不是个一流的编剧。我苦恼死了。我是一个职业导演,我的长项是用画面讲故事,我多么期盼能有一个好剧本,我拿来以后基本不修改我就拍,太舒服了。我就这个愿望至今不能满足。
三联生活周刊:《血迷宫》最触动你的一点在哪里?
张艺谋:命运的隐喻。作为处女作,故事并不是特别流畅。但在当年,这里投注了导演的一种力量和感觉。我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看了这个电影,25年来就再也没看过第二遍,可没靠翻译就记住了。一直到我要重拍它,我才拿来看。
好的作品就是这种独特性,杀人放火的动作片很多,但有独特性的并不多。
三联生活周刊:你以前电影形式感很强,色彩也很饱满,但这一次这么大红大绿地用下来,非常戏剧性,非常艳俗。这种夸张是你故意追求的么?
张艺谋:过去唱戏,色彩总属于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包括宫廷的色彩都很显眼,但是一到客栈、老百姓那儿就灰色、褐色,老百姓演的群众演员都是灰突突的一片,稍微有点颜色就是有钱人。
这次我们拍的是面馆、客栈,就是小老百姓,要是不用我现在这种颜色,而是回到古装片的颜色里去了,那闭上眼睛一想,全是灰色、黑色,就像横店满街跑的群众演员一样,有啥意思。所以我想,算了,咱们就放大吧,让他们穿最花的。
对于颜色,我是个人爱好,我不能因为一批评就没了个人爱好,再说也没一个真理,就好像我爱吃辣的,但您愣批评我,弄得我最后不吃辣的了,那我就没意思了。所以,对色彩的追求纯粹是我个人爱好,它不决定我的美学高低。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美学没标准,是么?
张艺谋:个人爱好,纯粹是个人爱好。我觉得在电影上,颜色鲜艳就好看。同时,我觉得颜色是视觉上的快感,除非我拍黑白电影,那是我要讲一个故事,让它冷灰调子,一路黑糊糊到底。但是你想《三枪》,固然有一个挺人文的主题,可第一我是贺岁档,第二我用小沈阳,我干吗要把人弄得灰头土脸的?还有一个,我觉得喜闹的包装,反而可以衬托另外的主题,因为本来的主题是很严肃的,科恩的主题和喜闹毫无关系。我自己想科恩要是看喜闹的开头,一定会觉得“这家伙怎么把我的电影弄得这么闹”。
三联生活周刊:《十面埋伏》的时候,当时我们的记者采访你,你说你的电影就是随大流,然后我们记者说,这个时代的大流是“快男”、“超女”,你会随着这个大流么?你当时就说,没准。看完《三枪》,再想想当时的对话,我觉得很有趣。
张艺谋:对,我们马上就顺应了流行元素。如果有博物馆文化和流行文化之分,电影是流行文化,电影不是让人供在那儿、敬在那儿膜拜的。对于广大的受众来说,一次演完就过去了。基本属于时令性的,季节性的。电影只有100年的历史,电影的传播渠道、流行元素,所有的一切,基本上是捆在流行文化上的,为什么要把它搞成博物馆文化呢?既然这个时代流行“快男”、“超女”,流行小沈阳,这些元素,你能用你就用吧。但这不是说你为用流行元素来做故事,那就本末倒置了,那就不行。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觉得你现在和拍《红高粱》的时候有什么变化?
张艺谋:我成熟了许多,沉稳了许多,但我自己有种东西没有变。比如某种张扬,某种对色彩的极致性的追求是没有变的,那也是个人爱好。我个性里某种强烈的东西没有变,只是再也没有碰到《红高粱》那一类形式的东西了,但要是有,我还愿意拍,就像《水浒》一样,张扬热烈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时代和上世纪90年代相比,你更喜欢哪个时代?
张艺谋:不一样。我们不能说这个时代好像在退步,我们不应该那么恋旧,不应该好像只是看到某种不满。整个80年代是一个可爱的年代,那个时代是全民在思考,所以才有那么多优秀的小说,提供了资源,所以我们才有了“第五代”,好像多么了不起。其实那都是时代造就的,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90年代,包括2000年以后,新的一代成长,步入商品经济的时代,跟国际开始接轨,这个时代给我们很多人新的命题,包括价值观发生改变,我们有新的多元化的思考。而今天这个时代,2000年以后的时代,或者奥运后的时代,真的很难有一个说法。就像互联网一样,无数个嘴在说,这就是多元化,不可抗拒。
三联生活周刊:意识到商品时代到来的时候,你自己心里没有任何的抗拒,或者心理转化的过程么?
张艺谋:我其实是在“第五代”中被误会的一个人。我们对“第五代”的印象是思考的一代,但我其实是个另类。我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是《红高粱》,那是充满了娱乐精神的电影,唱了三首歌,跳了两段舞。后来我拍《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十面埋伏》,还要拍动作电影,我根本不抗拒它。有时候我拿了一堆碟回来,也经常先看商业片,把文艺片搁到最后,还看是不是话题,有时候看到一半看不动了,就关了。
其实“苦大仇深”的作品,我也做得很好啊:我们不是天才,是时代影响我们。如果没有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没有那个时代全民的反思,我们第五代算个什么呀,啥也不懂。所以实际上是时代给了我们源泉、土地土壤,我们只是顺应时代做了一些事情,何况还借助文学作品的强大,所以我一点都不高估自己,我做的东西都是在时代中做的,都是借助时代的力量做的,我没要显示自己有多高深和伟大。
但是到了娱乐时代、娱乐精神,我也不是装的。经常有人也说“张艺谋不争气,堕落了”,那是因为他们以前把我看高了,我不是堕落,我天生就有这个——你看看这个人的以往表现,发现他的狼子野心都在那儿露着呢。别人要按照自己的想象打扮你,认为你要这样那样,可能是寄托了他的想象。实际上,我这个人正邪之间吧,雅俗之间吧。自然我不具备那么高的原创性。你要是给我一个特别雅的小说,但特别具有力量,我也能拍得像模像样,一不留神就成了塔可夫斯基;但你要是给我一个挺棒的商业题材,我也能拍得很不错。对我自己来说,我没有那么高看自己,我其实是一个从老百姓当中长出来的人,也没有那种世家子弟的优越感。我认为电影不是哲学思考或者参与哲学思考的形式,电影就是可以承载很多东西的游戏,一个幻觉,一个梦。你真的不要把它端那么高,你要是端那么高,你学哲学,学思想,学社会学,你写诗都可以,这些东西深。但电影真不深。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自己是个机会主义者么?
张艺谋:机会主义者,在我们的语境里是个贬义词,我当然不承认。所谓机会主义者,我是这么看的,他去主动地索取和利用这些机会,他孜孜不倦地去抓和寻找机会。在这个概念里,我完全不是,我至今都很被动。
还有一种机会主义者,他甚至以损害别人的渠道来索取机会,那也是机会主义者,这一点我就更不可能做,我就从来没有故意伤害过任何人。
三联生活周刊:怎样看待张伟平给你的帮助。
张艺谋:我种萝卜,他卖萝卜。他卖得特别好,而我自己很不会卖萝卜。我拍啥电影,他都觉得好。他对我带着感情色彩,这样子的搭档才可以没有太多的利益关系,所以我就很乐意把萝卜交给他卖。
三联生活周刊:做了那么多艺术门类之后,电影是不是还是你最想做的形式?你拍电影想拍到多少岁?
张艺谋:拍电影是我最喜欢的形式,电影仍然是我的最爱,而且我还坚定地认为,我在这些东西上的成功,都是电影的成功,因为电影是综合艺术。
拍到什么时候?拍到老呗,拍到拍不动。进电影院的都是年轻观众,当年轻观众不喜欢看你电影的时候,你也就大可不必再拍了,你就回去过你的日子。
导演到了75岁以后,你真的要看看人家真的是喜欢你的电影么?我看国际上的大导演,到了80多岁还在拍,我觉得是大家哄他玩呢,他的“粉丝”、学生拿钱给他,其实已经不太看得懂他要拍什么了。
三联生活周刊:列一下你最喜欢的三个导演?
张艺谋:黑泽明,塔可夫斯基,斯皮尔伯格。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价值。■ 张艺谋不是活着三枪拍案惊奇红高粱电影三联生活周刊机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