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作者:薛巍
( 齐泽克不仅是哲学家,还是精神分析家和影评人,他在纪录片《变态者电影指南》中评论了40多部经典电影 )
金融危机的发生并非意外
齐泽克新著的书名引用的是马克思的话——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开头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齐泽克所说的悲剧和笑剧分别是标志着21世纪头10年的开头和结尾的两件大事:2001年的“9·11”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以笑剧的面目的重演可能比悲剧更可怕。
“9·11”和金融危机为什么是同一场世界历史事变,它们有何共同之处?齐泽克首先指出,布什总统在两次事件之后对美国民众的讲话非常类似,就像同一个演说的两个版本。两次布什都说到美国生活方式面临的威胁,以及迅速、坚决地应对这一危险的需要。两次他都号召为了拯救同样的价值观而中止美国人的价值观(保证个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其次,它们都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特征。马克思曾经说,德国旧政权只是想象它仍然相信自己,在同一时期,克尔凯郭尔发展出他的这一思想:我们人类从来都无法确定我们相信,最终我们只是相信我们相信。“只是想象它相信自己”表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能够发挥社会纽带的作用。今天的自由民主也只是想象他们仍相信自己的意识形态,虽然只是想象,他们仍继续实行着其意识形态。本雅明预见到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如何相信它的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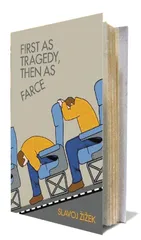 ( 齐泽克的新著《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笑剧》 )
( 齐泽克的新著《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笑剧》 )
齐泽克喜欢用故事做类比,在这个论题上,他最喜欢的一则轶事是:一位科学家去物理学家玻尔在乡下的房子参观,惊讶地发现他的大门上挂着一块马蹄铁,在欧洲迷信的人认为它能够阻挡恶鬼。这位科学家问:“你真的相信这个吗?”玻尔回答说:“当然不信,我不是一个白痴,我是一个科学家。”那位朋友又问:“那你为什么挂这个?”玻尔回答说:“我不信,但人家告诉我即使你不信,它也会起作用。”
齐泽克说,意识形态今天就是这样运作的:没人把民主或公正当真,我们都清楚它们腐败的本质,但我们参与其中,表现出我们对它们的信仰,因为我们假定我们即使不相信它们,它们也能起作用。我们取消民主,但行动时又假定它有效。这是一种奇怪的情况,因为年纪大一点的人还记得,过去权力的公共形象是尊严、信念,私下里人们取笑它。现在,权力的公共形象变得越来越公开地粗鄙、下流。在贝卢斯科尼性丑闻质询中,他的律师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说声称贝卢斯科尼性无能的人是说谎,贝卢斯科尼准备在法庭上证实这是谎言。怎样证实?他这话什么意思?“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愤世嫉俗的时代,他们不仅是不把自己当回事,而且拿自己开玩笑。好像即使你取笑它,这个制度仍然能够运行。”
“当代一直被认为是后意识形态时期,但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否认只不过证明我们比之前更加置身于意识形态之中。意识形态一直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包括争夺过去的传统的斗争。自由和民主都是下层阶级在19世纪和20世纪通过长期的、艰难的斗争赢得的,它们绝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然结果。”
1990年,福山宣布历史终结、自由民主的信念获胜,“9·11”的发生象征着克林顿时期的终结。齐泽克说:“好像福山90年代的乌托邦要死两次,因为‘9·11’时自由民主的政治乌托邦没有影响到全球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乌托邦。2008年金融危机的历史意义是,它标志着福山的梦想经济的一面的终结。”
齐泽克说:“2008年金融危机唯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很容易就以为它的发生是无法预测的。”其实之前很多人表示了对发生金融危机的担心:新千年的第一个10年里,每一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会时,抗议者抗议的不仅有通常的反全球化主题(对第三世界的剥削等等),还有银行如何以虚拟的钱制造了增长的幻象,这种做法将如何以失败告终。保罗·克罗格曼和斯蒂格利茨这样的经济学家曾发出过警告,指出那些许诺持续增长的人不知道眼下在发生什么。2004年,在华盛顿,很多人就金融危机的危险举行游行,警方被迫增派了8000名地方警员,后又从马里兰和弗吉尼亚调来6000人。他们使用了催泪瓦斯、棍棒,逮捕了很多人——多到警察要用公共汽车运送。
齐泽克一直支持奥巴马:“奥巴马正在打的医保战争非常重要,因为它跟统治意识形态的核心有关。”反对奥巴马运动的核心是自由选择。但如果他获胜,教训是自由选择很美好,但是只有在深厚的管制、道德假定和经济条件下才可行。对于医保的选择自由是可以放弃的自由,就像供水和供电。你可以说你没有选择供水商的自由,是你的居住地强加给你的。但是人们乐于失去这一自由,一些基本的选择宁可由社会来做,像供电和供水、医保,这样开启了在别的方面的选择自由。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说:“今天我们被迫好像我们是自由的一样地活着。”我们一直受到自由的轰炸,你被迫去做选择,哪怕没有选择的背景条件。
对金融危机的反应
金融危机发生后,没人知道该怎么办,这是因为期望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市场如何反应不仅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干预,更取决于他们认为别人对他们有多大的信任。凯恩斯精彩地解释过这种情况,他把股市比做一场愚蠢的竞赛,参赛者要从100张照片中选出几个漂亮姑娘,胜者将是那个选择的姑娘最接近一般意见的人。“不是要选择你认为最漂亮的,甚至也不是一般认为最漂亮的。我们琢磨的是一般人以为一般人会选择什么。”凯恩斯说。
“别光说,行动起来”的老话现在不太合适,“也许,不久前我们做了太多,像干预自然、破坏环境等等。也许该回撤一步,思考和表达正确的东西了。确实,我们经常只说不做,但有时我们做是为了避免说和思考。比如,对金融危机这一问题抛出7000亿美元,而不是思考它起初是怎么引发的”。
齐泽克在书中说:“这场金融危机主要的受害者可能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西方‘左派’,至今它没能给出一个可行的全球性选择。”西方“左派”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它变得越来越道德化,一种抗议非正义的纯粹形式,唯一能做的是道德论坛。在这种意义上,很多前“左派”变得非政治化,他们不再追问真正的基本问题。就像现在,所有高声叫喊的是那些奸商银行家,但当前危机的根源不只是贪婪。在泡沫之后,人们想的是如何保持繁荣,保持经济的活跃。现在只有一点点真正超党派的决定:让房地产业更容易一些,使它继续发展。在银行家的贪婪这一心理学问题之下有一个结构性问题——资本主义如何运行的问题。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麦道夫身上,他只是这个制度如何逼迫人的激进版本,不要通过把它归结为心理问题而化解这个问题。邪恶的人还要有特定的制度、经济、协作、背景允许他干他所干的事。
西方“左派”的第二个问题是提出要“帮助百姓街而不是华尔街”,但是那些银行经理会强调说,在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华尔街就没有百姓街。因为在今天的经济中,由于竞争和对新发明的巨大投资,贷不到钱,就没有百姓街的繁荣。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应该避免迅速地道德化。
齐泽克认为,仍要尽可能积极地与资本主义斗争。“汉娜·阿伦特认为经济不是真理的空间。在她看来,经济只是功利的东西,真正重大的政治不会发生在那儿。但是我们需要马克思所说的政治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