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宾的“亲密的第三重人生”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苌苌)
 ( 科尔姆·托宾与他的作品《大师》(中文版) )
( 科尔姆·托宾与他的作品《大师》(中文版) )
生于1955年的科尔姆·托宾(Colm Tóibín),是爱尔兰当代重要作家。1985年后,从记者转为职业作家,他发表了5部长篇小说及十几篇短篇小说。托宾写作题材多样,线索涉及爱尔兰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他又生活在海外,如以他早年在巴塞罗那生活为蓝本的《南方》,以及他最新的小说《布鲁克林》,后者是他从女性的视角,写一个独自在布鲁克林生活的爱尔兰女孩的爱与失去,以及她对个人身份的认定。托宾在中国目前唯一一部翻译出版的《大师》,也是他获奖最多的一部长篇小说,以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为主角,截取了他生活中重要的几个节点,写他避居爱尔兰,结识当地名流的那个阶段,以他知识分子的视角对当地生活的讽刺和看法,其中揉进了很多托宾自己的体验,同样也是表现亨利·詹姆斯的爱与失去。“爱与失去”是托宾一贯的创作母题,他像很多一流作家一样,趣味广泛而高产,成为作家后,他没有完全放弃记者的职责,经常有戏剧评论和文学评论文章见诸于报刊。
托宾在上海复旦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做的两场讲座的主题都是关于文学和生活。他说,尽管很多文学作品是虚构的,但总有一部分来自你对生活的观察。比如亨利·詹姆斯在《贵妇的肖像》中,曾经把他祖母的家复制到小说中,或者把佛罗伦萨朋友的房子复制进小说里。托宾也讲到,在他自己的《布鲁克林》中,着力挖掘的不是他对这个地方的生活经验,而是自己的感觉经验,比如晕船的感觉和思乡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很难虚构的。在一本小说中,如何以这些真实的细节跟想象的情节联系和转换,这是托宾要告诉中国的文学爱好者的。
三联生活周刊:从爱尔兰最著名的作家乔伊斯身上,你师承了什么?
托宾:乔伊斯让我学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人的意识和时间的把握。在《都柏林人》的最后一个故事中,他开始有这种尝试,到了《尤利西斯》就比较明显。乔伊斯笔下的人物布鲁姆对环境的反应,好像他是活在你头脑里的一个人。在这本书之前的小说,人物很明显是虚构的,思想太整齐,太有逻辑性,但在布鲁姆身上,头一次让人感觉到,他是一个和你一样的人,他的大脑活动与你一样,想法都是短暂的或者被打断的。但是,如果你真写一个完全和人的思考一样的小说是没法看的。乔伊斯就明白这一点,他知道人的思维是怎么回事,他写作本身并不真的像人的思想,但读者会觉得像人的思想,他知道怎样有选择地复制这种感觉。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喜欢的海明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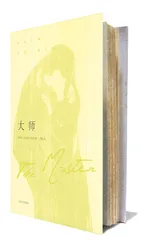
托宾:在我成为一个作家前,我是读海明威的,乔伊斯直到很晚才进入我的生活。从19世纪的小说到20世纪的小说,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跟电影和摄影的发展有关。比如哈代写地貌,会用好几页慢慢地描述,但再往后,可能就用一句话,海明威在这方面有革命性的改变。他的能力就是写很短很短的句子,但是涵盖的意思非常广,节奏感也非常快。我还记得我17岁时躺在海滩上读《太阳照常升起》的情景,从词语间流淌出来的情感穿过我的身心,至今我仍喜欢里面的一些句子和节奏,我想我1975年去西班牙生活,可能就和这部小说的影响有关。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在《大师》中,你用了一种很经典的叙述,更接近亨利·詹姆斯的时代?
托宾:英语有来自不同语言的一些词,古英语是德语系语言,这种盎格鲁-撒克逊的语言,单词短促、有力,而来自拉丁语的单词比较长,也是比较经典的风格。这部小说,用了很多来自拉丁语的词,我觉得比较符合小说的气氛。
三联生活周刊:你也是爱尔兰一个艺术团体的成员,而你谈到过你对立体派的迷恋,无论《尤利西斯》、海明威,还是立体派,都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那是人类文化艺术特别活跃的一个时期,你也很喜欢爵士乐吗?
托宾:我听很多音乐,不很喜欢爵士,觉得它太自由。我听音乐时,一直很注意它的结构,钢琴奏鸣曲就有结构,我更喜欢这类音乐。当然还有用一种颜色或线条表达感情的艺术,也是非常震撼的。我在美术馆看到蒙德里安,能得到一种很纯粹的快乐。这些对我小说的影响是,我对小说控制得特别严,虽然读着好像很随机的,但都是计划出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故意的。我有些作家朋友,他们会去做很多尝试,看看能发展出什么,我做不了这种事。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中文译者柏栎说,他在翻译《大师》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体验:“它几乎将我包含在内,素昧平生又似曾相识。”你是否预料到读者会有这种感受?是刻意营造的吗?
托宾:没错,尤其是在《大师》中,我想让读者感觉自己已经变成了亨利·詹姆斯,我堆砌很多细节,让读者想象他心理是怎么样的,不仅想象,还变成这个人物,从这个人物的身份出发来想象世界,观察世界。我把这个叫做“亲密的第三重人生”(the third person intimate),我小说里的世界全是从第三人称的视角来看,作者本人不在现场。书里只有这些人物,但有一部分是拿你自己的感情装饰人物的感情,你要做到的,是读者看不出来这些感觉是作者在说话,就像口技一样。这种做法,我也用在了《布鲁克林》中,比如女主角晕船,我可以通过写作,让读者感受到同样的感觉,目的就是希望读者和人物有认同感,就好像看你自己的故事,如果你继续翻页,我就赢了。
三联生活周刊:《布鲁克林》从女性的体验来写,你是如何获得这种视角的?
托宾:一个小说家都应该有这种想象力,我也可以从拿破仑的视角来讲故事。话说回来,小时候,我身边全是女人,我的妈妈有两个姐妹,我也有两个姐妹,我老是听她们讲衣服、感情,七七八八的事情。我对英语最早的印象就是听女人说话。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一个女性看待事物会和男性有何不同呢?
托宾:这非常重要,比如一个男人从爱尔兰到布鲁克林去,尤其是在50年代,他会去看体育比赛,去酒吧,来掩饰他内心的孤独。但一个女孩子不可能独自去酒吧,连在马路上走路,都要规规矩矩的。女孩可能会沉默下去,躲回到房间里。但另一方面,女人比男人更容易承认自己的感情,女人对自己的感情比较诚实。她们的这些感情来得纯粹而强烈,不是自我欺骗。男人比较不容易承认这种感情,而是摆出一个潇洒的架子.我为什么选择女性?区别就在这里。
三联生活周刊:《布鲁克林》更多是往内心里走的,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布鲁克林”可以换作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托宾:没错。我这么做不是想改变世界,而是想做点有意思的事儿。我想写的是那种离乡背井的感觉,离开你熟悉的地方。巴西人去了欧洲,或者中国人到了纽约,感觉这个国家不是我的国家,早上的空气不是我熟悉的空气,有很多人在世界上走来走去,每次都是一个人,到了一个新地方,照样起床工作。慢慢地,他没有那么想家,但偶尔会因为一个声音或气味,而思绪突然回到故乡。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你也热衷于政治,那你觉得一个作者的角色应该是什么?
托宾:应该对你的句子负责。如果觉得政治上有什么该做的事儿,那你就别做作家了。你专心写你的句子,尽量保证都是真实的,有责任感,就这些。如果尽量写到真实,就会引发别的问题,关于世界、人心,但你的出发点,最核心的,就是写一个真实的句子。一个完美的句子也可以隐喻现实的真实性,但如果认为你的角色是引导别人,也别做作家了,有的是更有效的引导方式。写作不仅是娱乐,也不仅是一种逃避的方式,好小说让世界变得更丰富,客观上也在改变世界,让人之间更近、更亲切,而你的责任是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让他读下去。小说可以掩饰你自己的缺陷,别把这些缺陷放到人物身上,没有人知道,把句子写好也是对这个世界的善意。
三联生活周刊:就是说,一本好小说是可以改变世界的?
托宾:19世纪女性开始写小说,真的改变了所有英国人对女人的看法,乔伊斯的小说改变了全世界对爱尔兰的认识,所以说,小说有时候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它的重要性不在这个,而是读者看到,在小说里,感情很深、思想很深的人怎么生活,自己能不能像这种人一样来思想和感受,这是一种很个人的改变,是有道德的结果,但不是直接引导。■
(感谢Eric Abrahamsen协助) 人生第三重托宾亲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