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斯托克野史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袁越)
 ( 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自娱自乐的乐迷(摄于1969年) )
( 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自娱自乐的乐迷(摄于1969年) )
1969年8月15日17点零7分,在美国纽约州伍德斯托克镇附近的一个名叫白湖的地方,一位名叫里奇·黑文思(Richie Havens)的美国黑人民歌手穿着棕红色大氅,足登一双凉鞋走上舞台,用手中的木吉他奏响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第一个音符。这个以“和平与音乐”为口号的音乐节吸引了大约50万观众,被公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运动最具代表性的事件,黑文思那天演唱的名为《自由》的歌曲,也成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乃至整个6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歌曲。
以上这段话是历史书上对那次音乐节的官方描述。
转眼40年过去。这40年里,大约有40本关于这次音乐节的回忆录相继出版,为后人还原出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伍德斯托克。
自由的代价
伍德斯托克原本是一个距离纽约市中心160公里的避暑胜地,当地居民多以务农为生。1902年,一个富有的英国商人为了寻找一片未被工业化污染的净土,满怀希望来到纽约,在伍德斯托克建立了一个以手工作坊为主的工匠村,吸引了大批工匠、艺术家和青年学生来这里从事原始的木工、纺织、铁器和陶器制造等艺术创造和生产活动。他本想以这种乌托邦式生产方式对抗资本主义制度,但这个计划却遭到了无情的失败,工匠们生产的手工产品造价太高,根本无法和大规模机器生产相对抗,维持这个工匠村还要靠他父亲当年开纺织厂时赚来的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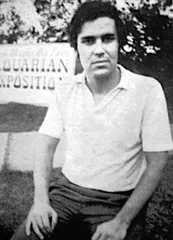 ( 音乐节创始人之一罗伯茨 )
( 音乐节创始人之一罗伯茨 )
自由是有代价的。
半个世纪后,这个理想主义者的故事又一次在伍德斯托克上演。60年代中期,一批音乐家看中了这里的艺术氛围,纷纷移居此地,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民歌手鲍勃·迪伦。1966年迪伦在伍德斯托克的森林里骑摩托车时遭遇了一起神秘车祸,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一年,复出后风格大变,唱起了毫无棱角的乡村爱情歌曲。歌迷们大为不解,不知道这个伍德斯托克给他们心中的偶像施了何种魔法。
 ( 1969 年8 月15 日,歌手黑文斯用木吉他奏响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第一个音符 )
( 1969 年8 月15 日,歌手黑文斯用木吉他奏响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第一个音符 )
与此同时,一个名叫迈克尔·朗格(Michael Lang)的长相英俊的嬉皮士搬到了伍德斯托克。朗格擅长组织音乐节,曾经成功地举办过“迈阿密流行音乐节”。这个于1968年底举行的音乐节吸引了5万观众,是那年数一数二的大音乐节。说来也怪,很多人认为音乐节是那个时代的标志,但是纵观1968年,整个美国办得成功的就只有这个迈阿密音乐节。因为大部分音乐节主办者缺乏资金,而嬉皮士观众又不喜欢买门票,结果造成了音乐节普遍质量低下,根本赚不到钱。因此,到了1969年,全美国已经没人再敢操办音乐节了。
朗格打算在伍德斯托克建一个录音棚,需要一笔投资。他去找“国会大厦”唱片公司副总裁阿蒂·科恩菲尔德(Artie Kornfeld)商量,两人决定先在这里办一个音乐节,把修录音棚的钱挣出来。恰在此时,两个毕业于常青藤学校的富家子弟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和乔尔·罗斯曼(Joel Rosenman)也打算投资一个项目挣点钱,4人一拍即合,成立了一个“伍德斯托克风险公司”,每人各占25%股份。其中真正有钱的是罗伯茨,他是个典型的“富二代”,他的开牙膏厂的父亲为他设立了一个委托基金,规定在他年满21岁时可以领取25万美元,25岁时可领取100万,30岁时还有100万,35岁时再有100万!要知道,60年代的1美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0美元。所以说,罗伯茨从来就没有尝过缺钱的滋味。
朗格因为有组织“迈阿密音乐节”的经验,被委以重任,负责整个演出的筹备。办音乐节说起来容易,可实行起来却是非常麻烦的事情。首先就是场地问题,伍德斯托克小镇本身没有大块平地,被排除在外。组委会经过仔细调查,发现在离伍德斯托克50公里远的沃基尔有一块待租的空地。经过讨价还价,组委会以7500美元的代价把这块地租了下来。
组委会最初向当地人保证说,音乐节最多不会超过5万名观众。但是,为了吸引更多观众,以便挣到更多的钱,组委会决定花大钱请大牌歌手和乐队。一开始那些大牌乐队都不愿意来,因为谁也没听说过这样一个演出公司。可他们都错了,这个公司背后的资助人罗伯茨可是真的有钱!他决定先不惜工本请来几个大牌乐队,希望能引起连锁效应,便首先用1万美元的出场费把“克里登斯清水复兴”(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乐队签了下来,而一般情况下,他们的整场音乐会出场费也就是5000美元左右。之后,著名的摇滚女歌手贾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又以1.5万美元的高价被签了下来,甚至连已经很久没有露面的美国民歌女王琼·贝兹(Joan Baez)也无法拒绝1万美元的出场费。最后,组委会决定请一个重量级的摇滚乐队来压阵,“披头士”和迪伦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人选,可“披头士”当时已经处于半解散状态,无论花多少钱也请不动。迪伦虽然就住在伍德斯托克,可英国怀特岛音乐节破天荒地给了他8.4万美元的出场费,硬是把他从伍德斯托克拉走了。最后,组委会只得以1.8万美元的代价把他们的第三选择——著名摇滚吉他手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划入了演出名单。为了安抚其他乐队,组委会不得不对外谎称亨德里克斯要演两场,才总算没有引起抗议。
歌唱自由也是有代价的。
随着签约歌星的数量和名气越来越大,沃基尔人开始感到不对劲了。他们意识到马上要在他们的后院里举行的不是一个只有5万观众的音乐演出,而是一次全国嬉皮士都要来参加的大派对。在这些保守的乡下人看来,嬉皮士就等于吸毒、性乱和暴力,他们可不愿意为了几个钱而牺牲自己宁静的乡村生活。值得深思的是,当初组委会选择这里就是要顺应嬉皮士们回归乡野的潮流,可最先反对音乐节的却是那些原本生活在乡村的农民们。
于是,就在距离音乐节开始只有一个月的时候,沃基尔村委会收回了演出执照。组委会没办法,只好到处打广告征求新的演出地点。一个名叫埃利奥特·泰伯(Elliot Tiber)的旅馆小业主看到了这个广告,主动向组委会提供自家的场地。朗格立刻坐着直升机来查看,却嫌地方太小。泰伯便又推荐了一个名叫马克斯·雅斯格(Max Yasgur)的农场主,他在离伍德斯托克不远的白湖拥有一片农场,主体部分是一块足有600英亩(约合2.5平方公里)的碗形山谷,其形状完全像是一个天然的剧场。更妙的是,这块地的后面还有一个风景优美的湖!
雅斯格很聪明,他在组委会原本答应付给沃基尔的7500美元后面加了个零,组委会没有别的选择,只好答应了下来。这个消息传开后,也有不少当地居民表示反对,还有人联名起草了一份公开信,呼吁大家罢买雅斯格的牛奶。雅斯格是个很守信用的人,收了钱后他保证绝不反悔,为此他顶住了来自周围的压力,使音乐节得以顺利举行。不过历史学家们后来认为,这里的居民普遍比沃基尔的要穷一些,音乐节所带来的额外收入对这里居民的吸引力比沃基尔大多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白湖的居民中反对音乐节的呼声比沃基尔要小很多的主要原因。
定下地方后,组委会立刻花重金招兵买马,搭建了主舞台、音响设备和后勤设施。谁知距离音乐节开始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就有大批嬉皮士从全国各地赶来这里,组委会根本来不及修围栏。为了不出乱子,组委会只好宣布演出免费,好在罗伯茨有钱,否则这场音乐会是不可能办下去的。
到了8月15日这天,闻讯赶来的嬉皮士把整个伍德斯托克地区的交通完全弄瘫痪了。据统计,当天涌进演出场地的嬉皮士大约有50万人,另有100万人因为交通拥挤而被堵在了路上。因为路不通,原本计划为音乐节打头阵的“甜水”乐队根本进不来,组委会只好让黑文斯打头阵,他是唱民歌的,只需要一把吉他。于是,黑文斯硬着头皮上台,并在连唱了将近3个小时,返场6次之后,把自己的存货都唱完了。当他第7次被迫返场时,望着台下50万双饥渴的眼睛,脑海中出现了一首古老的黑人民歌《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但是他记不住原来的歌词了,只好重复地唱道: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这个场景被拍摄了下来,成为纪录片《伍德斯托克》中最经典的画面。
黑文斯的救场为组委会争取到了宝贵时间,让他们得以联系上了美国军方,花重金雇用了几架军用直升机把“甜水”乐队,以及其他一批被堵在外面的摇滚乐队运了进来,这才没有出乱子。那部纪录片没有拍到的一个镜头是:就在接替黑文斯上台的摇滚乐手乔·迈克唐纳在舞台上大唱反战歌曲的时候,一群美军直升机呼啸着从空中掠过,为50万名观众送来了精神食粮。
享受自由更是要付出代价的。
镜头后面的故事
纪录片《伍德斯托克》的导演是一位名叫迈克尔·维德利(Michael Wadleigh)的独立电影人,他发明的分屏剪辑法为后来的摇滚纪录片树立了榜样。维德利的助手名叫马丁·斯科西斯,关于他的故事可以另写一本书了。
这部获得过1970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电影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但镜头后面的故事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镜头一:一辆垃圾车从一堆垃圾中开过去,却没有注意到一条脏睡袋里还睡着一个人。结果,一位来自新泽西州的才17岁的年轻人被活活轧死了。音乐节上还有一个人因过量吸食海洛因而中毒身亡。不过,后来人们都同意,在动荡的60年代举行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活动,最后只死了2个人,而且都可算做是意外事故,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镜头二:毒品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成为音乐节的首要问题。农场里到处都能听见叫卖大麻和LSD(一种化学致幻剂)的声音,一种黄色LSD药片因成分不纯,让400多人发了疯。幸亏在场的嬉皮士公社——“小猪农场”的成员对这种病症很有经验,他们不是给病人们服用解毒剂(这有可能更糟),而是抓住病人的手,不断地和他们讲话,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孤独的。最后这400多名患者无一留下后遗症。后来有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这次音乐节之所以那么和平,没出什么乱子,完全是因为几乎所有到场的观众都在某一种毒品刺激下“高”了,大家整天都晕晕乎乎处于迷幻的状态,哪还有什么心思去闹事?
镜头三:因为使用过量,场边的临时厕所很快就满了,加之道路被堵,清理车开不进来,致使场子里的许多厕所“粪香四溢”,许多人都不得不跑到附近老百姓的农田里“解决问题”。遇到当地农民们的干预,他们还振振有词地说:“没管你们收施肥的钱就不错了!”为了防止大雨把农场变成一个巨大的化粪池,组委会不得不在场地后面挖了一个大坑,把排泄物都倒在坑里。虽然加了许多化学药剂,可还是掩盖不住那强烈的味道。大概这也是大家拼命吸大麻的原因之一吧。
镜头四:因为人太多,原本搭建好的16个食品摊点前全都挤满了人,食物很快告罄。第二天,一群激进组织的成员抱怨音乐节出售的食品价格太高,又不好吃,开始砸场子。经过一轮哄抢,有12个食品摊位被毁。再后来,一场大雨过后,许多存放在露天的食品全都被浇坏了,组委会不得不出动直升机往农场里运送食品。当地的老百姓也都纷纷主动把家里存放的食物拿出来分享,虽然他们不同意嬉皮士们的主张,可他们却相信这一点:绝不能让孩子们饿着!但贡献最大的要算是“小猪农场”的成员们。他们预先囤积了大量便宜的花生、椰肉、瓜子、燕麦、葡萄干、面粉和糖,到时候只需把它们一股脑地放进锅里,再加水熬成糊就行了,又方便又有营养。“小猪农场”就用这样简陋的办法喂饱了大多数观众。
镜头五:美国60年代著名的异见组织“雅皮士”(Yippies)在场子里搭设了一个宣传站,向过往人群散发传单。大概是嫌这种办法效果不好,“雅皮士”的领导人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冲上舞台,夺下一支话筒发表演讲。正巧这时轮到英国摇滚乐队“谁”(Who)上台演唱,乐队的吉他手皮特·汤森(Pete Townshend)不认识霍夫曼,便二话不说,抄起电吉他就往他头上砸去,一家伙把他砸到了台下。从此以后音乐节上就再也没有人见到过霍夫曼了。
镜头六:就在音乐节开始的前两天,原本答应派警察来维持秩序的纽约市警察局突然变卦,组委会面临着没有保安的困境。后来经过紧急磋商,一部分警察答应以匿名的身份前来帮忙,并又借机把工资翻了一番。就这样,演出那天好不容易凑齐了300个名字叫做“米老鼠”或者“罗宾汉”的便衣警察,但他们大都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在“放荡”的女嬉皮士面前毫无抵抗能力。于是,现场的治安几乎完全交给了“小猪农场”临时召集来的“民警”,他们之间的暗语居然是“我忘了”。这些嬉皮警察对待大多数观众都是放任自流,除了太出格的举动外一律不加干涉,事实证明这可能是组委会所采取的最明智的政策之一。
自由之后
音乐节的第三天,农场主雅斯格被请上舞台,冲着台下欢呼的人群说道:“我认为你们向全世界证明了一点:50万个孩子完全能够聚集在一起,享受3天的娱乐和音乐,而不出任何麻烦!”
对于观众而言,这句话总结得很好,但是对于组织者而言就不那么准确了。演出结束后,组委会立刻接到了约80起各类诉讼,虽然大多数诉讼最后都不了了之,可还是让组委会头痛了很久。从组委会后来公布的账目看,音乐节共支出340万美元,收入只有130万美元,亏了210万美元。虽然后来有很多人指责组委会公布的数字有虚假成分,但他们亏了很多钱应该是没错的。最后还是罗伯茨的父亲用牙膏厂赚来的钱替儿子填补了亏空,才算没有迫使他申请破产保护。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4个创始人为了得到伍德斯托克这个名字的使用权而互相起诉对方,当初创业时建立起来的友谊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就在演出开始前两天,维德利曾经因为拿不出拍摄纪录片需要的10万美元而想反悔,有人建议罗伯茨自己掏钱先把电影拍下来,以后再想法卖。可当时已经彻底破产了的罗伯茨没有答应,而是又去找别的投资人。最后直到音乐节开始后的第二天,华纳公司才终于答应提供拍摄所需的10万美元,并以100万美元的代价把整个影片的版权买了下来。他们的理由是:只要当时在场的50万名观众每人掏2美元购买一张电影票,就能收回投资了。签约后罗伯茨是轻松地舒了一口气的,因为他终于有了第一笔实实在在的收入。可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是罗伯茨一生所做的最糟糕的决定。纪录片《伍德斯托克》及其附带的原声唱片在出版后的第一个10年里就为华纳挣来了5000万美元,而伍德斯托克组委会只拿到了其中一个很小的零头。
作为压轴的亨德里克斯是在8月18日上午8点半才终于上台演出的,当时台下只剩下不到5万名观众了。从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幕摇滚音乐史上最有代表性的画面:初升的太阳映照着一片狼藉的农场,原来满是观众的草坪被无数的垃圾所代替。亨德里克斯面对着阳光,用电吉他为大家演奏美国国歌,可从音箱中传出的声音却酷似炸弹的爆响,飞机的轰鸣,人们熟悉的旋律在亨德里克斯的即兴演奏下变成了一个动荡时代的最佳配乐。
第二年底,亨德里克斯因为吸毒过量死在了自己的床上。几个星期后,另一位在伍德斯托克表演过的摇滚歌手乔普林因为同样的原因死在了旅馆里。
就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开始前的一个星期,以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为首的几个嬉皮士闯入好莱坞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的家中,杀死了他的妻子莎伦·泰特(Sharon Tate)和几个朋友,当时泰特怀有8个月的身孕。警察在案发3个月之后才破案,美国公众对待嬉皮士的态度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嬉皮士运动被迫从城市转移到了乡村。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结束后,美国的音乐媒体都预言,今后将会有无数个伍德斯托克,但由于摇滚乐队们开始漫天要价,以及很多其他原因,这个预言并没有实现。就在那年底,著名摇滚乐队“滚石”在加州举办了阿尔塔蒙特音乐节,却因到场的观众互相斗殴,并杀死了一名黑人歌迷而宣告失败。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结束后不久,纽约州政府就专门通过一条法律,禁止大规模集会。雅斯格在农场里撒满了鸡粪,防止嬉皮士们前来纪念。事实上,他的顾虑是多余的,纵观整个70年代,只有很少的美国人会想到去雅斯格农场追忆一下当年的盛况,那个演出场地没有任何标记,个别慕名前来的人都因找不到准确地址而空手而归。这个情景很像是一个成年人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喝醉酒之后的“壮举”,要么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要么是一笑了之,没人真拿它当回事。
1999年,在距离原址300多公里远的罗马市曾经举办过一次纪念伍德斯托克30周年的演唱会,最后却以歌迷纵火焚烧场地设施而狼狈结束。2009年,组织者朗格打算在原址举办一次40周年纪念演出,却因找不到赞助商而被迫取消。
著名导演李安根据旅馆小业主泰伯的回忆录拍摄的轻喜剧《制造伍德斯托克》于2009年8月28日在美国公映,成为电影界纪念伍德斯托克40周年唯一的行动。但是伍德斯托克并不是这部片子的主题,李安只是借助这一事件,表现了一个同性恋者向自己的家庭和内心妥协的有趣过程。
不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仍然是世界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一次音乐节。从此以后,整整一代人就又多了一个共同的称号——伍德斯托克一代。虽然后来人们都说,当初参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年轻人现在都是公司老板和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可不管怎么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以及那部同名纪录片都真实地记录了这一代人曾经有过的梦想,和他们火红的青春。■ 音乐节伍德野史斯托克嬉皮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