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造字与敬惜字纸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刘涛)
 ( 仓颉图像 )
( 仓颉图像 )
古人相信文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的。黄帝时代的年限是公元前2550年到公元前2450年,这是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一书的推测,并把黄帝以前的历史称为“传说时代”。
仓颉造字之说,战国时代已经盛行。《世本》那部史书说,“黄帝使仓颉作书”,《韩非子·五蠹》有“古者仓颉之作书”云云。《吕氏春秋·君守》追溯六类“事物”之源,除了奚仲作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鮌作城,也有“仓颉作书”。所谓“作书”,就是发明文字。
仓颉如何“作书”,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叙》中有一番遥想当年的合理想象:仓颉见到鸟兽留下的蹄爪痕迹,悟到分明别异之理,造出了文字。“仓颉造字”的概念配上这样的故事,古代史学家和文字学家不断的重复,成为深入人心的常识,而且派生“仓颉四目”、“四目电光”的神异之说。
神化仓颉的参与者,还有书法家和画家。“书契之兴,始自颉皇”,这是东汉草书家崔瑗《草书势》所说,尊仓颉为“颉皇”。北宋时,仓颉被政府衙门从事文字书写的书吏称为“仓王”,在每年秋天的赛神会上举行祭祀。古代画家绘出了仓颉的形象:头披长发,嘴唇上下留着长胡须,身披草衣,袒胸露腹,表示生活在远古。按“仓颉四目”的传说,让他多出一双眼睛。古人如此臆造,想来也有道理,许多人都见过鸟兽的蹄爪之迹,唯独仓颉知别异之理,造出文字,他的眼力当然不同于凡俗之辈。眼力属于智慧之类,要在人的相貌上表示出来,只能在“传神写照”的眼睛上用心思。
造字的仓颉,从远古的口头相传,而后进入文献,演绎加上神化,最终在图像上完成他的神异形象。中国文字发生史就这样累积起来。近世以来,随着科学的昌明,文字的产生才有了合乎历史逻辑的解释。如鲁迅所说,上古社会的人们,“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信,口口相传,文字就多了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文字出现的原因非常实际,只是出于生活的需要,出自众手,经过长时间的孕育,由少渐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而后“壹”于史官。一代代主掌文字记录的史官有多人,而又“壹”于一位有名的仓颉。如果“黄帝使仓颉作书”还有真实的成分,也许黄帝时代是文字的萌芽时期,史官担当了采集、选练文字的重要角色。
 ( “大汶口文化”陶尊上刻划的图形
)
( “大汶口文化”陶尊上刻划的图形
)
发明文字是人类最突出的成就,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古人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公元前2世纪初,淮南王刘安《淮南子》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意思是,文字的出现惊动了天地鬼神,逼得“造化不能藏其秘,灵怪不能遁其形”。此属“天人感应”的文字观。公元2世纪初的东汉,许慎对文字作用的认识转入理性,所谓“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现代的学者认为,文字是文明开端的标记,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叫“文明史”,此前的历史口口相传,没有文字记载,称为“史前史”。
许慎编出我国的第一部字典,为了编字典,他把“文”和“字”做了区分。最初的造字方法是“依类象形”,那些与物(象)对应的象形字,谓之“文”,后人称为“初文”。在这些部件基础上用“形声相益”的方法繁衍的字,则谓之“字”。字是孳生繁衍的意思。许慎编的那部字典叫《说文解字》,他采用了以“文”率“字”的方法,“文”是部首,下列同一部首的“字”,开创了字典的“部首”编纂法,沿用至今。现在也有按汉语拼音排序的编纂法,以音查字,很实用,却割裂了文与字的关系。部首编纂法可以显示汉字的源流和字义的类属,使用者可以坐收举一反三之效。
 ( 殷商甲骨文
)
( 殷商甲骨文
)
东汉学者把造字的方法总结为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名为“六书”。这是最早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当代学者大多认为,前四种才是造字法,后两种是用字法。依靠这些方法,古人不断地造出新字,单字量越来越大。殷商甲骨文的单字数量约4500个。汉朝《说文解字》所收单字9353个,数量翻倍。清朝《康熙字典》,正文收单字4.7万余个,连同补遗、备考的字,单字多达4.9万余个。但是,很多字有古今之别,有繁简之异,还有一字异体者,都属于“一字多形”,还有一些弃而不用的死字,所以后世的单字数量就多了。据统计,源于象形和指事的文字,不到汉字总量的10%,会意字和形声字占汉字总量90%以上。
对于考古发现的古文字,当今学者仍然采用汉朝人归纳的造字理论去释读。越古的文字越难释读,殷商的甲骨文,犹有上千字未能释出。更早的遗迹,是新石器时代器物上零星见到的符号,辨认这些符号类似猜谜,但是基本方法还是东汉人总结的“六书”理论。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山东莒县阳陵河出土的陶尊上,刻画着一种图形,上为“日”形,中为“火”形,下为“山”形,简者是上“日”下“山”。考古学者称为“天象刻文”,文字学家有的释为“热”,有的释为“旦”,但都是从“会意”的角度释读这个图形。“大汶口文化”晚期约当公元前2800年至前2500年间,和黄帝时代的上限相接。与“大汶口文化”大体并行的“仰韶文化”遗址,如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边上也刻画着一些原始符号,有的象形,有的是记数的抽象符号。这些早期刻画符号和刻文,郭沫若认为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于省吾说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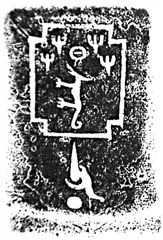 ( 殷商《二祀其卣》族徽文字
)
( 殷商《二祀其卣》族徽文字
)
迄今所见最早的汉字符号系统,是殷商甲骨文。殷商比黄帝时代晚1000多年,文字的形成也许就在这1000年间。殷商的文字,还见于青铜器上,叫“金文”,有装饰性,又是一类。那时的社会已经形成等级,文字被少数服务君王的史官、巫觋所垄断,文字不仅代表着权力,也是沟通神灵的媒介。殷商金文里,还有一种名为“族徽”之类的图文符号,所以文字的形式本身也具有“内在的力量”。
文字的“神性化”后世一直存在。不仅是文字的形式具有象征意义,文字承载的语义更使文字的威力如虎添翼。高山崖壁上镌刻的佛号,象征着佛的存在。家家供奉的祖宗牌位,上面书写的文字象征着祖先的存在。道教把古篆与草书化为符书箓文,造成人所不识的“天书”,人们相信这类文字有着驱鬼、招魂、禳灾的灵异功能,威力巨大。古代民间以诅咒文来惩罚仇敌,一直流传,也是深信文字具有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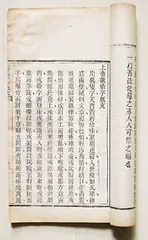 ( 民间集资刊刻的《文昌帝君惜字律》仓颉画像 )
( 民间集资刊刻的《文昌帝君惜字律》仓颉画像 )
前几年,我在报国寺文化市场买到一本民间集资刊刻的《文昌帝君惜字纸律》。“文昌”是星名,亦称文曲星,或文星,古代认为是主持文运功名的星宿。后来民间和道教把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称为“文昌帝君”。这本薄薄的书,刻于清朝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里面有多种惜字的律文,都是以道教神灵的名义发布。开卷序言就说到“仓颉造字”的功用:“有字则古人之意可见于今,远方之言可传于近,哑人能字则手可代口以为言,聋者识字则目可代耳以为听。”提到当时地方官“出示晓谕,敬惜字纸,倡募刊书立会”。
“惜字”有两种惜法。一是“下笔”之“惜”,共有12项,比如有关人的性命者,有关人的名节者,有关人的功名者,离间骨肉者,谋人自肥者,这类文字都要“惜”,劝人不要形诸文字。这是劝善。另一种是珍惜字纸,列有“十八戒”,比如卖废书与人,将字纸遗弃污秽中,脚下践踏字纸,拿字纸糊窗壁、覆缶、裱画、拭几砚、擦垢秽,烧字纸夜照、点火吸烟,以书做枕或者塞在墙壁孔内,等等。
“敬惜字纸”的观念,深入民间。赵珩《记忆中的收藏·字纸篓儿》中描写了他少年时代所见的一幕,那是上世纪50年代北京街头,收废纸的老头歇在街边,在地上把一堆纸团一一展平,带在身边的孩子无聊,看蚂蚁打架,累了坐到旧书报上,老头看见,掴了孩子一掌。赵珩不解,上前询问,老头回答:那上面有字,字是仓颉造的。做过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也曾有过类似那小孩的遭遇,留学定居欧洲之后,有年回台北,垫着报纸坐在路边歇息,一位老年人看见,指责她坐在字纸上。龙应台感慨,这就是文化。■ 汉朝考古仓颉造敬惜字纸惜字仓颉文化黄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