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鉴定之初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 定武本《兰亭序》所见“徐僧权”押署
)
( 定武本《兰亭序》所见“徐僧权”押署
)
鉴定家的对手是作伪者,但是作伪者从不露面,只是制造赝品,通过好事的收藏家,与鉴定家展开博弈。这个三角关系,始于南朝初年。
收藏之风导致作伪和鉴定。收藏名人手迹的风气,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末的西汉。《汉书·游侠传》记载,哀帝时,豪侠陈遵(孟公)封侯居长安,“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牧守当之官及郡国豪杰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陈遵是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不但行侠仗义,而且“略涉传记,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东汉前期,帝王也好收藏书法名家的书迹,《后汉书》说,宗室敬王刘睦“能属文”,“又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病寝,(明)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
南朝以前,收藏活动都很单纯,既无造假之虞,亦无鉴定之烦。到了“二王称英”的公元4世纪至5世纪之交,出现了伪造的“二王”书迹。当时揭露造假活动的人是中书侍郎虞龢,他奉宋明帝(465~472年在位)诏令,鉴定宫廷的书法藏品,在呈送的《论书表》这份“总结报告”中指出:宗室新渝惠侯刘义宗喜好收藏,不计贵贱地悬金招买“二王”书迹,“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刘义宗是《世说新语》作者刘义庆之弟,刘宋建国的公元420年由新渝县男进爵为侯,公元444年卒,谥“惠侯”。
南朝时有伪字,尚无伪画,虞龢的鉴定活动只是针对书法,当时称为“科简”,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区分“字之美恶,书之真伪”,然后“评其品题,除猥录美,供御赏玩”。这两个作业,后世的收藏家、鉴定家各有概括:唐朝张彦远分为“鉴识”和“阅玩”,明朝张丑称为“鉴”、“赏”。张丑说:“赏鉴二义,本自不同。赏以定其高下,鉴以辨其真伪,有分属也。当局者苟能于真笔中力排草率,独取神奇,此为真赏者也。又须于风尘内屏斥临模,游扬名迹,此为真鉴者也。”
鉴定之后的御府书法藏品,重新整理装裱:第一,“补接”藏品的“败字”,做到“体势不失”;第二,将原来长短不齐的卷轴剪裁皆齐,二丈为度,以整齐装治的形制;第三,装裱在一卷之内的各帖,重新编排次序,按书法水准,好者在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后,虞龢说这样做是针对赏玩的心理,“人之看书,必锐于开卷,懈怠于将半,既而略进,次于中品,赏悦留连,不觉终卷”;第四,按藏品的质地、书体分类,分别装为珊瑚轴、金轴、玳瑁轴、旃檀轴。
 ( 王徽之《新月帖》所见“姚怀珍”、“满骞”押署
)
( 王徽之《新月帖》所见“姚怀珍”、“满骞”押署
)
将藏品登记造册是虞龢鉴定活动的最后一项工作,他编制了名家书迹的目录:《钟张等书目》(一卷)、《新装王羲之镇书定目》(六卷)、《新装王献之镇书定目》(六卷)、《羊欣书目》(六卷)。这些书迹目录属于“目录学”一类。目录学的先河启自《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文献典籍,后来成为专门的学问。书迹编目则始于虞龢,但是这些书目早已失传,不知具体登录了哪些项目。此后南齐的马澄编有《逸少正书目录》,据说录有帖名、卷数,还简短的注文。唐朝褚遂良的《右军书目》现在还能见到,分正书、行草书两门,著录每卷的编号,抄录帖首一段文字,以及帖文的行数。虞龢所编的名家书迹目录,大概不外如此。
讨论书法真伪的最早文献是梁武帝与陶弘景“《论书启》九首”,即9件往来的书信,梁武帝4封,陶弘景5封。梁朝收藏的名迹数量居南朝之首,“二王”书迹多达“七百六十七卷”,如果按每卷10纸(帖)的装治规制计算,“二王”书迹合有7600余纸(帖)。刘宋的收藏规模居南朝第二,“二王”书迹有247卷2400纸(帖),犹不足梁朝的半数。但是,梁武帝并不相信内府所藏的名家手迹都是真迹,将藏品送到陶弘景隐居的茅山,请他鉴定把关,两人通过书信交流鉴定意见。他们依据书家的书法特征辨真识伪,例如笔画之粗细、笔力之老嫩、结构体态,甚至书家书迹的阶段性特征。这种识别真伪的鉴定方法,名为“目鉴”,只有见到一人或一个时代的大量书迹才能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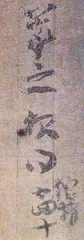 ( 王羲之《寒切帖》所见“徐僧权”押署
)
( 王羲之《寒切帖》所见“徐僧权”押署
)
梁武帝、陶弘景甄别出来的伪作,并非全是为牟利而故意造假的赝品,还有相当数量的赝品属于张冠李戴的无意混淆,成因比较复杂,析而论列,分为三类。
第一类,代笔的赝品。陶弘景指出:王羲之晚年有人代笔,笔迹“缓异”,世人不能分辨,“呼为末年书”。羲之亡后,年方十七八的献之全仿此人书,遂与之相似。
 ( 王羲之《何如帖》所见“姚察”、“唐怀充”押署
)
( 王羲之《何如帖》所见“姚察”、“唐怀充”押署
)
第二类,因名家笔迹相近而混淆。王献之学王羲之,父子书法相近,献之《不复展》帖就混在梁内府所藏编号二十四的王羲之卷中。王羲之好友谢安的书迹,王羲之从子王珉的书迹,也被认在王羲之名下。这种情况,唐朝依然存在,张怀瓘《书断·中》记载,南齐张融善草书,多骨力而有古风,人们误“以为张伯英(芝)书”。
第三类,将临摹本混同为名家书迹。经陶弘景鉴定,第二十四卷的王羲之书迹,《便服改月》一纸“是张翼书”。张翼“善学人书”,东晋穆帝时,仿写王羲之奏表,羲之也不能辨别,感叹“几欲乱真”。梁朝的藏品,这类赝品最多,“后人学右军”的《黄初三年》一纸,甚至“摹王珉书”的《五月十一日》一纸,都误为王羲之书迹。唐朝张怀瓘《二王等书录》指出:南朝人康昕、王僧虔、薄绍之、羊欣摹学王献之,他们的书作也混在“二王”书迹中。南齐时,内府曾经复制了一批藏品,赐予皇室诸王与朝廷重臣,这种复制品,当时称为“出装书”。宫内传出的摹本又会广泛复制,从而衍生大量摹本。梁武帝收罗法书名迹之际,大量临摹本进入御府,梁朝收藏的名迹数量远远多于刘宋御府,也就不足为怪了。
 ( 王献之《廿九日帖》所见“徐僧权”押署 )
( 王献之《廿九日帖》所见“徐僧权”押署 )
经过鉴定的真迹,须由宫廷的“鉴识艺人”在宫廷藏品上署名,作为秘藏、鉴定的标记。这是南朝上层的书法鉴定活动中一直实行的“押署”之制。唐朝《历代名画记》卷三记载了南朝“鉴识艺人押署”的名单:宋3人、齐2人、梁14人、陈2人。各朝御府押署人数之多寡,应该与各朝藏品数量相当,间接地反映了各朝藏品数量上的差异。现存的东晋法书名迹,还能见到一些南朝的押署遗存。例如辽宁博物馆收藏的《万岁通天帖》(《王氏一门书卷》),天津博物馆藏王羲之《寒切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这些珍贵的唐摹本、古摹本,也将押署照摹这来,有“满骞”、“唐怀充”、“徐僧权”、“姚怀珍”,都是梁朝宫廷鉴识艺人的押署,有的姓名全署,有的只署名。《平安·何如·奉橘三帖》上还有隋朝“姚察”的押署,表明这个制度延续到隋朝。押署题于这些名帖的首尾,有的并排联署,后人割裂重新装裱之后,位置贴近纸边,在帖的首尾接缝处,后人再加裁割,有的残留半个字。我们今天见到“半字”押署,即可知道该帖曾经裁接。借助押署,后世鉴定家可以考察某一书迹(原迹)的流传经过。
南朝内府相沿的鉴藏制度,在唐朝发生了一些变化。贞观年间,内府装治王羲之法书,开始在卷中接缝处钤盖“贞观”小印。后世收藏家在藏品上钤盖私印、收藏印的风气,肇端于此。也是在唐朝初年,名迹又有“跋尾”,后来发展为书画题跋。唐人在藏品上钤印、跋尾的做法,皆属南朝押署的变制。北宋时,私家收藏风气盛于唐朝,收藏鉴定家黄伯思以考察“文本”来辨别古代法帖真伪,这种“考订”的鉴定方法,完成了传统鉴定的学术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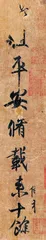 ( 王羲之《平安帖》所见“徐僧权”押署 ) 之初南朝梁高祖书法鉴定艺术陶弘景王羲之二王文化王羲之书法
( 王羲之《平安帖》所见“徐僧权”押署 ) 之初南朝梁高祖书法鉴定艺术陶弘景王羲之二王文化王羲之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