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发表50周年
作者:薛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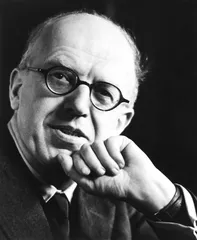 ( 斯诺和他的文集《两种文化》 )
( 斯诺和他的文集《两种文化》 )
诗人要不要懂科学?
1956年,英国物理学家、政府科学顾问和小说家斯诺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题为《两种文化》的文章,3年后的5月7日,他将文中的思想加以扩充,在剑桥大学做了一个著名演讲,题为《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斯诺感叹,整个西方社会的知识生活日益被分化成两极群体: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斯诺指责文学知识分子们导致了两个群体之间缺乏了解。斯诺说,文学知识分子对科学家从不读英国文学名著嗤之以鼻,但他们说不出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内容却丝毫不以为耻,而这相当于问科学家是否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
关于文人不懂科学,斯诺还说道:“20世纪的科学很少有被吸收进20世纪的艺术中的,这是令人不解的。我们过去常常看到诗人有意识地使用科学术语,不过却用错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折射’一词经常以神秘的形式出现在诗中,‘极光’也经常被使用,好像作家们幻想这是一种特别令人崇敬的光。”
不过,1910年,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在《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书中说:“艺术所从事的心理学与关于心灵生活的抽象科学毫无共同之处,任何人也不会建议诗人去从事科学的心理学研究,以便通过这种方法更好地学会如何写诗。艺术不是从概念上而是直觉地把握心灵生活。”
斯诺的演讲引起了轩然大波。剑桥大学的利维斯对斯诺发起了人身攻击,说斯诺在智力上并不出类拔萃,他的演讲展示的恰恰是“智力特色的全然缺乏和令人窘迫的粗俗风格”。美国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的评论则更为绵密、温雅,但他也认为,斯诺的书确实在很多方面都出了错。和利维斯一样,特里林不同意斯诺对19世纪文人的抱怨,斯诺说19世纪的文人不是憎恨工业革命,就是干脆无视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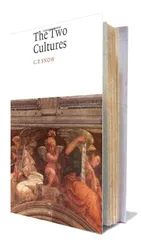
今天,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发生了交汇,但跟斯诺当年预料的不同。过去20年间,约翰·布罗克曼一直在宣扬“第三种文化”这一概念,指出进化生物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家们正在揭示生命的深层含义,取代文学家和艺术家,塑造我们的思想。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约翰·博伦(Johan Bollen)等人对在线科学期刊的点击流量进行分析,这些数据显示使用者在各种期刊之间跳读的时间间隔,由此总结各学科间的网络关系,例如阅读医护期刊的读者,会翻读到皮肤科或大脑研究、认知科学、语言等等。该研究项目本月发布的知识地图显示,虽然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仍然界限分明,但明显有几个交叉和重叠的区域。
1963年,斯诺在《再谈两种文化》中说,用热力学第二定律考验科学常识不太恰当,因为没有一些物理学知识,理解它是不可能的。他想把第二定律换成分子生物学,“第二定律是涵盖宇宙的普遍原理,分子生物学则只与宇宙的微观部分打交道,由于这些微观部分恰好与生命相关联,它们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意义”。分子生物学不涉及严肃的概念,不需要太多数学知识来理解它,“最需要的是视觉和三维想象,它是一个画家和雕塑家可能会立即认同的学科”。但斯诺以为,社会科学家将形成第三种文化:一些社会历史学家既同科学家保持着友好关系,又感到有必要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文学知识分子。
自然科学影响普通人的中介到底应该是什么?哈贝马斯在《向着一个理性的社会》中说:“科学的内在发展使得即使在不同学科分支之间进行技术信息的恰当转译也成为基本上不可解决的问题,更不用说在科学和广大公众之间了。”因此需要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基于人类对于历史理解旨趣的解释性科学,以促成把科学信息转译为日常的实践语言。
技术进步与文化传统
斯诺在书中主要不是批判文人和科学家之间的鸿沟,而是宣扬技术能给我们带来的美好未来。《两种文化》(1963年出版,汇集《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再谈两种文化》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了中译本)更深层的论点不是我们拥有两种文化,而是说科学将使我们过上繁荣、安稳的生活。
斯诺断言:“如果说科学家与生俱来充满希望,那么传统文化的反应是但愿这种希望根本不存在。”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科学家是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不知道人类的状况,“大凡思想深刻的人,不管他们情绪多么高昂、多么有幸福感,甚至包括那些情绪最为高昂、最为幸福的人,悲剧感一直深藏在他们的骨子里,挥之不去。但科学家更想急切地去做事情,并且认为除非被证明不可行,否则就是可以做到的。这就是他们真正的乐观主义”。
斯诺认为,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导致人们忽视科学的使命,阻止了我们利用它解决世界上的主要问题:工业化国家的人们越来越富,非工业化国家的人们充其量只不过是维持现状,所以工业化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每天都在加大。为了世界的稳定,为了西方不再富裕但不安地生活,西方必须促使穷国转变成富国,但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却导致西方人难以把握这种转变的规模必须是多大,这种转变会有多快。
斯诺相信,随着社会变化速度的加快,贫困问题很快就能解决,穷国的人不再需要等到下一辈子了,贫富差距不会延续到21世纪。西方只要向亚洲和非洲派出科学家,把自己知道的东西传授给他们,他们也能迅速实现工业化。但西方人不能以家长作风做这件事,要把当地人当作同事。这对科学家来说并非难事,“因为他们比大多数人更不容易受种族情绪的影响,他们的文化在人际关系方面是民主的。他们圈内的气氛是:人类平等的春风迎面而来”。技术很好学,很长一段时间,西方极为严重地看错了这一点。“我们不知不觉地让自己相信整个技术多少是一种无法说出来的技术。”英国人较早地掌握了技术,只是因为他们的儿童都玩机械玩具,美国10个成年人中9个能开车。“这些都不是大问题,为了使一个大国全面工业化,像今天的中国,只要有意志就可以培养出足够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没有证据表明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科学理解力上比另一个更好,传统和技术背景只起极小的作用。”
迪奇克说,斯诺描绘的工业化道路追随的是经济学家罗斯托“从起飞进入经济持续增长”的理论,这种现代化理论认为,所有国家都可以效仿西方的发展轨迹。斯诺的理论带着很多当时的历史印记,比如他说科学革命需要资本,所以必须是国家行为,私人工业不能涉及它。
与斯诺相反,迪奇克认为,美国人的技术创新跟他们的企业家精神有关,他认为:“斯诺对贫富差距问题的诊断仍为人们普遍接受,但他开的药方被忽视了。我们近几十年来认识到,技术进步发生于不可预测的创业洪流,由此我们才能够立于创造性破坏的风头浪尖上。在这种情况下,一位严谨的英国技术专家倡导的大规模政府援助计划就显得不对胃口了。”■ 科学革命两种文化发表50周年